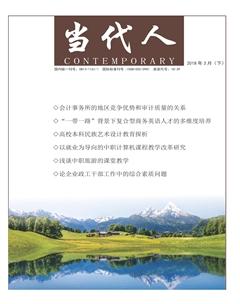我演奏三弦參加戲曲伴奏感悟
耿在恩
我從13歲開(kāi)始學(xué)習(xí)演奏三弦,于1985年考入濮陽(yáng)市戲曲學(xué)校85音樂(lè)班,專門學(xué)習(xí)三弦演奏。從13歲到現(xiàn)在演奏三弦多是參加戲曲伴奏,多年來(lái)的演奏實(shí)踐,使我深有感觸。
我深知要想把三弦演奏成功,必須深入研究音樂(lè)的特性。按照《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shū) 音樂(lè)·舞蹈卷》中對(duì)“音樂(lè)”條目的解釋,音樂(lè)是憑借聲波振動(dòng)而存、在時(shí)間中展現(xiàn)、通過(guò)人類的聽(tīng)覺(jué)器管而引起各種情緒反應(yīng)和情感體驗(yàn)的藝術(shù)門類。”從目前的音樂(lè)生活中大多數(shù)人日常所能欣賞到的音樂(lè)基本上都可以包含在這一關(guān)于音樂(lè)的定義范圍內(nèi),但是20世紀(jì)一些現(xiàn)代音樂(lè)流派的“作品”顯然難以用這一定義涵蓋,例如偶然音樂(lè)的一些作品(如美國(guó)作曲家約翰·凱奇的《4分33秒》是不由演奏者發(fā)出任何聲音的所謂作品)。不過(guò),這些特例,不應(yīng)該影響我們對(duì)音樂(lè)這門音響藝術(shù)的一般理解。
從這一定義出發(fā),我們可以具體地確認(rèn),音樂(lè)是一門聲音藝術(shù),但它采用的聲音材料具有非語(yǔ)義性的特征,正是在這一點(diǎn)上它區(qū)別于口頭語(yǔ)言藝術(shù)。后者的聲音雖然也是在時(shí)間上展開(kāi)的,但它是按照語(yǔ)義學(xué)的規(guī)則組織的,而音樂(lè)的非語(yǔ)義性音響則是遵循各時(shí)代、各民族的音樂(lè)規(guī)律和習(xí)慣構(gòu)成的。另外,音樂(lè)還是一門非描繪性的藝術(shù),它不可能描寫(xiě)生活中具體事物和場(chǎng)景,而是通過(guò)時(shí)間展開(kāi)音響構(gòu)成的各種要素,以直接激發(fā)和呼喚聽(tīng)者的情緒、情感和意志。與文學(xué)和繪畫(huà)等藝術(shù)相比,音樂(lè)藝術(shù)更注重嚴(yán)謹(jǐn)?shù)男问胶徒Y(jié)構(gòu),因此也有人說(shuō)音樂(lè)是一門形式的藝術(shù)。
三弦是一件較難學(xué)成的樂(lè)器。民俗有這樣的描述:“千日琵琶百日箏,半世三弦難學(xué)成”。同時(shí),三弦又是一件“源于民間,存于民間”的傳統(tǒng)樂(lè)器,若要深入地學(xué)好三弦,發(fā)展三弦,要立足傳統(tǒng)。三弦是我國(guó)民族樂(lè)器中一件古老的彈撥樂(lè)器,其獨(dú)特之處在于自誕生之日起就長(zhǎng)期流傳、發(fā)展于民間,作為一件純粹的民間樂(lè)器,三弦有著豐富深厚的民族底蘊(yùn),但從另一角度來(lái)說(shuō),其過(guò)于分散自發(fā)、較局限性的存在形式,也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三弦的繁衍與發(fā)展。可是,三弦仍然作為一件極富表現(xiàn)力和感染力的民族彈撥樂(lè)器,而深受中國(guó)廣大群眾乃至世界廣大群眾的愛(ài)戴和喜歡。
首先,三弦是皮膜(琴鼓蒙蟒皮)彈撥樂(lè)器,使其音樂(lè)粗獷、深厚而響亮,極具特點(diǎn);其次,關(guān)鍵在于,三弦無(wú)品(這在我國(guó)彈撥樂(lè)器中較為罕見(jiàn))且頸長(zhǎng)(音域?qū)拸V),這一設(shè)計(jì)幾乎催化出三弦演奏技術(shù)的全部?jī)?nèi)涵和特點(diǎn)。也正是這一形制上的獨(dú)特設(shè)計(jì),使三弦得以成為更能表現(xiàn)中國(guó)民族傳統(tǒng)音樂(lè)“音腔”特色的彈撥樂(lè)器。所謂“音腔”,即指在音樂(lè)的過(guò)程中有意運(yùn)用的,與特定的音樂(lè)表現(xiàn)意圖相聯(lián)系的音成份(音高、力度、音色)的某種變化,源于對(duì)這種民族傳統(tǒng)音腔特點(diǎn)的適應(yīng)和充分體現(xiàn),三弦左手演奏技巧(如滑音)應(yīng)運(yùn)而生。而具體的音色變化又可表現(xiàn)出諸如剛、柔、濃、淡、厚、薄、明、暗、實(shí)、虛、潤(rùn)、澀、華、樸、圓、尖、顫等多種不同的層次。
如何把三弦這件民族彈撥樂(lè)器融入戲曲伴奏樂(lè)隊(duì),發(fā)揮其獨(dú)特的魅力,是我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標(biāo)。
在1998年,我有幸參加了張士芳編劇、導(dǎo)演及編舞的大型柳子戲伴舞《貂蟬拜月》的伴奏。當(dāng)時(shí),這個(gè)戲是由山東省柳子劇團(tuán)的著名作曲家侯俊美先生擔(dān)任作曲。后來(lái)這個(gè)戲演唱及曲譜分別由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社和中國(guó)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也在河南省電視臺(tái)“梨園春”欄目演出,又到山東省省會(huì)濟(jì)南以及山東菏澤等多地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感到三弦的獨(dú)特藝術(shù)魅力,是不可低估的。例如:全劇一開(kāi)始,舞臺(tái)上出現(xiàn)用演員組成的一朵碩大的“荷花”。飾演貂蟬的演員用“大臥魚(yú)”在舞臺(tái)中部,舞女們用長(zhǎng)水袖及象征荷葉的綠色舞裙把潔白漸粉色服飾的貂蟬包起來(lái),組成一朵碩大的荷花。一輪潔柔明亮的圓月懸掛碧空,清澈碧透的湖水托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這時(shí)的舞臺(tái)是靜止的,演員貂蟬是在聽(tīng)了恩師、義父王允的囑托也可以說(shuō)是指令,身負(fù)重任,為了祖國(guó)統(tǒng)一,去離間漢未權(quán)奸董卓與呂布的關(guān)系,貂蟬作為一名潔白無(wú)瑕的美貌少女,要去虎狼之窟,用自己自身的潔白之身去離間一對(duì)“亂世奸雄”,她的內(nèi)心是極矛盾的,這些激烈的內(nèi)心掙扎,全靠音樂(lè)來(lái)表現(xiàn)。況且,三弦是柳子戲三大件之一主奏樂(lè)器,其表現(xiàn)力不容忽視。伴著貂蟬“上拋袖”、“下摔袖”、“小蹦子”、“翻身”、“臥魚(yú)”以及舞女們“平轉(zhuǎn)”、“點(diǎn)地翻身”、“大臥魚(yú)”的各種身段造型,三弦時(shí)而如撥動(dòng)心弦的強(qiáng)音,時(shí)而冷靜,時(shí)而激越,沒(méi)有嫻熟的演奏技巧是絕對(duì)完成不了這一演奏任務(wù)的。我反復(fù)聽(tīng)導(dǎo)演闡述,對(duì)貂蟬此時(shí)此地的心情以及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的局勢(shì)作全面了解,才準(zhǔn)確地傳達(dá)出貂蟬的內(nèi)心,每演到此處,觀眾總是報(bào)以熱烈的掌聲,我感到,三弦在演奏中的作用是巨大的。還有這個(gè)戲的重場(chǎng)戲;貂蟬向月神傾訴自己的心事。只用三弦這一件樂(lè)器伴奏。當(dāng)時(shí)的舞臺(tái)上,舞女們組成曲經(jīng)通幽的迴廊,貂蟬穿過(guò)其中,向月神傾訴心事,并祈問(wèn)自己應(yīng)該不應(yīng)該去赴國(guó)難,一直到最后下決心去,這個(gè)過(guò)程,一直用三弦獨(dú)奏配合演員的演唱,我當(dāng)時(shí)調(diào)動(dòng)了全部演奏技巧,用心演奏,準(zhǔn)確傳達(dá)了貂蟬的內(nèi)心。我感到這源自于對(duì)三弦演奏技能的嫻熟和對(duì)劇本的深入研究。我深有感觸,每演至此,觀眾在深深打動(dòng)的同時(shí),高聲叫好,掌聲雷動(dòng),我也享受到了演奏得到觀眾認(rèn)可的喜悅。這需要演奏者對(duì)按音、把位、換把、揉弦,滑音等技巧的嫻熟運(yùn)用。我感覺(jué)到在弦索漫長(zhǎng)的發(fā)展流傳與繼承的過(guò)程中,三弦這件由華夏人民創(chuàng)造的富有特色的樂(lè)器,一直占據(jù)著不可忽視的地位,在弦索發(fā)展的同時(shí),作為主奏樂(lè)器的三弦也形成了自己的演奏特色。
我在大型現(xiàn)代豫劇《月到中秋別樣圓》中的三弦演奏,更令人難忘。
《月到中秋別樣圓》是濮陽(yáng)市豫劇團(tuán)參加河南省第十一屆戲劇大賽的獲獎(jiǎng)劇目,并獲得了河南省“五個(gè)一工程”獎(jiǎng),我在該劇伴奏過(guò)程中,也感受到了三弦的獨(dú)特魅力。
《月到中秋別樣圓》是通過(guò)一個(gè)愛(ài)情和一個(gè)家庭悲歡離合的故事,折射出了新時(shí)期人們思想、觀念的裂變,用劇中男二號(hào)張海良的話說(shuō),就是:“你我是同在一個(gè)煤窯挖煤,生死與共的患難弟兄,可一個(gè)成了殘廢,跑了老婆,一個(gè)卻成了大老板,多了個(gè)老婆!哼...哈...嘿......!”張海良說(shuō)的“成了殘廢,跑了老婆!”就是張海良自己。說(shuō):“一個(gè)成了大老板,多了個(gè)老婆!”是該劇中男一號(hào)李春和,李春和成了大老板,打算八月十五中國(guó)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回家與愛(ài)人離婚,和城市人結(jié)婚。可是碰到“一團(tuán)亂麻”的家庭糾葛、感情撕扯,全劇就這樣展開(kāi),尤其是劇中的男二號(hào)張海良(由張士芳飾演)在劇中有一件傳統(tǒng)樂(lè)器隨身帶:三弦!這個(gè)戲的作曲就在導(dǎo)演張士芳的要求下,把以三弦為主奏樂(lè)器的樂(lè)段作為主題音樂(lè),由劇中張海良飾演者張士芳演奏三弦自彈自唱的唱段作為全劇的貫穿唱段,也可以說(shuō)是主題歌。這給我演奏三弦?guī)?lái)了施展演奏技巧的廣闊天地;同時(shí),也帶來(lái)了難度。我需要把劇本研究透。張士芳導(dǎo)演寫(xiě)的《月到中秋別樣圓導(dǎo)演闡述》我?guī)г谏磉叄磸?fù)琢磨。劇本的時(shí)代背景、主題、立意、現(xiàn)實(shí)意義、演員的情緒分析、劇中人物的思想線、行動(dòng)線、感情線、劇本的題材、體裁、人物語(yǔ)言的行動(dòng)性、音樂(lè)的特色及伴奏要求,我下了大工夫深入研究。尤其是張士芳飾演張海良的主題歌;“肚子餓了別害怕,有糧吶;身子乏了,別害怕,有床吶;孩子哭了,別害怕,有娘吶;日頭落了,別害怕,還有天上的月亮吶......”我更是反復(fù)研究其中的無(wú)窮內(nèi)涵和蘊(yùn)含的哲理,并把這些思考運(yùn)用到三弦演奏實(shí)踐中去,取得了很強(qiáng)的藝術(shù)感染力。
我從中也體會(huì)到了,演奏員必須有深厚的音樂(lè)素養(yǎng),才能成功完成一個(gè)戲的演奏。中國(guó)無(wú)數(shù)音樂(lè)名曲在我演奏中給我了滋養(yǎng)和動(dòng)力,例如:傳統(tǒng)名曲《陽(yáng)關(guān)三疊》、《揚(yáng)州慢》、《滿江紅》,民間歌曲《小白菜》、《繡荷包》、《藍(lán)花花》、《走西口》、《康定情歌》、《小河淌水》、《孟姜女》、《茉莉花》、《鳳陽(yáng)花鼓》、《嘎達(dá)美林》,民族器樂(lè)獨(dú)奏曲《梅花三弄》、《流水》、《廣陵散》、《瀟湘水云》、《喜相逢》、《百鳥(niǎo)朝鳳》、《二泉映月》、《光明行》、《十里埋伏》、《彝族舞曲》、《漁舟唱晚》、《中花六板》、《雨打芭蕉》、《春江花月夜》等,以及近現(xiàn)代中國(guó)名曲《黃河大合唱》,小提琴協(xié)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tái)》等,還有眾多外國(guó)名曲。這些中外名曲給了我無(wú)盡的音樂(lè)元素滋養(yǎng),促使我在三弦演奏中能施展自己的演奏技能,縱橫馳騁,用心琢磨揮灑自如地去成功演奏作品。
戲曲音樂(lè)是我國(guó)獨(dú)立屹立于世界藝術(shù)之林的瑰寶,戲曲伴奏中的三弦演奏藝術(shù)是戲曲音樂(lè)伴奏藝術(shù)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shí)也是總體三弦演奏藝術(shù)中一個(gè)極具光彩的重要方面,對(duì)三弦獨(dú)奏作品的形成與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戲曲伴奏中的三弦演奏藝術(shù)是一個(gè)值得研究的內(nèi)容豐富、涵蓋面廣并歷久彌新的課題。
對(duì)歷史的反思,可以使我們明確今后的努力方向。面對(duì)祖先留給我們的富貴財(cái)富,我們所考慮的,是如何更好地將它傳承下去,這是我多年來(lái)演奏三弦參加戲曲伴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