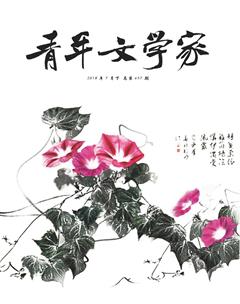《左傳》中“鄭伯克段于鄢”與《圣經》中“雅各以掃兄弟相爭”的比較研究
作者簡介:田嘉輝,河北大學2017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1-0-02
無論中西古今,兄弟相爭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反復上演的事件,而這一現實問題也總是被文學作品所反映。例如,《尚書·堯典》中的“舜象之爭”。還有西方文學經典《圣經》中“該隱殺弟”的故事。本文以《左傳》中的“鄭伯克段于鄢”和《圣經》中的雅各和以掃兄弟之爭的故事,這兩個中西文學中“兄弟相爭”的典型代表作為分析對象。兩個故事的主題都是兄弟二人對于族、國領導權的爭奪。
一、對兩對兄弟的道德評價標準不同
鄭武公一家正是儒家倫理體系的絕佳象征,其父既是家父又是國父,其母既是家母又是國母,其子既是兄弟,又是未來的君王。“君王之家”既是國內千萬小家的楷模,又是一個國家興衰的晴雨表。而身處至高位置的“君王之家”,由于各方勢力的滲透、糾纏,往往也是最難和睦相處的。鄭伯和共叔段所遇到的正是這個問題。鄭武公死后,鄭莊公繼位,武姜氏和兒子共叔段本應安守本分、輔佐國君,共同維持小家和大家的雙重穩定。但共叔段心生嫉妒,再加上母親武姜氏的縱容,身為“京城太叔”屢屢做出越軌行徑,甚至在哥哥的眼皮底下屯糧招兵建立一個“國中國”。所以左丘明將《春秋》中的“段”解釋為“段不弟,故不言弟”。身為弟弟不但不尊敬兄長,反而肆意縱容自己的野心,暗中覬覦兄長的王位。再來看鄭莊公,身為昆兄同時又是一國之君,明明已經察覺到弟弟圖謀不軌,面對臣下的屢次諫言無動于衷,甚至還說出“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且待之。”讓大臣和自己一同看弟弟的不義之行是如何招致災禍降于己身的。在以傳統倫理觀和儒家生命哲學為指導的價值判斷下,左丘明對于這個發生在“君王之家”的兄弟鬩墻的悲哀行為,自然會各貶一筆。而這場兄弟之爭的收尾,依然需要儒家倫理觀念的彌合。
下面來看《圣經》中“雅各和以掃相爭”的故事。對比雅各何以掃兩兄弟,弟弟給人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聰慧、伶俐,以及對于美好、幸福生活的無比渴望。這一點在他出生時的細節中有所表現,雅各雖說晚于哥哥出生,但是卻緊緊抓著以掃的腳跟,仿佛對于僅晚哥哥一步來到世上的結果很不服氣。因此“雅各”的名字在希伯來語中有“抓住”的意思。后來,雅各用紅豆湯和面餅從打獵歸來的以掃那里騙得了長子的名分。接著又在母親的幫助下,從父親那里騙得了原本為哥哥準備的祝福。為了逃避以掃的報復,只好寄人籬下于母舅拉班家中。為了娶到美麗的表妹拉結,在舅舅家中勤勤懇懇地工作了十四年。返回家鄉時又運用聰明才智,將拉班家中的肥壯牲畜帶走。在歸鄉途中,和上帝派來的使者摔跤,雖然大腿受傷卻從對方那里得到了祝福和“以色列”的稱號。在和以掃相見之前雅各依舊表現出了極高的智慧,他讓獻給以掃的牲畜隊先出發,以平息哥哥的怒氣,又將大部隊分為兩隊,以確保以掃殺來時自己的家產不至于喪失殆盡。縱觀雅各的經歷,可以發現有兩個關鍵因素貫穿始終,對上帝堅定不移的信和對成為強者的不懈追求。
其背后所隱含的是猶太民族對于“強者精神”和“信者精神”的建構。首先,從客觀歷史現實的角度看,猶太民族誕生于兩河流域,這片古代文明的搖籃,但是在其出現之前這片土地上便已經繁衍出了蘇美爾、阿卡德、古巴比倫,等強盛的文明。猶太民族作為一個后進民族唯有通過自身不懈的努力克服強敵環肆的惡劣環境,才能夠生存和繁衍。于是,對于民族富強和個人強大的追求,便同他們對耶和華的信仰結合在了一起。猶太民族因信而強,因強所以更信。其次,對“信”和“強”的看重,在《圣經》敘事邏輯內也是合理的。當初人類始祖亞當、夏娃,在伊甸園中選擇吃了智慧之樹的果子,從而獲得了最接近神的智慧。而“智慧”便在人類總世代相傳。所以,在猶太人看來,“智慧”是具有神圣性的。《圣經》中所刻畫的英雄形象,雅各、摩西、約書亞、所羅門王,沒有一個不是智勇兼備,又敬愛上帝的。
二、家人關系彌合的原因不同
《左傳》中引而不發的鄭莊公,看準時機后向弟弟進攻,把他接連趕出了鄢、共二 地。面對里應外合共叔段謀反的母親姜氏,他只得“遂寘姜氏于城穎”并發下誓言“不及黃泉,無相見也。”這便是鄭莊公和共叔段二人爭斗后的悲慘結局。后來鄭莊公聽從穎谷地方官員潁考叔的建議,“闕地及泉”與母親姜氏在“大隧”之內相見,母子重歸于好。
鄭莊公最終選擇與母親相見與大隧之中,以及左丘明對他悔改認錯的肯定態度,其背后的主導因素是儒家的生命哲學。它是“一個暖烘烘的火爐,又像一個溫情的大懷抱”,要求人在面對個人欲求和家國倫理的矛盾時,必須犧牲個人的需求,以滿足家國穩定。當然這樣做雖會損害個人利益,卻能夠讓人不必游蕩于殘酷的世間,每當遭遇挫折都可以退回到“大家庭”中尋求慰藉。但與此同時其人格的獨立性也會隨之喪失,淪為儒家倫理“大家庭”中的附屬品。即便是鄭莊公也不得不面臨此種兩難境地。若要記恨于母親、弟弟,便得忍受“孤家寡人”的寂寞,并且被后斥為“不孝不友”之君。他思想出現轉變的原因,是儒家生命哲學一直所宣揚的家國倫理。
相較于《左傳》中鄭莊公和姜氏母子相見與隧中的和好方式,《圣經·創世紀》中雅各和以掃兄弟關系的復合則顯得一波三折。雅各寄居在舅舅拉班家,并全心全意地服侍了他十四年。在雅各在妻子拉結生了小兒子約瑟后,他便對舅舅說“請打發我走,叫我回到我本鄉本土去。請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兒女交給我,讓我走。我怎樣服侍你,你都知道。”從雅閣萌生返回家鄉的念頭,到兄弟二人相見冰釋前嫌,其中有兩次重要的轉折點。在這兩次轉折中上帝作為隱含的“觀察者”都起到了關鍵作用。
首先是“工價”問題。拉班因為知道雅各受到上帝的眷顧不愿將他放走,生怕自己的家業會衰落。在雅各的再三要求下,只得同意。借助上帝的啟示,雅各帶走了牲畜群中有斑點、條紋的肥壯的一批。拉班帶人追趕,上帝卻在夢中警告他不得威脅雅各,拉班無奈在追上一行人后只得佯裝送別,并與雅各立約此后互不侵犯。第二是,雅各在河邊遇見上帝的使者,并與其摔跤。擁有非凡神力的使者,雖然僅僅“摸一把”雅各的大腿根就能讓他骨折,但卻無法在角力中將他制服,結果反被雅各所鉗制。雅各逼他留下了對自己的祝福。
在《圣經》的敘事模式所形成的情感傾向和意識形態導向中,以掃是否能夠主動原諒雅各從來都不是關鍵性因素,這也是為什么故事中根本沒有描寫以掃見到弟弟派來的使者和禮物后的反應的段落。敘述者的描寫始終都集中于“選民中的選民”——雅各和他的庇佑者上帝一邊。這可以為我們揭示兄弟關系復合的原因提供一點啟示。
結語:
《左傳》“鄭伯克段于鄢”中,兄弟二人的矛盾因私心和權勢欲而起,一度致使兩兄弟都離“大家庭”而去。共叔段反叛失敗,流亡國外,鄭莊公與弟弟反目成仇后,更是與母親斷絕了關系。當鄭莊公與姜氏相見于大隧之中的時候,那個暫時被個人私欲驅使而離家出走的“浪子”又回歸了溫暖的“大懷抱”。整個故事也就變成了一場在溫暖“大家庭”中上演的內部糾紛,是一段在以現世安樂為主題的生命之樂中出現的“小插曲”。
《圣經·創世紀》中“雅各以掃相爭”情節上的關鍵轉機往往都是隱含的“觀察者”——上帝一手操縱。我們可以說上帝才是整個故事的唯一主人公,而“雅各和以掃”兄弟相爭的故事,只不過是在他的主導下上演的一場“木偶戲”。通過這場戲,《圣經》向信徒們宣揚的追求“信”、“強”,并且在這一過程中不得違背上帝旨意的意識形態目的也在潛移默化中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