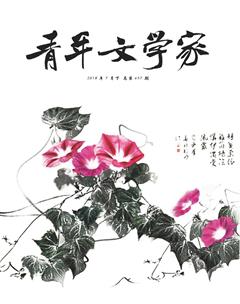心靈的光影
曹璐
摘 要:李商隱的詩在藝術的世界里登峰造極,在文學史上意義非凡,千百年來受到讀者的審美的偏愛,其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詩呈現了一個深窈緬邈的心靈世界。善感纖細的心靈特質和失意挫傷的人生體驗奠定了李商隱孤獨迷惘的心境和一往情深、傷感無奈的情感本質。他以描摹心靈的方式寫詩,他的詩是他的心靈的光影的折射。其詩詩境與心境相融,字句間折射著他本質的情感,具有如光影般幽微窈眇、變幻朦朧的美學特質。
關鍵詞:李商隱;心靈;光影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1-0-02
引言:
李商隱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重要的詩人,他在詩歌創作上取得了諸多成就,對詩歌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在所有的成就和影響中,最重要的一點莫過于他對心靈世界的挖掘和展現。
中國古典詩歌從《詩經》開始,有“詩言志”的傳統,“在心為志,發言為詩[1]”,其對心靈的表現是自然的抒發,近乎不自知的,其表現方式也是直接的,所謂“思無邪(《論語·為政》)”;到屈原《離騷》,因其志之強烈,用情之深,詩中對心靈的表現也自然加深,但仍是與情志相融的;漢魏古詩較好地沿襲“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毛詩序》)”的詩學傳統,心與物、情與景之間仍保留有“比興”之自然融合,以致“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滄浪詩話·詩評》)”[2];從漢魏以后,詩的發展走向更加精細的分化,情、辭、采、聲律等各方面分別得到更為細致和深入的發展,到盛唐達到“聲律風骨兼備[3]”的大融合,被稱為“盛唐氣象”。“盛唐氣象”是勃發的生命力的高舉,是蓬勃的心靈的力量的凝聚,是一片向外閃射、共襄盛世的光芒。而盛唐的輝煌在安史之亂后一點點消褪,詩歌作為時代最敏感的反映,其向外獲取生命力漸漸變得難以為繼,詩人只有走向自己的內心。李商隱是一個主動走向內心,有意挖掘和展現心靈世界的詩人。他的詩有時表現為純粹的對于心靈的審美和描摹,沒有明確的外物的引發,也沒有明確的感情的表達,帶有幽微窈眇、變幻朦朧的美感。漢魏及以前的詩表現心靈是與情志融為一體的,自然渾成,或天真爛漫,或堅貞不屈;漢魏以后,詩在各方面精細化深入化地發展,但其對心靈的表現的精細化和深入化可以說是在晚唐才有明顯的發展。而在之后,更為精細地表現心靈、帶有“要眇宜修[4]”之美的詞興起。李商隱的詩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做出的貢獻非同小可。在他的大多數詩中都含有對于心靈細微而深邃的描摹,通過對實有的現實、物象、典故等的虛化來達到心靈化,因而他的詩中常寫記憶、幻想、神話等遠離現實之物。另一方面,對心靈的深入挖掘也產生了對情感的深入表現。李商隱的詩呈現的是一種情感本質,沒有與志結合,是情感更為原始的狀態。它不是一種具體確切、凝聚有力的成形的感情,而是徘徊在心中不斷向外發散的情感本質,折射到詩中,帶有深情緬邈的美感。
一、從虛化看李商隱對心靈的描摹
李商隱對內在心靈的描摹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對外在現實的虛化來完成的。在他的詩里,很多地方虛化現實,包括現實中的物象、事件、人物,轉而描寫與心靈相關的感受、想象、記憶。他把向外尋求的目光探向內心,又將心靈的光影投射到所描寫的事物上,使之呈現出朦朧窈眇的境界。
李商隱詩中的意象往往不是對物象直接的選取和挪用,而經過了對物象本身的虛化和心靈化的修飾。《重過圣女祠》中“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雨和風兩個實有的意象被修飾為“夢雨”“靈風”,因而帶上一種虛渺、迷離之感,由現實中具體可感的物象變得朦朧起來,使其既指圣女祠中凄清的環境又指作者內在凄涼孤寂的心境。對物象本身進行虛化,使其與心靈相融,進而得到不斷的向內的闡發,達到幽眇朦朧的境界,因而后人稱其“有不盡之意”(呂本中《紫微詩話》)。《錦瑟》詩中“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珠有淚”與“玉生煙”都是作者想象中的意象,本身就是對現實的虛化,而“淚”因其緣由不明,“煙”因其縹緲不定,更加深了虛化。義山把對意象的描摹與對心靈的描摹融合在一起,意象上透露著心靈的光影,而心靈的幽光也借助意象得以展現,致使他的詩含有一種幽微迷人的美感。
在詩中描寫想象也是李商隱虛化現實、描摹心靈的顯著體現。《無題·紫府仙人號寶燈》以神話中的人物開頭,一開始就營造虛構性的背景,通篇描寫想象,講述追尋仙人,最終求而不得的故事。然而整個敘事中沒有出現具體的時間、地點,只有一個簡單的輪廓,可見其對具體事件的虛化。他一方面虛化具體的事件,另一方面描摹想象中的情景和心靈的微觀感覺。“云漿未飲結成冰”是他想象杯中的云漿來不及飲下、旋即結冰的情景,傳達出一種理想旋即幻滅,悵然無措的心靈感受。而“雪月交光夜”是對于天氣的想象,實則描摹的乃是心中孤寒寂寥的微觀感覺;“更在瑤臺十二層”,幻想仙人所處之地的高遠與窈眇,傳達出可望而不可即之感。整首詩極具虛構性,高度意象化,充分地表現了其幽微的心靈變化,顯得幽約迷離。又如《燕臺》詩中“此日東風自不勝,化作幽光入西海”,想象東風隨著春逝而變成幽光逝入西海。如此凄美,如此不可把捉的想象無法與現實產生明確的對應,而純粹地是復雜幽微的心靈的一種投射。那道最終無可奈何逝入西海的“幽光”其實也是他自己的生命意識的閃現,在遭遇人生挫傷之時,他的生命也是這樣,在無可奈何之中褪去生命的強力,只留下心靈的幽光和如光影般凄美的詩篇。《燕臺》詩寫于李商隱的早年,但其中隱含的生命意識卻貫穿他的一生,這也正說明他對心靈的描摹之深之細微。
此外,義山對心靈的描摹還體現在用典上。余恕誠先生曾指出“李商隱擅長對典故的內涵加以增殖和改造[5]”。這種“增殖和改造”實則是虛化典故本身的含義、而對其進行心靈上的情景再現。如《嫦娥》詩中“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用嫦娥奔月的典故,但虛化典故本身的含義,以想象的方式進行敘事。“應”字懷著對嫦娥的心境的揣測,再現了嫦娥獨自面對“碧海青天”時的夜夜孤寒,傳遞出與之相融的凄清寂寞的心境。與一般的用典不同,義山用典重在再現典故的情景,在這個過程中打通自己與主人公之間的心境,達到心靈與故事情景的融合。因為與心靈的交融,故事往往被闡發出豐富的含義,超越了典故已有的明確含義,更為深邃細微,更能引發讀者的聯想和共鳴。
二、從復沓和虛詞看李商隱詩中隱性的感情結構
復沓是常見的藝術表現手法之一,在義山的詩中被頻繁地使用。他的詩中既有句中的復沓,如“昨夜星辰昨夜風(《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無題》)”“他生未卜此生休(《馬嵬》)”“一寸相思一寸灰(《無題》)”;又有句子間的復沓,如“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夜雨寄北》)”“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春日》)”“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暮秋獨游曲江》)”。這些復沓一方面營造了回環往復的音韻美,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義山詩中一種徘徊宛轉的感情結構。《無題》中“昨夜星辰昨夜風”,仿佛記憶就徘徊在心里,揮之不去,復沓之中追憶之感一點點地浸潤開來;《馬嵬》中“他生未卜此生休”一句宛若詩人的喃喃自語,悵惘之情蟄伏其后,顯得低回婉轉;《暮秋獨游曲江》中“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在重復中層層點染,烘托出深層的悲哀;《夜雨寄北》整首詩意境混融,雖寫現在和未來兩個畫面,但在前后的復沓中兩個畫面交融在了一起,今日遙想來日,來日追憶今日,來日的相聚在今日的分別里顯得更為無望,今日的蕭瑟在來日的溫暖里顯得更為凄清,在宛轉的復沓中對朋友的思念之情更顯深摯。義山的抒情往往不是精確地一步到位、表達后有去無回的,而是在重復中層層點染、委婉曲折,以整個混融的詩境來烘托感情的。此為義山詩中一種徘徊宛轉的感情結構。
虛詞的使用也是義山的詩的一大特色,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心路的深曲宛轉和情感的深邃緬邈。他的詩中常見“如何……不(已,更)……”“縱使……可堪……”“……,只是……”這類虛詞結構,其中隱含著一種轉折的邏輯關系,使情感的表達波蕩起伏,深化了一種落空之感。虛詞中所蘊含的他的感情結構的另一種體現方式是“推進一層”。李商隱的詩中頻繁地使用虛詞“已”“更”“又”字,如《二月二日》中“新灘莫悟游人意,更作風檐夜雨聲”,“更”字在原有的基礎上加深了凄涼;《無題》中“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已”“更”連用,加強了情感的推進,把思念推向深遠乃至絕望;《柳》中“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帶斜陽又帶蟬”,“已”“又”連用,把蕭瑟的氛圍連同無奈感推向了極致;《花下醉》中“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紅燭賞殘花”,這里的“更”把傷感推向自持、自賞,傷感之外增添了一層自知的孤寂,體現了一種深情和執著。在一種感情的基礎上喚起更深的感情,在傷感中反復咀嚼、自知傷感而執著于傷感,這是義山一往而深的用情方式。繆鉞在《論李義山詩》說:“義山蓋靈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譴者,方諸囊昔,極似屈原。[6]”義山對他的心靈挖掘之深,用情之執著,他的詩中方頻繁地出現這種“推進一層”的表現方式。而此種感情方式中尚含有一份自知與自持,義山詩中最深的感傷來自“一往情深,而不能自譴”。
李商隱的詩中還有一些虛詞,與其他部分沒有邏輯的聯系,體現一種沒有緣由又極其深至的感情。如《錦瑟》中“錦瑟無端五十弦”之“無端”,看似多余且無理,實則暗含著一種無可奈何的愁緒,既不知為何而起,又不知如何安放,因而生出“無端”之辭;《燕臺·夏》中“直教銀漢墮懷中,未遣星妃鎮來去”中的“直”,含有徑直、理直氣壯之感,表明不計一切地執意要讓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發生,表露出心中偏執的深情;再如《西溪》中“人間從到海,天上莫為河”的“莫”,與上一句之間沒有明顯的邏輯關系,放在這里顯得有些無由無憑,而這種缺乏邏輯和道理的表述近似于一種質問,又含有哀求的意味,體現出無可排遣的至深之情。葉嘉瑩先生在論詩詞的時候曾說:“有的時候,在詩詞之中,是‘無理之語卻是‘至情之辭。[7]”義山用情之深,到“不能自譴”的地步,這時他已經不能再自持這份感情了,深情無措,無可奈何,散發出來即是這樣的“無理之語”。
李商隱的詩歌為歷來的讀者所偏好和模仿,但人們往往知其美而不知其所以美,致使西昆體學其皮毛、遺其骨髓,也給大多數人留下“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十二》)”的遺憾。李商隱的詩最重要的美學特質是幽微窈眇、深情緬邈,如光影般難以把捉,而這種特質本質上來自其對心靈的挖掘和描摹。李商隱的詩是他的心靈的光影的折射。
注釋:
[1]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明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09.
[2](南宋)嚴羽《滄浪詩話》,中華書局,2014.04.
[3]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教育出版社,1996.
[4]王國維《人間詞話》,中華書局,2015-06-01.
[5]余恕誠《李商隱詩歌的多義性及其對心靈世界的表現——兼談李詩研究的方法問題》,《文學遺產》,1997(2).
[6]繆鉞《詩詞散論》,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05.
[7]參見葉嘉瑩《唐宋詞十七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