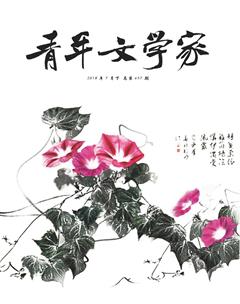文化歸途
摘 要:以塞義德的東方主義為理論基礎,美籍華裔作家譚恩美的《喜福會》為文本,從東方主義視角出發,重新解讀譚恩美小說,通過其反東方主義元素以及其展現方式,提出譚恩美并不是在迎合東方主義,而是通過正視東方主義解構東方主義并獲得文化身份的真實回歸。
關鍵詞:譚恩美;《喜福會》;反東方主義;文化身份
作者簡介:項聿培(1996-),女,江蘇常州人,南昌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文學專業本科生。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1--02
1989年,譚恩美出版了第一步長篇小說《喜福會》,該作品通過講述四位中國母親與他們各自的女兒通過誤解、產生沖突最后獲得理解的故事。縱觀近幾年主流讀者對《喜福會》的評論,大多是開始從東方主義,后殖民主義與他者的角度進行解讀,然而筆者發現,這些解讀都重點落于闡述《喜福會》如何建構了東方主義,而并沒有關注譚恩美在消解東方主義上做出的貢獻。本文從東方主義的視角出發,解讀了譚恩美在小說中如何展現其反東方主義情結,進而提出了只有正視東方 主義與歷史,才能對其進行解構,獲得真正意義上文化身份的回歸。
1.塞義德“東方主義”
著名文學評論家薩義德在二戰后提出的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中,使用了東方主義的觀點作為其核心思想,“東方”并不只是地域上、人種上與“西方”的區別,更是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性,一種思維方式上東西方之間的徹底對立。東方主義是一種對東方人的錯誤而僵化的描述,即東方人是異常的野蠻的。這種文化與政治的優越性滿足了西方對控制東方,凌駕于東方的病態心理,將東方歸結為低人一等的“沉默愚鈍者”形象,東方人通常被描述為沉默者和他者。東方主義顯示西方通過將東方歸于低等的他者并強化西方自身的優越性來實現其霸權。[1]
2.正視歷史 與東方主義存在
賽義德曾指出:“在討論東方之時,東方是完全缺席的,人們感到出席的只是東方主義者和他的言論;然而,我們不應忘記的是,東方主義者的出席恰恰是由東方的實際缺席造成的。”[2]實際上,縱觀譚恩美的《喜福會》,我們都能看到真實的東方者的存在,正是這些東方者的訴說讓我們了解到了真實的歷史。
2.1正視歷史,出席歷史
人們傾向于了解那些我們愿意了解的事物,因此在閱讀《喜福會》時許多讀者認為譚恩美筆下迷信、血腥的中國并不是真實的中國,是對于中國的丑化,為了迎合東方主義的高高在上的文化優越感,然而四位母親的故事發生在解放前 ,當時的中國,雖然思潮涌現,然而迷信仍然是人們心上抹不去的陰影,魯迅先生也曾反映過當時的人們食用“人血饅頭”治病的可怕現實[3],一味地否定 無法解決問題,這些令人讀起來產生不適的文字卻恰恰反映了真實的中國,將其歸結為“滿足東方主義”,實際上是武斷的。直視真實的歷史或許會令人痛苦,但能讓我們看清過去,而非盲目自信。母親們對過去故事的敘述,正是愿意直視傷民族之殤的體現。長期無視傷口并不能從根本上治愈,只能愈發使自身深陷于自卑與痛苦中,正如《喜福會》中的映映選擇丟失過去的自己直視使她感到迷失和困惑,最終勇敢地站出來 “現在,我該把這一切也告訴我女兒。”[4]225讓她走出痛苦,清醒過來,重塑了自我。
2.2正視東方主義的存在并進行解構
許多“華裔作家,感受到民族強大的重要性,從而從自己的良知出發,竭力維護華人形象,強調并宣傳正宗的中國文化經典,來解構西方的‘東方主義意識形態。”[5]譚恩美正是其中之一。她實際上意識到了“東方主義”的存在,并想要進行合理的解構。小說中的女兒們在美國出生,在美國生長,深受美國社會對東方的認識的影響,這種意識形態對她們的作用是潛移默化的,譚恩美借用女兒們對于母親的不理解,甚至是鄙夷,展現了當時日益強盛的“東方主義”。小說中的女兒們西方文化身份看待東方,對中國文化理解片面,帶有偏見,實際上正是西方文化的“東方主義”在作怪,作者借由母親們在沖突中的無奈與痛苦,展現了這種東方主義帶來的負面作用,實際上體現了作者對中國的維護。
2.3民族身份的回歸
《喜福會》的設定是在麻將桌邊,四個母親輪流做東,輪流講述自己的故事,這些回憶性質的故事讓女兒們了解到了過去,這不僅是她們母親的過去,更是中國的沉重的歷史。這種述說,一方面是母親們獲得了自身民族身份的回歸,他們通過講述這些故事,正式了自身的傷痛。通過幼年時的孩子們無法理解,產生了對于中國的錯誤理解,然而隨著她們慢慢長大,逐漸意識到這正是她們無法割舍的民族記憶,是她們的民族身份。“兩首曲子,其實是同一個主題的變奏。”[6]25當君終于認祖尋親,找到兩位姐姐時,她終于意識到她身上的中國身份是不需要由別人來認同的,那是刻在他們骨子上,流淌在血液里的,這體現了民族身份的真正回歸。譚恩美并不是迎合“東方主義”,而是借此體現對于自身民族身份的逐漸認同,一蹴而就的認同是不切合實際的,這種逐漸的醒悟才更為流暢自然。母親們讓身處西方文化身份中的女兒們了解到了中國的真相,雖然它迷信、甚至殘忍,但是同時也傳遞著母親們的信仰與美好的愿望。
3.展現反抗精神,絕非沉默
長久以來,沉默成為東方主義對華人刻板化描寫的一個重要特征。華人女性沒有說話權是一種民族和性別上雙重的他者形象,長期失語使她們只能依附于他們來表現自己,然而我們看到,在《喜福會》中,這些女性沒有選擇讓他人來替自己發聲,扭曲自身形象,而是勇敢積極的站了出來,或作出反抗,或大膽發聲,有些反抗的形式或許受困于時代因素,但已經是女性精神的重大突破,完全有別于過去“東方主義”對華人女性的刻板描述。
小說中的母親一方面頑強地反抗自身命運,雖然由于受困于時代與環境因素,或許仍然會體現當時中國的迷信,但是相較于被動等待,不做反抗已經是華人女性形象的重大突破。小說中,琳達成功地利用智慧與觀察,積極主動地把握住了自己的命運,從她第一次的婚姻中逃脫出來,最終解除了婚約,決不讓自己成為封建婚約的犧牲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我終于醒悟了,發現了一個真正的 自我,并任憑著這個‘我的思想來帶領自己。這種對婦女“沉默”狀態的成功突破,是對長期以來東方主義的駁斥與解構。另一方面積極主動站出來,不再沉默,消除與女兒的矛盾與誤會,鼓勵引導著女兒們追尋真正的幸福。麗娜的丈夫自私自利,明明領著比自己妻子要高八倍的工資,卻還要和她什么都均分,哪怕是麗娜并不愛吃的冰激凌,麗娜的母親映映便打碎花瓶,以此來開導她頑強地站出來,不要畏懼。小說中的華人女性不再是以往東方主義所認為的沉默隱忍的形象,而是主動站出來勇敢的追尋自己幸福的表現。
4.展現真實中國,不迎合東方主義
在小說的最后,君回到了中國,譚恩美借君的雙眼與描述展現了一個與東方主義構建下完全不同的中國,“出租車在一幢豪華的、比希爾頓還要華貴的建筑前停下。‘這里是共產黨中國嗎?我驚奇地差點叫了出來……真闊氣!只見一個穿著筆挺制服的侍應生,奔過來把我們的行李搬進大廳里,只見大廳四周都是花崗巖和亮晃晃的鏡子,金碧輝煌。”譚恩美終于無法克制其民族自豪感,用直白的話語展現了真正的中國,一個文明先進,經濟獨立的中國,一個不是東方主義視角里野蠻骯臟的中國。
5、結論
譚恩美的《喜福會》并不是對于東方主義的盲目迎合,她展現了真實的令人心痛的中國過去的形象,意在令我們不忘歷史,牢記歷史;同時通過對第二代美籍華裔移民與第一代移民的沖突真實再現了東方主義思想形態與發展中成長中的真實中國的沖突。這有力地沖擊了一直高高在上的西方霸權文化,粉碎了西方人心中的所謂文化優越感,譚恩美將真實的中國文化引向世界,不藏不遮,既自豪于中國目前的優秀,也不因痛苦的過去而自卑,她將西方人帶著東方主義的有色眼鏡看中國人具象化并成功解構,粉碎了西方人固有的東方主義,還中國文化一個清白,獲得了真正意義上文化身份的回歸。
參考文獻:
[1]揣瓊.《喜福會》中的東方主義[J].英語廣場(下旬刊),2014,(7):58-59.
[2]愛德華 · 賽義德. 東方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28-30
[3]魯迅,吶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31-42
[4]譚恩美.喜福會[M].程乃珊,嚴映薇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5]沈琳.《喜福會》中的文化內涵及其對"東方主義"的解構[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6):78-79.
[6]陳茗,聶靖.雙重身份下的雙重寫作——論《喜福會》中的東方主義元素與反東方主義元素[J].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1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