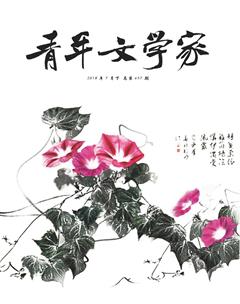電影符號學視閾下姜文影片解讀
趙雅馨 魏子賀
摘 要:克里斯蒂安·麥茨提出的電影符號學是現代電影理論成熟的標志之一,而大陸導演姜文的影片,無論是在麥茨第一電影符號學視域下的敘事和視聽風格等電影語言方面,還是在第二電影符號學視域下對于個人的成長,英雄的政治理想還是國民性的批判與反思等深層內涵方面,都表現出了導演的天才創作力。因此,本文以姜文的影片為研究對象,探究其符號學特征。
關鍵詞:姜文電影;克里斯蒂安·麥茨;電影符號學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1--02
一、克里斯蒂安·麥茨的“電影符號學”的發展及意義闡釋
電影符號學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麥茨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為藍本,在1964年發表了《電影語言系統還是語言》,標志著電影第一符號學的誕生,它包含三大研究范疇:(1)確定電影符號學的性質;(2)劃分電影符碼的類別;(3)分析電影作品——影片文本的敘事結構,即電影語言的系統研究。它的基本觀念是:電影是具有約定性的符號系統,它的創作有可循的社會公認的程式,雖然電影語言不等同于自然語言,但電影符號系統與語言符號系統本質相似,其研究重點則應當是外延與敘事。第二電影符號學是以麥茨1975年發表的《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與電影》為標志,是電影符號學與精神分析學相結合的產物。它以精神分析為模式,全面解釋了觀影主體觀看過程和創作主體創作過程以及表演主體表演過程的心理學。
二、第一符號學視域下的姜文影片解讀
(一)敘事:錯亂中的有序人生
《陽光燦爛的日子》全片采用平敘的敘事手法,圍繞馬小軍的個人成長展開敘述,故事雖然發生在文革期間,但導演卻將鏡頭對準人性,記錄著一代人成長的酸甜苦辣。打群架、談戀愛,看電影成為那些孩子的日常生活,通過這些零碎的小事,導演向觀眾展示了那個時代的人生經歷。相比《陽光燦爛的日子》,《讓子彈飛》的敘事更為流暢,快速的剪輯和幽默的語言,使這部長達140 分鐘的電影完成藝術創造的同時,又成功的走上了商業片的道路。《鬼子來了》這部故事片并不是全片采用平敘的手法,馬大三對于“我”的到來的回憶,對于不敢殺死花屋小三郎,而把他們藏起來的述說,運用了插敘的手法。平敘為主,插敘為輔的敘事策略,使故事構成更加完整。《一步之遙》整體上依然平敘的敘事手法,圍繞“花域大選”和“槍斃馬走日”兩部分展開。但在此片中,倒敘和插敘的聯合使用,使得該影片在敘事策略上別具一格。《太陽照常升起》一反經典敘事,采用組合化、片段化的非線性敘事手法。圍繞“瘋”、“戀”、“槍”、“夢”四個段落來完成敘事,將整個故事的源頭——小隊長的出生放在了最后,前置的三部分一直暗含的死亡,后置的一部分——誕生,這種敘事順序不僅很好營造出一種懸念感,更產生了一種敘事跳躍的效果,給接受主體帶來很大的觸動和震撼,同時也使得影片的視聽表現力和藝術效果大大加強。
(二)視聽語言:夢境般的自我顛覆
1.夢幻般的色彩鋪陳
著名攝影師斯托拉羅曾經說過:“色彩是電影語言的一部分,我們使用色彩表達不同的情感和感受,就像運用光與影象征生與死的沖突一樣”。[1]《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導演極力的抓住“燦爛”的要義。大量的陽光直射鏡頭造成了畫面的朦朧感,馬小軍春心萌動,在米蘭房間,視覺效果均處理為暖色,伴隨陽光的攝入,營造著一種夢幻般的畫面,這也正是馬小軍內心世界的體現,鮮紅的內衣,碧藍的泳池,明媚的眸子,這些細節的渲染,凸顯了影片“ 燦爛”的視覺效果。相比之前的兩部影片,步入成熟之后的《太陽照常升起》、《讓子彈飛》對于色彩的處理更加濃重,給接受者的感覺已經不僅僅是“燦爛”而達到了“熾熱”的地步。這種飽和的顏色,深深這烙下了作者的痕跡。如《太陽照常升起》火紅的魚鞋躺在滿是紅花綠草的軌道上,五彩鳥在樹上高飛,高原鄉村的“紅土”,戈壁灘上的白駝,都為影片視覺效果的傳達增加了一抹亮色,同時為主題的表達提供了助力。
2.富有張力的音樂格調
《太陽照常升起》中音樂的美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音樂大師久石來給電影做原聲音樂。在電影中,梁老師的吉他彈唱《梭羅河》作為連接“瘋”和“戀”的轉場音樂,充滿著異域風情,也唱出了一種對于自由地渴望。影片伊始和瘋媽去邊境尋找愛人時異域風情的音樂,不僅契合影片浪漫的風格,并且為畫面涂上了一抹瑰麗色彩。同樣是異域風情的音樂,《一步之遙》不僅頻頻向經典影片致敬,并且開始走向國際化,《蘇爾維格之歌》、《羅門湖》、《我親愛的爸爸》,《茶花女》中的經典曲目《祝酒歌》等等,伴隨著音樂元素的融入,不僅體現著影片中人物的性格特征,標明人物的身份,同時也體現著導演對于演唱者的態度。武大帥與俄羅斯女子結婚時,當眾高歌《祝酒歌》,滑稽可笑,體現著導演對于這種權力聯姻的深惡痛絕。
三、第二符號學視域下姜文影片的解讀
(一)成長的傷痛與追憶
弗洛伊德認為,夢的意義就是愿望的實現或者說是欲望的達成。因此可以說人生體驗和生活感悟,會在潛移默化中對藝術家的創作,產生重要的影響,而在這些影響中,童年的經驗,影響尤其深刻。
小隊長可以理解為進入俄狄浦斯階段時遭遇的致命挫折與傷害。小隊長從一出生就沒有父親,對父親的印象只有一桿槍和母親的一張沒有臉的合影以及阿廖沙等一些零碎的符號,這些完全不能構成“父之名”和“父之法”的權威,而越是匱乏就越是有欲望,當唐叔帶著一把槍和一個成熟的女人到來的時候,他立刻把對母親的傷痛轉移到對那把槍上,迅速地把對于母親的認可轉變為對父親的認可,忙著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抓住機會與唐嬸偷情,但遺憾的是這種轉變只是小隊長為自己的快速成長建造的空中樓閣,始終沒有對于“父之名”,“父之法”的認可,沒有完全的戰勝俄狄浦斯情結。相比之下,馬小軍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的童年時期,父親雖也不總在身邊,但他的父親作為一名戰斗英雄,在馬小軍的內心深處是極其認可的,并且馬小軍也幻想著自己可以出生在戰爭年代,成為戰斗英雄,“父之名”得到了認可,而對于母親的依戀,在影片中是完全沒有體現,可見馬小軍已經成功地度過了俄狄浦斯階段,因此馬小軍的童年時光是陽光燦爛的。
(二)英雄的彷徨與吶喊
弗洛伊德視藝術為一種白日夢,根據他的夢的理論,藝術內容實際上是將藝術的意義翻譯成另一種更為隱晦和陌生的形式,這種翻譯的過程是通過凝縮、置換、具象化和二次加工的手段將無意識的隱意轉變為可感知的顯意的過程,想要探解影片的深層無意識,就是破解其象征含義,進行解碼的過程。[2]
《讓子彈飛》中的張牧之是曾經追隨過蔡鍔將軍的手槍隊長,革命的果實被竊取之后,成為了落草為寇的張麻子,劫持馬邦德之后,搖身一變做了縣長,無論是作為革命者、土匪還是縣長,張牧之的理想都是為了實現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所以說張牧之其背后所指的是革命先烈。有革命者就必然有要被革命的對象,影片中的黃四郎是鵝城的土老爺,身邊還有著胡百、胡千、胡萬以及武教頭等一系列狼狽為奸者,他們象征著剝削階級,舊勢力舊思想。在這場斗爭中勝利后那些和張牧之共同斗爭過的兄弟,在革命勝利之后,駕著和馬邦德一樣走馬上任時的馬拉火車去了上海,紛紛離開了他,試想這些人去浦東做什么,他們是革命的勝利者,而此時的他們想去做什么,想去成為第二個馬邦德還是黃四郎呢?夕陽下,蒼鷹在天際劃過,孤獨的長鳴,張牧之迷茫地駕著一匹白馬,徐徐前行,此時的張牧之是彷徨的,雖然他戰勝了黃四郎,還了鵝城百姓公平,可天下還有康城,還有浦東……理想的社會何時才能真的成為現實呢?
無論是從第一電影符號學的視域下分析姜文影片的敘事和視聽語言,還是從第二電影符號學的視域下分析姜文影片所要滲透的深層內涵,都可以看出他獨立于旁人的天才創造力和哲人的思辨能力。姜文憑借對藝術的純粹信仰和獨特的氣質在中國電影界樹立起了一面專屬于自己的旗幟,并召喚著更多的電影人在題材和類型上為了突破“商業模式”的桎梏而繼續努力,同時希望沉睡的國人可以運用智慧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品評歷史,感悟生活,提高審美能力,真正完成思想上的成熟與飛躍。
注釋:
[1]王云《試論色彩與電影藝術的關系》,《理論觀察》2008 年第 6 期,第 3 頁。
[2]【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引論》,北京:北京出版社,張堂會譯,2007年版,第88頁。
參考文獻:
[1]韓笑《姜文電影的美學探究》,《電影評介》2012年第14期。
[2]【法】克里斯蒂安·麥茨 《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與電影》,北京:中國廣播電視
[3]馬睿、吳迎君 《電影符號學教程》,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