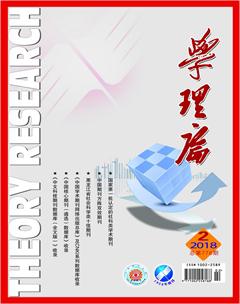馬克思的生態(tài)思想及其當代啟示
韓秀霜
摘 要: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是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之上的。自然史與人類史不可分割,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相互制約。人與自然的關系受到社會生產(chǎn)方式的制約,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方式造成了人與自然的尖銳對立。人與自然的矛盾的解決既要建立在人類對自然規(guī)律的認識和把握的基礎上,又要建立在消除人與人的對立關系的實踐基礎上。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危機,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我們,必須尋找建設解決環(huán)境問題的突破口,真正落實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科學發(fā)展觀和生態(tài)文明理念。
關鍵詞:馬克思;生態(tài);實踐;自然觀;生態(tài)文明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2-0031-03
近代以來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引發(fā)了人們對于這一問題的無限深思。關于人與自然矛盾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理論界產(chǎn)生了一個又一個頗具分析力和影響力的論斷,如人類中心主義批判、民主缺失論、市場失靈論等等。這些理論都在某個角度或者某種程度上解釋了人與自然矛盾的原因。國內外也有不少學者研究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觀、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關系理論、資本主義經(jīng)濟危機理論等。概括來看,這些理論分析主要是強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受到社會的制約,將生態(tài)危機的根源歸之為資本主義制度。這種分析在解釋當代環(huán)境問題方面是深刻的。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深刻洞見了人與自然矛盾對立的根源,今天看來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
一、馬克思的生態(tài)思想
馬克思并沒有專門、系統(tǒng)論述生態(tài)問題,但是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視角理解生態(tài)問題給人以深刻的啟發(fā)。馬克思的生態(tài)思想為透視當今生態(tài)環(huán)境危機提供了一種獨到的視角,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生態(tài)觀,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造成了人與自然的尖銳對立,只有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實現(xiàn)社會主義理想,才能從根本上實現(xiàn)人與人的和解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解。
1.實踐基礎上的人與自然、自然史與人類史
馬恩承認自然界的客觀實在性,自然界先于人類社會而存在,是人類實踐活動的前提。但馬恩從不抽象談論自然界,他們更重視的是進入人類認識和實踐活動領域的自然界,因為人類實踐活動領域以外的自然界,對人來說是無意義的。從實踐出發(fā)來理解和把握周圍世界,把世界看作一個現(xiàn)實的世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特征之一。①在實踐基礎上,人與自然形成了對象性的關系。人把自然界作為自己實踐的對象,人在實踐活動中全面地占有自然界。反過來說,自然界通過人的活動獲得新的形態(tài),自然界通過人來實現(xiàn)自身從自在自然向自為自然的轉化,從而獲得屬人的性質。在實踐基礎上,自然史與人類史不可分割、相互制約。歷史發(fā)源于人類的物質生產(chǎn)活動,在這一過程中,人類把自然納入自身實踐的過程;自然在人類生產(chǎn)實踐中體現(xiàn)自身的現(xiàn)實性。因此馬克思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1]196。馬克思始終強調實踐“是整個現(xiàn)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他批判費爾巴哈離開實踐談論周圍世界的觀點,還批判那種脫離實踐的歷史觀。
實踐基礎上人與自然、自然史與人類史的這種關系說明,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自然也不是人的主宰,自然規(guī)律與人類實踐相互制約。人類實踐活動必然不斷擴展延伸到原本“無人”的自然界,自然規(guī)律必然對人類實踐活動中“超自然”力量的運用加以制約。恩格斯的話絕好地闡明了這一點,他說“只有人能夠做到給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記,因為他們不僅遷移動植物,而且也改變了他們的居住地的面貌、氣候,甚至還改變了動植物本身,以致他們的活動的結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滅亡一起消失”[2]421,因而“隨同人,我們進入了歷史”;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2]560。
2.人與自然的關系受到社會生產(chǎn)方式的制約
人與自然的關系受到社會生產(chǎn)方式的制約。“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chǎn)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fā)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這里所說的個人是“現(xiàn)實中的個人”,這些個人是從事改造自然的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chǎn)的個人,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人與自然關系中的“人”是社會中的人,因此人與自然的關系必須納入社會中去考慮。正如馬克思所說:“社會是人同自然界地完成了的本質的統(tǒng)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xiàn)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地實現(xiàn)了的人道主義。”[1]187人與自然關系中的“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是以生產(chǎn)關系為基礎的種種社會關系的總和,每一個人都是這種社會關系的一個交織點。因此,人與自然關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會生產(chǎn)方式的制約。
3.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造成了人與自然的尖銳對立
從資本主義社會在歷史上的積極意義上說,人類改造自然實踐活動范圍和活動能力大幅度提高,特別是當生產(chǎn)和科技相結合,生產(chǎn)成果和社會財富急速增多。人與自然之間廣泛的對象性關系促進人與人之間形成了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人與人之間越來越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反過來也促進人與自然之間形成更廣泛的對象性關系。從資本主義社會在歷史上的消極意義上說,單個人只有在擁有貨幣的情況下,才可以使自身不必依附于他人,并在一定限度內獨立地、自由地用貨幣去交換任何商品。因此人人都想盡可能多地得到貨幣和財富,人與人之間也就展開了剝削工人的競爭、引誘消費的競爭等。這一過程中人與人的對立同時也必然加深人和自然的對立,自然日益成為資本家在競爭中試圖控制和征服的對象。
資本家生產(chǎn)的目的只是為了獲取盡可能多的利潤,自然界的利益不在他們考慮范圍之內。恩格斯指出銷售時可獲得的利潤是資本家唯一的動力,“西班牙的種植場主曾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以為木灰作為肥料足夠最能盈利的咖啡樹施用一個世代之久,至于后來熱帶的傾盆大雨會沖掉毫無掩護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巖石,這同他們又有什么相干呢?”[2]562馬克思則指出,資本主義生產(chǎn)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使人的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破壞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馬克思洞悉,資本主義工業(yè)化的發(fā)展是通過剝奪農(nóng)民發(fā)展起來的,這一過程給城市和鄉(xiāng)村帶來了自然環(huán)境破壞。
資本家剝削工人,工人則被擠進惡劣自然環(huán)境。工人創(chuàng)造的財富日益增多,工人生活環(huán)境卻日益惡劣。馬克思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甚至對新鮮空氣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而且工人還不如從前住在洞穴中的野人,野人住在洞穴中感到如同魚兒在水中那樣自在,因為”他每天都可能被趕走。他必須為這停尸房支付租金”。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也對此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揭露,大批窮人被吸引到大城市里來,卻被擠進一個狹小的空間;他們呼吸的空氣“比他們的故鄉(xiāng)——農(nóng)村污濁的多”;他們用的水是被污染了的河水,因為“自來水管只有出錢才能安裝”;他們把所有垃圾都扔在大街上,因為“沒有任何別的辦法處理這些東西”。
4.只有共產(chǎn)主義社會才能實現(xiàn)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
以“人的依賴關系”為特征的社會里,人類深受自然界擺布。以“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為特征的社會里,大工業(yè)的發(fā)展使得人類具有降服自然的能力,但是資本破壞了自然,工人則深受資本、自然的雙重奴役和壓迫。沒有人對自然規(guī)律的充分把握,人只能臣服于自然界,屈從于共同體;沒有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和解,就必然存在階級利益和人類共同利益的對立,就必然有人故意違背自然規(guī)律。人與自然的矛盾的解決既要建立在人類對自然規(guī)律的認識和把握的基礎上,又要建立在消除人與人的對立關系的實踐基礎上。
當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越來越阻礙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新的社會形態(tài)的出現(xiàn)也就越來越近。當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的矛盾、人與自然的矛盾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以經(jīng)濟危機和生態(tài)危機的形式爆發(fā)出來,直到這種“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社會的消亡。伴隨著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能力的空前發(fā)展,人類第三個社會形態(tài)終將到來,這一社會形態(tài)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fā)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chǎn)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基礎上的自由個性”,也就是共產(chǎn)主義社會。人類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深度和廣度空前提高,生產(chǎn)產(chǎn)品極大豐富,私有財產(chǎn)和異化勞動被揚棄,人與自然都得到解放,人獲得自由全面發(fā)展。共產(chǎn)主義社會一是生產(chǎn)力高度發(fā)達;二是消滅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xiàn)象,因此能夠實現(xiàn)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用馬克思的話說,共產(chǎn)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1]185用恩格斯的話說,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chǎn)資料“人才在一定意義上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tǒng)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xiàn)在卻受到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jīng)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2]300
二、馬克思的生態(tài)思想對中國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啟示
生態(tài)文明是對工業(yè)文明的超越,是一種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特征的高級的人類文明形態(tài);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超越,是以實現(xiàn)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解為目的的一種更為美好的社會理想。生態(tài)文明與社會主義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然而,“生態(tài)文明必然是社會主義的”這一論斷遭遇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之一就是,變革資本主義、實現(xiàn)生態(tài)社會主義的主體力量不是越來越強大,而是越來越復雜化和弱化。拋開這一點不說,即使是在已經(jīng)實現(xiàn)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其生態(tài)化的進程也明顯滯后于資本主義國家。由于資本主義生產(chǎn)的盲目性,西方發(fā)達國家在分享工業(yè)文明帶來的物質繁榮的同時,也不得不承受工業(yè)化造成的環(huán)境惡化。于是發(fā)達國家率先反思過去,20世紀70年代初,在一些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興起了環(huán)境保護運動,提出可持續(xù)發(fā)展理論和生態(tài)現(xiàn)代化理論等。發(fā)達國家憑借自身經(jīng)濟優(yōu)勢,通過嚴格的環(huán)境保護立法、最新的環(huán)保科學技術以及將污染轉移到發(fā)展中國家等各種手段,實現(xiàn)了環(huán)境“局部有所改善”。因此,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危機,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我們,必須尋找建設生態(tài)文明的突破口。
工業(yè)發(fā)達國家也曾吃盡了工業(yè)污染的苦頭,倫敦的濃霧曾經(jīng)比今天北京的霧霾還要具有殺傷力,日本四日市重金屬微粒與二氧化硫形成硫酸煙霧曾使哮喘病驟增。工業(yè)發(fā)達國家治理污染有方,他們通過資金、技術、對外污染轉移等途徑再次實現(xiàn)了天藍水綠。中國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的資金和技術投入是逐步增多的,但遠遠不夠。中國也不可能走對外污染轉移這條路。地球村已經(jīng)千瘡百孔,牽一發(fā)而動全身,溫室效應傷害的將是全世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將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希望寄托于自我的內在約束,倡導符合生態(tài)原則的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令人感到有希望的是,符合生態(tài)原則的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所構成發(fā)展的內涵并不意味著貧瘠,恰恰相反,這種發(fā)展可以具有更豐富的意義。這種發(fā)展倡導人們在不壓迫大自然的生命的前提下,約束自身的物質需求,增強自身的精神需求,過一種不是物欲橫流但是更富有內容的生活。然而這種意義上的發(fā)展對于每一個人來說并不意味著物質財富的驟增,但它意味著生命內容的豐富。因此在當前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具備一定基礎之時,我們不應當僅僅強調經(jīng)濟建設,不應當強調單純的物質財富的增長,甚至不應當只是追求國富民強,而是追求建立在每一個人生命內容豐富的基礎上的國家進步。當人們不再把追求物質財富看得如此重要,國家和民族才可能不是一架異化了的機器,而是更具活力的生命聯(lián)合體,備受摧殘的大自然才有機會得以喘息,生態(tài)文明建設才更加有希望。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許廣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