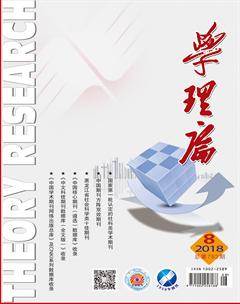習近平青年觀探析
喻金倫 鄧雨珠
摘 要:習近平的青年觀是馬克思主義青年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的青年觀內涵豐富、思想深刻、影響深遠,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對當代我國青年的成長成才和青年工作的開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深入學習習近平的青年觀,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關鍵詞:習近平;青年;青年工作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8-0013-02
青年是祖國的明天和未來,承載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夢想和希望。重視青年,贏得青年,重用青年,一直以來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政治優勢和優良傳統。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在社會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會、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聯合國青年論壇等多個場合發表了許多關于青年的重要講話,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青年及青年工作做出了許多重要指示,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青年觀。習近平的青年觀,是對馬克思主義青年思想繼承和發展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我國青年工作的理論依據和行動綱領。習近平的青年觀,為新形勢下我國青年教育“培養什么樣的青年、如何培養青年、為誰培養青年”等問題指明了方向,對于我國青年的成長成才以及青年工作的開展具有重大意義。
一、習近平青年觀的主要內容
習近平青年觀的形成,離不開習近平對青年清晰而又準確的歷史定位。習近平的青年觀,既蘊含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馬克思主義青年理論,也繼承和開拓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中關于青年的重要思想。習近平的青年觀深刻揭示了青年成長過程中的本質規律和特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青年的時代使命做出了重要論斷,具體而言有如下三個方面。
1.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也是黨的未來和希望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生力軍和后備力量。習近平強調:“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也是我們黨的未來和希望。”[1]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青年是國家進步發展過程中一股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也是民族繁榮昌盛進程中重要的依靠對象。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青年黨員就扮演了重要角色,發揮了重大作用。黨一直以來就十分重視青年及青年工作,積極努力地爭取贏得青年的信任,并對青年委以重任,把青年作為黨的得力助手,將青年作為黨和國家事業后繼有人的重要保障。同時,青年又是值得信賴、大有可為的一代。習近平曾說過:“國家的前途是當代中國青年必須和必將承擔的重任。”[2]青年是富有青春夢想而又朝氣蓬勃的,他們充滿活力,創造性十足。因此必須對青年加以正確的價值觀引導,讓青年心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定其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讓青年成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磅礴青春力量。
2.青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生力軍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夢”的本質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中國夢”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夢想,是中華民族每一個民族的夢想,也是每一位中國青年的夢想。無論是在近代反侵略反封建的斗爭時期,還是現當代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廣大青年都勇于為了“中國夢”無懼危險和困難,揮灑了自己寶貴的青春與熱血,體現了青年無比崇高的歷史責任感和時代擔當精神。對此,習近平曾著重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終將在廣大青年的接力奮斗中變為現實。”[3]青年是飽含青春夢想的一個群體,而青年的青春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有許多共通之處,二者相互依存,相輔相成:青年青春夢的實現有賴于“中國夢”的實現,“中國夢”的實現為青年青春夢的實現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和支撐條件;青年的青春夢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每一個青年青春夢的實現都為“中國夢”的早日實現提供了催人奮進的強大精神動力。“中國夢”是當代中國青年運動的時代主題。因此,青年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青年要具有時代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為早日實現“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3.青年是中外友好交往的橋梁
青年不僅對我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促進中外國際交流與合作的舞臺上扮演著重要角色。青年人大都開朗活潑、風趣幽默、意氣相投,互相之間很容易找到共同話題打成一片,從而成為朋友結下深厚的友誼。青年的友誼是純真而珍貴的,中國青年在同世界各國青年交流交往的過程中,促進了中外文化、經濟、政治等多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正因為青年是中外友好交往的橋梁,習近平時常鼓勵和勉勵中外青年之間的友好互動,讓中國青年積極主動做中外和平友好事業的促進者和建設者。2015年4月,在同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會談時,習近平指出:“‘國之交在于民相親,而‘民相親要從青年做起。”[4]各國青年之間的交流是國與國關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在各國青年互相之間充分溝通和交流的前提下,才能帶動各國民眾之間的認識和了解,從而逐步消除互相之間的誤會與隔閡,增進國家之間的友誼與合作。除了國與國之間,在談及中國與廣大非洲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時,習近平在非洲的坦桑尼亞發表的演講中強調:“中非關系是面向未來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非有志青年共同接續奮斗。雙方應該積極推動青年交流,使中非友好事業后繼有人,永葆青春和活力。”[5]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不斷加大,各國間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作為中外友好交流的重要橋梁,青年要提高自身綜合素質,在互相學習和借鑒的基礎上促進中外關系的健康發展,做中外關系的繼承者、參與者和貢獻者。
二、習近平青年觀的當代啟示
1.堅持和加強黨對青年及青年工作的領導
歷史和現實已經多次證明,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才能實現民族解放、國家獨立、人民幸福。黨的十九大已經明確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6]青年是單純而又稚嫩的,青年時期是人生三觀形成和確立的關鍵時期,而青年的三觀決定了整個中華民族未來的價值取向。未來屬于青年,青年的成長成才事關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和進程,且青年是黨十分重要的后備力量和得力助手,因此,堅持和加強黨對青年及青年工作的領導是習近平青年觀的題中應有之義。堅持黨對青年及青年工作的領導,就是要求青年永遠跟著黨走,堅持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堅決執行黨的意志和決議。只有堅持黨的領導,青年才能朝著正確的方向成長成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薪火相傳。加強黨對青年及青年工作的領導,就是要根據當今時代發展的特點和青年成長的規律,有目的、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做好青年工作,為青年的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氛圍和條件,為青年的鍛煉和出彩創造良好社會機遇和舞臺。學習和貫徹習近平關于青年及青年工作的重要講話精神,黨和社會要更加關心青年、服務青年、重用青年,努力將廣大青年培養成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
2.明確共青團工作的根本原則和行動指南
青年是一個富有青春活力的群體,而共青團是黨領導下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是黨和政府聯系青年的紐帶和橋梁,因此共青團是一個飽含朝氣和創造性的進步青年組織。共青團作為黨的生力軍和突擊隊,一直以來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走在時代的前列。習近平在同團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座談時強調:“青年在哪里,團組織就建在哪里;青年有什么需求,團組織就要開展有針對性的工作,努力使團組織成為聯系和服務青年的堅強堡壘。”[7]堅定的政治性,是共青團作為戰斗堡壘的靈魂所在。共青團必須要一心跟黨走,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這是共青團工作的根本原則。同時,共青團要以正確引領青年的思想為行動指南,在工作中要堅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引導廣大青年牢牢樹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自覺為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服務。習近平對于共青團工作根本原則和行動指南的明確,是共青團準確把握青年時代脈搏,引導青年堅定理想信念,提高共青團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法寶。
3.青年要努力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和能力
青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是“中國夢”實現的實踐者。因此,青年身上肩負著時代的重任,任重而道遠。打鐵必須自身硬,青年想要擔當重任,除了要具備正確的價值觀導向,還必須努力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和能力。學習是提升綜合素質的階梯,實踐是提高能力的途徑。一方面,廣大青年要將學習作為人生的首要任務,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通過提高知識儲備來提升和充實自己。另一方面,廣大青年要勇于實踐,將理論與實踐充分結合起來,積極主動地學以致用,用青春和熱情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生動實踐。青年是社會實踐的重要參與力量,“青年要積極投身于火熱的社會實踐當中,在實踐中增長才干、實現價值。”[8]青年只有努力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和能力,才能不負祖國和人民的重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偉大進程中續寫新的輝煌。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7-02(2).
[2]習近平.習近平致全國青聯十二屆全委會和全國學聯二十六大的賀信[N].人民日報,2015-07-25(1).
[3]習近平.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3-05-05(1).
[4]習近平.習近平同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舉行會談[N].光明日報,2015-04-08(1).
[5]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08-309.
[6]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習近平.緊跟黨走在時代前列走在青年前列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中續寫新光榮[N].光明日報,2013-
06-21(1).
[8]楊曉慧.習近平青年價值觀教育思想論要[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1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