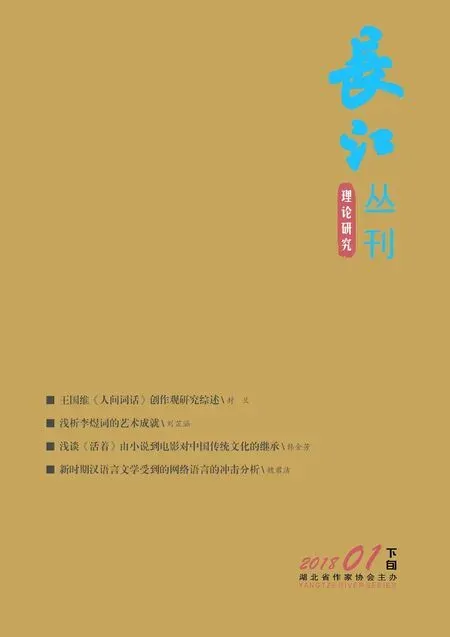李清照詞《醉花陰》文本細讀研究
蘇 敏
一、讀詞牌
《醉花陰》是詞牌名,初見于毛滂《東堂詞》:
檀板一聲鶯起速。山影穿疏木。人在翠陰中,欲覓殘春,春在屏風曲。勸君對客杯須橋覆。燈照瀛洲綠。西去玉堂深,魄冷魂魂清,獨引金蓮燭。
《醉花陰》詞牌便取義于此。《醉花陰》又名《九日》,五十二字,形式屬雙調小令,音韻屬仄韻格。上下闋各五句,一般以李清照《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為正格。
二、讀作者
李清照工詩善文,更擅長詞。其詞流傳至今的,據今人所輯約有45首,另存疑10余首。她的《漱玉詞》既男性亦為之驚嘆。她不但有高深的文學修養,而且有大膽的創造精神。她的作品取材生活,作品風格與生活經歷息息相關,創作內容因她在北宋和南宋時期生活的變化而呈現出前后期不同的特點。
前期作品集中于寫自然風光和離別相思,真實地反映了她的閨中生活和思想感情。如《如夢令》二首,用語活潑,意象清新;《蝶戀花·晚止昌樂館寄姊妹》設句巧妙,語言流轉,寫對女伴們的留戀,感情真摯。她的詞雖多是描寫寂寞的生活,抒發憂郁的感情,但卻清麗、明快,妥帖地傳達了她對大自然的熱愛,也坦率地表露出她對美好愛情生活的追求。《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是詞人李清照早年的作品。
后期作品集中抒發傷時念舊和懷鄉悼亡的情感,因為國破家亡后政治上的風險和個人生活的種種悲慘遭遇,使她的作品充滿了凄涼、低沉,在流離生活中她常常思念中原故鄉。
如著名的慢詞《永遇樂》、《轉調滿庭芳》都將過去的美好生活和今日的凄涼憔悴作對比,寄托了故國之思。
三、讀作品
“薄霧濃云愁永晝”,“霧”“云”是意象,“霧”的特點是朦朧、虛幻,于是“霧”的意象里暗含有“情感的朦朧、慘淡”“前途的迷惘、渺茫”“理想的落空、幻滅”,而前面的修飾詞“薄”更增添了朦朧的意味;而“云”形態萬千,恰喻多樣不定的人世,“濃”寫出了心情的繁重。“永晝”即“晝永”,這是為了押韻的需要。而第一句中的“愁”卻直接點出了作者的心情。
“瑞腦銷金獸”,“瑞腦”即“香料”,瑞腦,又稱龍腦香、冰片,多形成于樹干的裂縫中,體積小的為細碎的顆粒,大的多為薄片狀,古代謂之“龍腦”以示其珍貴,“金獸”是“獸形的香爐”。“焚香之趣”除卻對“芳香之味”的情有獨衷,更與文人騷客的附庸風雅頗有聯系,爐煙、杯茗、操琴的翰墨人生,雅中有靜,淡中有致。煙之輕逸、悠遠、濃淡,總會讓人賦情于形,心境也隨之起伏不定,飄搖不平。
“佳節又重陽”,“又”有對時光流逝的慨嘆。而這句又有用典,化用了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玉枕紗廚”,“玉枕”是“玉制或玉飾的枕頭”,“紗廚”是“紗做成的帳子”,這是環境的具體寫照,可以看出詞人早期生活是比較精致的。
“半夜涼初透”,這是運用了雙關的修辭手法,“涼”字,不僅僅是秋風的涼爽,更是詞人心情的反映。面對佳節美景,本應該與丈夫共渡,卻相隔萬里,凄涼心情自然而生。
“東籬把酒黃昏后”,這句的“東籬”是用典,陶淵明《飲酒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為古今艷稱之名句,故“東籬”亦成為詩人慣用之詠菊典故。
“有暗香盈袖”,這句亦是用典,《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此詩寫一個婦女對遠行丈夫所產生的深切懷念之情。詞人用其意正是表達了對遠行丈夫的思念之情。
“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西風”多代表蕭瑟、別離。“人比黃花瘦”,詞人將人喻作花,“花”的“發芽、成長、綻放、凋謝、纖瘦、枯死”,“人”的“出生、成長、青年、衰老、消瘦、死亡”,這兩者基于物理相似又激發了“人與花”的概念性隱喻。
四、讀風格
李清照在她的著名文學評論性文章《詞論》中提出:
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有押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
——李清照《詞論》
在這篇文章中,她提出了詞的基本特點是“鋪敘、典重、故實、音韻”,通過對《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的標題、作者、語句、風格四個方面的解讀,我們發現,這首詞集中體現了這幾個主要特點:音韻協和,多重意象鋪敘,用典靈活,用語清新。
[1]江弱水.詩的八堂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2]老舍.文學概論講義[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3]王國維.人間詞話[M].北京:中華書局,2009.
[4]孫紹振.名作細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