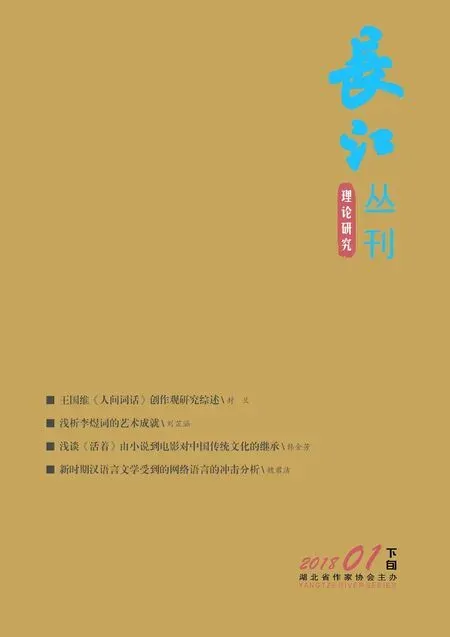焦慮與期盼
——從書信透視沈從文對建國初文學(xué)的復(fù)雜心態(tài)
盧 軍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文代會在北京開幕,雖然沈從文被拒之門外,但他依然眷念著文壇。老友巴金回憶說:“首屆文代會期間,我們幾個人去從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緒,他臉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們打聽文藝界朋友的近況,他關(guān)心每個熟人。”1949年8月,沈從文由鄭振鐸介紹到新成立的歷史博物館工作。但轉(zhuǎn)行進行文物研究的沈從文對文學(xué)界的關(guān)注一如既往,常在給親友的書信中談及。現(xiàn)從沈從文這個時期的書信中探究他對建國初期文學(xué)發(fā)展的真實看法。
一
沈從文最關(guān)注的文體是短篇小說,他20年代從湘西到北平投身新文學(xué)運動時就立誓“要為新文學(xué)運動中小說部門奠個基礎(chǔ),使它成為社會重造一種動力”,主要希望為整個新文學(xué)運動短篇小說部門作尖兵、打前站。因此建國初期的沈從文相當關(guān)注短篇小說的發(fā)展,在1951年9月寫給一位青年記者的信中他寫道:“新時代應(yīng)當有一種完全新型短篇出現(xiàn),三兩千字,至多五千字。一切是新的,寫新的典型,變化,活動,與發(fā)展。這種新型文學(xué)作品,到現(xiàn)在還沒有見到。……一切作品偉大和深入,都離不開表現(xiàn)和處理。目下說,有政治覺悟似乎什么都成,其實不成,還要點別的,要情感,要善于綜合與表現(xiàn)!這不僅是生活經(jīng)驗和政治性高度熱情即可成事,還有些應(yīng)當從更多方面來培養(yǎng)的東西。要一種厚厚的土壤,才可望發(fā)芽生根。”(《19510902北京致一位青年記者的信》)可見他對當時的文藝界領(lǐng)導(dǎo)對作家管束太多頗有微詞,認為對一個作家,尤其是非黨作家,機械的用種種紀律和政治學(xué)習(xí)來管理要求,對其創(chuàng)作弊大于益,應(yīng)給他們時間上、行動上、經(jīng)濟生活上的一定自由,才能使他們更好地為黨的利益服務(wù)。
沈從文一向主張保持文學(xué)的獨立性,反對將文學(xué)與政治等同看待。他對五十年代初動輒上綱上線的文藝界的批判活動頗多批評,呼吁要給作家營造一個寬松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凡事從理解和愛出發(fā),比對人只主觀的從打擊出發(fā),會不同得多。因此生命會慢慢的日漸豐富起來”。(《19510902北京致一位青年記者的信》)這也與沈從文感慨自身在建國后受到的不公正對待有關(guān)。
沈從文對建國初那些“緊跟”、“配合”政治的作家是不以為然的。認為巴金、張?zhí)煲怼⒉茇痊F(xiàn)代文學(xué)名家的新作遠不如前,對老舍大獲好評的話劇《龍須溝》也提出質(zhì)疑。在他看來,偉大的作品都賦予一種深刻的詩意,但“就現(xiàn)在看看,文學(xué)作家和記者中,這一點都太缺少了。這種詩的感興,不只是善于作文,還在真正有思想!……近來在報上讀到幾首詩,感到痛苦,即這種詩就毫無詩所需要的感興。如不把那些詩題和下面署名連接起來,任何編者也不會采用的。使人痛苦不僅是作者的作品能流行,重要還是它有影響。!”沈從文在信中用大段篇幅提到自己對1951年在全國范圍開展的對孫瑜編導(dǎo)的電影《武訓(xùn)傳》的批判運動的看法,“目前罵武訓(xùn),許多人都隨聲附和,對武訓(xùn)究竟是什么,可并沒有知道。正如贊美魯迅,魯迅文章好處何在,有些什么文章,也從不仔細認真看過。……世人多附和而少真知”(《19510902北京致一位青年記者的信》)。沈從文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他認為對《武訓(xùn)傳》的批判已遠遠偏離以作品為中心的文藝批評范疇,在那個年代敢發(fā)表這樣的見解是需要相當?shù)哪懥康摹?傊麑▏跗诘奈膶W(xué)界看法是“時代十分活潑,文壇實在太呆板!”
二
沈從文一向非常看重作品的表現(xiàn)形式,因為表現(xiàn)形式將影響到讀者。他指出好的作品決不是從課堂上講授的文學(xué)概論或小說作法而來,“凡最好的詩歌,最好的音樂,最具感染力的好畫,來源幾乎完全相同,不同處只不過是它的結(jié)合成形的方式和材料安排而已。……如照目下訓(xùn)練培養(yǎng)方法,短篇作者所能達到的境界,大致不會是這種結(jié)果的。方法有問題。”(19631112長沙致張兆和)言下之意,沈從文認為好的作家要有豐富的想象力和對人生的理解力,要勇于嘗試用各種方法組織材料,以達到最佳表達效果。
在沈從文看來,重思想、輕技巧、缺少獨創(chuàng)性是建國后文壇存在的最大問題。“對《紅旗譜》、《紅旗飄飄》、《謝瑤環(huán)》、《李家莊的變遷》等主流作品,沈從文在自己的書信中都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批評。”他在1959年寫給大哥的信中毫不留情地批評一些作家“永遠在寫,永遠寫不出絲毫精彩過人之處”(19590312北京復(fù)沈云麓),他指出好作品少見的原因在于作家的創(chuàng)作觀太陳舊,題材雷同、敘事手法單一。
沈從文對當時風(fēng)靡一時的一些作品并不認同,自嘲說“社會變化大,新舊要求不同,新文學(xué)方面,我并作一讀者資格也不多了。因為經(jīng)常看看月刊上的作品就多不懂好壞。而一再受推薦的,也還是看不出它的好處何在”(19650504北京復(fù)程應(yīng)繆)。建國初期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兩大題材,一類是反映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作品,一類是反映革命歷史斗爭的作品。對譽為寫農(nóng)村的“鐵筆圣手”趙樹理的小說,沈從文毫不留情地進行了批評,指出趙樹理寫的《三里灣》等農(nóng)村題材小說中有有三分之一是關(guān)于鄉(xiāng)村合作社的名詞,讀來累人得很,尤其不適合青年學(xué)生閱讀。針對軍事題材作品,沈從文認為主題大多雷同,很多作品人物臉譜化、模式化,根本深入不到人物的靈魂深處。對《林海雪原》等革命英雄傳奇小說中的浪漫夸張敘事手法他是不贊成的。他尖銳地指出:“《紅旗飄飄》文章有的是不同動人事件,可是很多卻寫得并不動人,且多相同,重點放在戰(zhàn)斗過程上,表現(xiàn)方法又彼此受影響,十分近似,——不會寫!” (19610202阜外醫(yī)院致張兆和)他還對一些革命回憶錄中濫用新名辭提出質(zhì)疑,認為這樣文章的史料價值就被破壞,文學(xué)價值也不可能再高,不能給人應(yīng)有的歷史氣氛和教育。針對如何提高敘事能力,他建議作家應(yīng)多讀些外國文學(xué)經(jīng)典作品,學(xué)習(xí)不同的表現(xiàn)方法、寫人寫事方法。他盛贊《戰(zhàn)爭與和平》寫得極好,談到小說匠心獨具的敘事視角,“寫決定放棄莫斯科的一次軍事會議,卻只是從一個六歲女孩眼中看到一個穿軍服的,和一個穿長袍的爭吵,又有趣又生動,真實偉大創(chuàng)造的心!寫戰(zhàn)爭也是文字并不怎么多,不到二三千字,卻全面開展,景象在目,如千軍萬馬在活動。都值得從事文學(xué)的好好學(xué)習(xí)”!(19610202阜外醫(yī)院致張兆和)沈從文還非常欣賞屠格涅夫的小說《獵人筆記》,尤其對小說中表現(xiàn)人物的寫作手法推崇有加,稱其能深入許多方面人物的靈魂深處。建國初沈從文還曾打算用《獵人筆記》手法寫他的生活回憶錄。
1962年7月,沈從文離京到大連修養(yǎng),前后共一個月。此間常坐電車上街轉(zhuǎn)轉(zhuǎn),看看市容市貌。他發(fā)現(xiàn)當?shù)厝罕娮x書興趣不高,在電車上看書報是“絕無僅有現(xiàn)象”。沈從文感嘆大連市一百萬人的市區(qū),街上卻看不見貼報紙板牌。本地報紙只有“小小一張”,內(nèi)容不如《北京晚報》活潑。報刊文章“多不帶勁”,雜文也“四平八穩(wěn),少性格,不深刻”,看到這些沈從文內(nèi)心深處產(chǎn)生一種“難于言說的憂慮”。沈從文在修養(yǎng)期間正值農(nóng)村題材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座談會在大連召開,8月2日,沈從文受邀出席東北作協(xié)宴請參加大連會議成員的宴會,與趙樹理、周立波、候金鏡等同桌。次日在給張兆和的家信中提到創(chuàng)作會議也應(yīng)讓刊物編輯這些看小說的改小說的人列席聽聽,且談?wù)剬徃宓目傮w印象會有意義一些。
看到不盡如人意的文壇,沈從文憂心忡忡,甚至一度打算重操舊業(yè)寫小說。1957在給大哥沈云麓的信中透露了這個想法:“我還能寫大作品,但得用我自己的方法。如只照目下有些人方法,什么也不能寫好的!”(19571120北京致沈云麓)1961年,因病住院的沈從文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有重新試來計劃寫個中篇的可能。看看近來許多近于公式的歌劇、話劇及小說,寫土豪、劣紳、軍官等等惡人通不夠深入,寫好人也不怎么扎實,特別是組織故事多極平凡,不親切,不生動,我還應(yīng)當試把筆用用,才是道理”(196101下旬阜外醫(yī)院致張兆和)。沈從文很快付諸行動,他計劃以妻子張兆和的堂兄——革命烈士張鼎和為原型創(chuàng)作一部傳記體長篇小說,表現(xiàn)一個世家子弟如何背叛本階級,走上革命道路。他廣泛搜集材料,探訪了烈士的親屬,撰寫了章節(jié)提綱,并進行了兩萬多字的試筆。遺憾的是,由于諸多復(fù)雜原因,這個寫作計劃最終沒有實現(xiàn)。
三
對當時許多作家、尤其是年青作家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沈從文也頗有微詞。他發(fā)現(xiàn)“有些聰明懂事人”只把寫作當個過渡工具,不太費力,從人事交際上多用點心,到如今卻得到雙豐收!“新社會凡事尚落實,惟作家還是有專從‘虛’字作去,倒反而頭頭是道的。只要對目下新事物善于贊美,即只寫點空空泛泛散文,也即可以得到好評,日子也可以過得真正是豐富多彩!因為可以各國走走,見聞日廣。”(19610413北京致沈云麓)因之時常感慨新一代文學(xué)工作者做作家方法和他當年已完全不同。“很多作家都不是靠本領(lǐng)而是靠另外力量支持,因為多難以為繼,越寫越壞,終于不寫。…… 常常一年選本看得過的,不會過十篇。重要作家如趙樹理或更年青些的,極少有人一年能寫上六個以上短篇的。以量計,也不能說是豐收!”(19610804青島致沈云麓)“一個作品稍微寫得好些,還可供全國廣播,或改成電影,成為全國知名作品!做一個現(xiàn)代作家,真正是幸福!其中也許還有些‘巧招兒’,比如說,他的文章即或并不怎么真正看得去,還是得到普遍好評,……過去我們寫作,以藝術(shù)風(fēng)格見獨創(chuàng)性,題材也不一般化為正確目的,現(xiàn)在搞寫作,主題卻不忌諱雷同,措辭也不宜有什么特別處,用大家已成習(xí)慣的話語,寫大家懂的事情,去贊美人民努力得來的成果,便自然可以得到成功!”(19630822北京復(fù)沈云麓)諷喻之情溢于言表。
1963年8月,在寫給張興良的信中,沈從文又提出好作品少見的原因在于作家的基本功不扎實:“當前寫作事,客觀困難易突破,主觀努力許多人還抓得不夠緊,因此機會條件盡極好,好作品還不能算已夠多。學(xué)習(xí)態(tài)度有的還值得考慮。因之做‘作家’似乎容易,產(chǎn)生好作品還相當困難。照一般話說來,即‘基本功’練得不大夠,許多人即成功了,還是難以為繼!”(196308下旬北京致張興良)沈從文總結(jié)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是:其一,盡量多看古今中外的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越懂得多,就會越容易懂得一個短篇可以用各種方法去處理;其二,去練習(xí)用筆,各樣題材都不妨去試試看。但他又感嘆世易時移,“像我這種老一套用心方法,似乎已不需要。新的要求已不同過去,方法也比較簡單便易,可能不怎么費事,就會取得較大成功的”(19630830北京致沈云麓)。但沈從文指出這種作品經(jīng)常是難以為繼的,極少有十年還站得住腳的,“能速成而不結(jié)實”。沈從文希望有志于文學(xué)事業(yè)的年輕人能用些看似陳舊但卻較扎實的學(xué)習(xí)方法來練習(xí)寫作,不要只顧眼前效應(yīng),以補救當時早熟早夭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
“我們相愛一生,一生還是太短。”這是沈從文對文學(xué)的真實情感流露。盡管對建國初期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現(xiàn)狀不滿,但他用發(fā)展的眼光把希望寄托在未來,1961年給早年在西南聯(lián)大的得意弟子汪曾祺的信中寫道:“你應(yīng)當在任何情形下永遠不要失去工作信心。你應(yīng)當始終保持用筆的愿望和信心!寫作上的‘百花齊放’,即或難望于同一時,卻必然可在異地不同時能夠體現(xiàn)”(19610202阜外醫(yī)院復(fù)汪曾祺)。時間見證了沈從文的預(yù)言,因為他對人生的豐富的理解,更因為他對祖國和文學(xué)事業(yè)的熱愛之情從未減退。
注釋
:①③巴金,黃永玉,等.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1989:11,160.
②劉永春.沈從文書信中的文學(xué)批評活動概述[J].海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