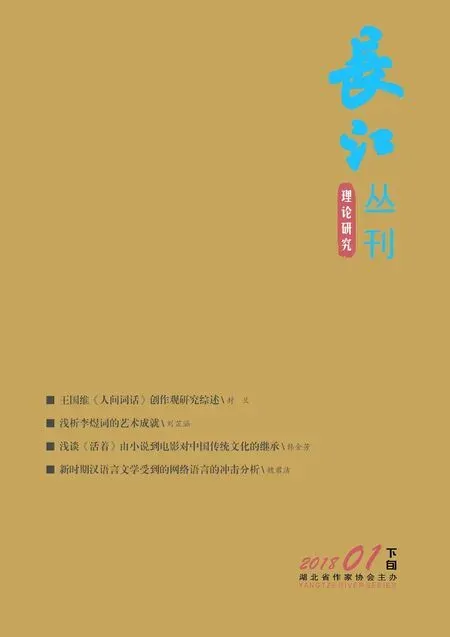孟子“心”的思想探究
李姿墨
一、孟子心的形成理論基礎
“心”字最早的記載是在殷周的甲骨文上,是一個象形文字,形似心臟,許慎《說文解字》中解釋為“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心出現的開始專指器官,人心在古人看來還有思維的功能。《釋名·釋形體》中指出:“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心也。”說明所有事物都是通過心來認知的,強調了心的功能。
心學的開端最早出現在《尚書》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至此哲學中開始出現對于心的研究,隨后心的使用非常頻繁,內涵也變得逐漸豐富起來。“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這些“心”的運用反映了人們“不快活之心”、“至誠之心”、“憂患之心”的情感及心里狀態,這些心已經被用于表達各種思想、意志、情感。
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其對于“心”的討論奠定了整個儒家對于心的探索的總基調。在楊伯峻先生在《論語譯注》中,《論語》中“心”字共計出現6次,“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終日飽食,無所用心,難矣哉!”,“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從論語的整篇可以看出孔子沒有對心做出具體的論述,但是“心”的內涵孔子是通過對于仁的闡釋來體現的。“仁”字的早期是由“身”和“心”構成,所以仁字包含身心合一的含義,那么孔子對于仁的理解實際上就是對于心的概括。基于孔子對于仁所闡釋的豐富內涵,可以推測出,孔子所說之心有四層含義:第一,“心”是受人思維控制的,內涵豐富情感的,人人都有之心。第二,心是人之道德的出發點,道德由心而生,人的所有行為受心的控制,道德的標準是一樣的,人的初心也是一樣的。第三,由心而生的道德標準也要由心支配人本身遵守道德,遵守道德的目地需要心的意志來完成。
一眾學者認為在孔子之后,《性自命出》及《情性論》對孟子心性論的形成也有著重大影響,其中有大量文字對心進行闡釋,除了直接使用心字之外,還大量運用由心構成的文字表達思想,如“德”、“仁”,表達心有意志之心、思情之心、情感之心、成德之心。
二、孟子心的內涵
唐君毅在《中國哲學原論》中指出孟子之學的中心就是心學,孟子的其他思想都是在心之上萌發的,心為人之根基,與物與動物有別,使人之為人。
(一)情感欲望心
孟子認為心中包含情感及欲望,是人最基礎的心里情緒。“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后快于心與?”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梁惠王上》)孟子所言此心可成為情感欲望之內,是人最本能產生的,人人都有,不可祛除的,本然之心。此心能夠產生想法,不受其他器官控制,并驅使人去做并不高尚或動物本能,甚至有違道德的事,孟子承認此心的存在。
(二)認知心
孟子沒有對認知心做出非常明確的闡釋,但是我們可以很清晰的推斷出其存在,是一個輸入的過程。第一,認知心為人心固有的,且心可以對任何事情做出判斷權衡,“權,然后知輕重;度,然后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梁惠王上》)可見心對所有事物皆有清晰明確反饋,并指導身做出反應。第二,心會受到外部環境和內在存養的影響,可以通過修養功夫再次獲得,也會因為沒有修養功夫的滋養而消失,所以孟子極為重視對于身心存養的功夫修煉。
(三)主宰心
孟子認為人身體和思想的主宰就是心,是一個輸出的過程。心可以控制身體活動和心理活動,并通過控制身體和心理的活動來達到內外的統一,孟子運用了一個比喻句來形容身心的關系“君子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離婁下》)”,認為君如心,臣如身,心指導身,臣服從君。“心之官則思”只有心是能夠思考的,其他的器官均不能,其他器官是通過心的指揮來發揮作用的,心可是身為心服務。
(四)道德心
道德心是孟子關注的重點,也是從情感欲望心、認知心和主宰心的基礎之上自然生發出來的,再次由心進行加工整理升華,同時也受上面三心的反作用,相互包含,相互影響。道德心既是一種感性存在,又是一種倫理存在。
道德心雖是生發出來,整個過程卻是一瞬間完成的,并可以持續存在,這種由心升華出來的道德心也可以稱為本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本心有四端是整個思維過程的一個開始,是性善的開始,是作為仁者圣賢的開始,之后需要通過修養功夫增強此心的境界。
孟子認為心是意識的主體,能主宰身體,能指導意識,對人生的價值取向起到關鍵性的指導作用。必須通過修養來滋養此心,要存養浩然之氣,養氣既是養心,深刻理解心的概念,是正確樹立存養功夫的關鍵。
[1]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60.
[2]焦循.孟子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7.
[3]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