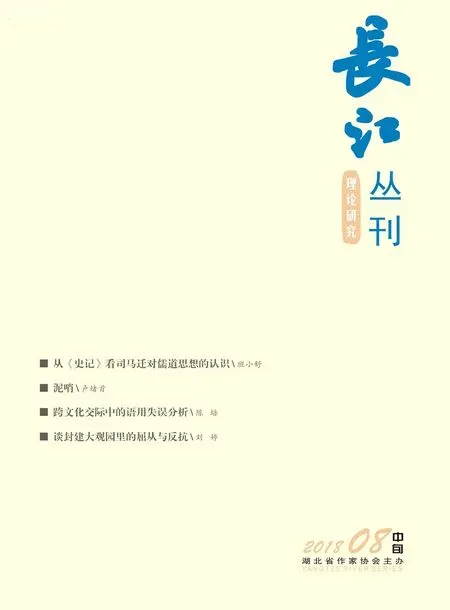泥 哨
■盧緒首/日照市規(guī)劃設(shè)計研究院
星期天,同事相約拓展訓練完后攀爬云蒙山。沿著山路和臺階,上上下下,欣賞著蒙山美景,呼吸著新鮮空氣,累并快樂著。突然一聲聲似曾相識動聽悠長的鳥鳴聲吸引了我們,情不自禁四處張望,原來是藝人吹奏的泥哨聲,逼真動聽極了。我不自覺湊上去:一籮筐泥哨,小鳥形狀,頭上有冠,兩側(cè)各有一小孔,底部也有一小孔,燒制的似涂了一層釉,通身透著粗制而古樸韻味。伴隨著一聲聲的鳥鳴聲,看著這些粗制而古樸的泥哨,一下把我?guī)Щ亓送甑哪莻€時候。
六七十年代的中國經(jīng)歷了“三年災害”,全國生活普遍匱乏,尤其農(nóng)村要是能解決吃飯且略有剩余,那就算好農(nóng)戶了。我們童年就是生活在那時的農(nóng)村,我們那一代普遍較矮。
當時我們農(nóng)村每家都有二三個孩子,父母似乎也不怎么寵我們,孩子們都是自然成長,還給生產(chǎn)隊里、家里干農(nóng)活,割草喂牛喂羊喂兔子。雖然那時農(nóng)村生活貧乏,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玩具,但玩是我們孩子的天性,在村里老人、閑時的大人幫助和支持下,我們自創(chuàng)或?qū)W會了很多玩法,也自制了很多玩具:老鷹捉小雞、丟沙包、踢毽子、跳繩、頂腿、打陀螺、打瓦、鏈子槍、彈弓、射箭、泥哨……
其時,我們最喜歡的還是做泥哨,吹泥哨。六七十年代,我們老家那一帶幾乎每個男孩都希望擁有泥哨。泥哨,是我們孩童的主要樂器,那時的我們總想選用最好的材料,做出自己最滿意的泥哨。純粹的胭脂泥細膩無雜質(zhì),適合做泥哨、泥壺等精品,為此我們經(jīng)常混跡于有風化土的斜坡,尋找一種叫胭脂泥的夾縫殘積土。找到胭脂泥后,剔除雜質(zhì),將其混合一定數(shù)量的水,反復揉搓,做到均勻柔順,隨后用手捏或模具使之成形,通常修整成鳥形、雞形等形狀,然后用較粗的鐵絲、細枝條從泥胎頭部試探著穿向尾部,通過腹部時向兩側(cè)旋轉(zhuǎn)側(cè)壓擴腔,直到穿透尾部,再在中上部軸線或兩側(cè)適當位置做出與中間通孔相連的一個、兩個音孔,當然有靈巧的還做出四孔五孔,甚至更多的音孔也不稀奇,最后陰干,放在爐火中燒制成泥哨。更多的孩童們未等泥哨陰干,還帶著泥土氣息就急不可待吹演一氣,有時雖然難聽,滿嘴泥屑,還是一臉滿足一臉笑意。于是田野、山坡、村落,白天、傍晚不時響起一陣陣鳥鳴聲、笑聲,充滿大地,充滿天空,似乎沒有饑餓,沒有憂愁,只有快樂、幸福……
一聲聲的鳥鳴聲,宛如天籟之音,深深地震撼著我,把我從童年時光里喚回到眼前。我喜歡泥哨,它寄托著我們那一代人太多的童年記憶,凝聚著我們童年的酸澀和幸福,更多的是甜蜜的回憶,它是我們童年的信使。我更是時常回憶起六七十年代的童年,它雖苦澀,但也幸福多彩,深深鐫刻著我們那一代人的生活:不怕貧窮,珍惜生活,樂觀向上。這些已融化到我們的血夜和性格里,永不消逝。
我多買了幾個泥哨,將與孩子們分享,帶著它們繼續(xù)往上爬,更高,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