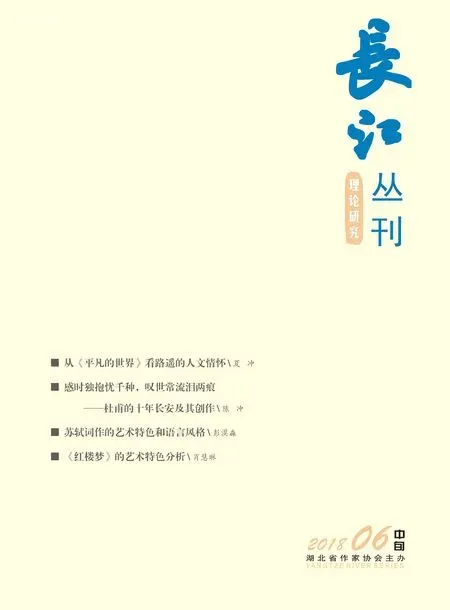《論語》中孔子對“勇”的態度探究
■張貽珉/北方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子曰:“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孔子認為“勇”是“君子之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君子應當具備的品德之一。但是與“仁”和“義”不同,孔子并不認為“勇”是一種“美德”,“勇者不必有仁”(同前),他對“勇”更多的持一種中性的態度。《論語》中“勇”字出現了16次,大多數時候是跟子路一起出現。在孔子的所有門徒中,子路以“勇”著稱,但孔子對他“好勇”一直抱以審慎的批判態度,還曾經告誡過子路總是這樣的話,會“不得其死然”,而后一語成讖。總之,孔子認為“勇”無法獨立作為一種“美德”存在,它必須必須“以‘義’為質,以‘禮’為節,統攝于‘仁’。”
“勇”要成為美德,首當其沖的就是要受到“義”的節制,子路向孔子提問“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當“勇”缺乏“義”做引導,就會成為“亂”和“盜”,而不是君子之“勇”。孔子還從反面論述,“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由此可見,君子之“勇”與“義”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脫離了“義”的勇,無論是“智勇”,還是無謀的匹夫之勇,都難以稱得上是美德,無“義”的“智勇”甚至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危害。關于“義”與“勇”,荀子對孔子的學說提出過補充,在荀子看來“勇”有四者,“狗彘之勇”、“賈盜之勇”“小人之勇”以及“士君子之勇”,前三種惟個人之利害是瞻,為食為利,“不知是非”,寡廉鮮恥,“輕死而暴”,都屬于“下勇”,而士君子之勇“義之所在,不傾于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為“上勇”(《荀子·榮辱》)。
君子的一切言行,都要“約之以禮”(《論語·雍也》),作為“君子之質”之一的“勇”也不例外。《論語·泰伯》中說:“勇而無禮則亂。”君子之“勇”,除了要以“義”為質,還要依“禮”而行,以“禮”制“勇”。《論語·陽貨》中記載了孔子與子貢關于“君子亦有惡乎”的對話,孔子在其中明確表示“勇而無禮”是君子所厭惡的行為:“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子貢也說自己“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有沒有依“禮”而行,以“禮”制“勇”,也是君子之“勇”與小人之“勇”的明確界線。
“勇”還要統攝于“仁”。“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前文提到,“仁”是孔子主張的一切美德的合集,包含了“恭”、“寬”、“信”、“敏”、“惠”、“忠恕”、愛人”、“孝悌”等美德,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君子之“勇”也包含在內。以“仁”為統攝的“勇”,方能做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孟子 ·滕文公下》)《論語·顏淵》中司馬牛向孔子請教:“不憂不懼就可以稱之為之君子了嗎?孔子答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在這里“內省不疚”彰顯的就是“仁者之勇”,心中有“仁”,勇者才能真正做到“勇者不懼”。另一方面也只有包含君子之“勇”的“仁”,才是真正的“仁”,心中懷有這樣的“仁”,才能形成君子外圓內方、不怒自威的風度品格,《論語·子張》中子夏所說:“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就是指的這個方面。曾子把帶有含蓄內斂特質的君子之“勇”描繪為:“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論語·泰伯》)只有具備了這種“仁勇”,才能成為《論語·泰伯》中所描述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君子”。與上文提到的“義勇”所透漏出的外在氣概不同,“仁勇”更多的著眼于君子的內在平和,著眼于君子在危險與誘惑面前,所流露出的鎮定自如的定力和風范。
在《論語》中的孔子所贊成的君子之“勇”,除了節于義,制于禮,統于仁以外,還有一個特質,就是強調以理性管理“勇”。即“智”。理性缺位的“勇”在《論語》中有兩種表現方式,第一種是“好勇”,不加節制。《論語·公冶長》中記載,孔子有一天說“道不行”,想坐船去海外,敢跟隨他去的恐怕只有子路了。子路聽了以后“沾沾自喜”,孔子說他“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批為:“夫子善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于義也。”由此處可見,孔子對于子路的“勇”是認可的,但認為他不加節制的“好勇”,以“勇”為驕是不可取的。那么孔子認為正確的態度是什么呢?就是《論語·述而》中所說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說只有顏回和他自己能做到這點,子路不服氣問孔子,如果統帥三軍,會選擇跟誰一起。這就引出了理性缺位的“勇”第二種表現方式,就是有勇無謀的匹夫之勇。子路問這個問題的本意,是希望得到孔子的肯定,然而孔子的回答是會選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順便批評子路的“勇”是“暴虎馮河”的匹夫之勇,這種兩只拳搏虎,兩條腿渡河,“死而無悔”行為不為君子所取。
公元前480年,衛太子蕢聵作亂,孔悝被挾持,當時子路是孔悝蒲邑的大夫。別人為避免殺身之禍都紛紛逃離衛國,只有子路逆著人群只身前往衛國營救他,正如他自己所言:“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后在戰斗中,子路身負致命傷,帽子掉在地上,臨死前說“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子路“食其食者不避其難”是為“義”,結纓而死是為“禮”,視死如歸,踐行己道是為“仁”。《論語》中關于“勇”的記載與子路的關聯最為密切,孔子對子路之“勇”的敲打也最多,而最后,也正是子路,用生命完整標致地詮釋出了孔門的君子之“勇”。
[1]陳立勝.《論語》中的勇:歷史建構與現代啟示[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4):112~123,205.
[2]李振綱,陳鵬.《論語》中的“勇”與子路“好勇”[J].河北學刊 ,2012,32 (01):30~33.
[3]司馬遷 .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2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