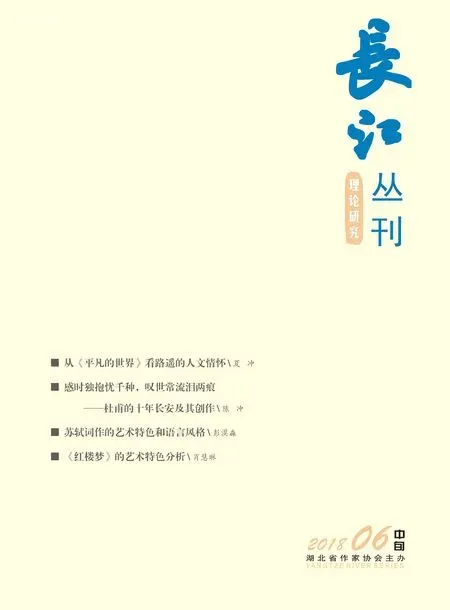崇禮尚武:論齊魯武術(shù)的地域文化特色
■楊向東 劉瑞忠/.山東省城市服務(wù)技師學(xué)院;.煙臺(tái)市體育運(yùn)動(dòng)學(xué)校
“齊魯文化”作為一個(gè)區(qū)域文化范疇與“燕趙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相并提,是一個(gè)有明顯地域特色的獨(dú)立文化體系,乃齊文化和魯文化的統(tǒng)稱。春秋時(shí)期的魯國(guó),產(chǎn)生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學(xué)說(shuō),而東臨濱海的齊國(guó)卻吸收并發(fā)展了當(dāng)?shù)赝林幕|夷文化)。齊文化尚功利,魯文化重倫理;齊文化講求革新,魯文化尊重傳統(tǒng)。而從武術(shù)文化的角度來(lái)看,齊文化尚武,魯文化崇禮,兩種文化在發(fā)展中逐漸又有機(jī)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具有豐富歷史內(nèi)涵的齊魯武術(shù)文化。
一、齊文化的尚武精神
“齊文化”就是先秦時(shí)代齊國(guó)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體系,此體系以博采眾長(zhǎng)、融會(huì)創(chuàng)新為特征,以實(shí)用主義為本質(zhì),以富國(guó)強(qiáng)兵、召令天下宗旨。與其他區(qū)域性文化相比較有著自己明顯的特征,其中,齊人尚武就是齊文化的一種典型特征。
首先,齊文化的尚武特性是由其地理環(huán)境引起的。在學(xué)者對(duì)區(qū)域文化考察研究中,很早就注意到了自然環(huán)境對(duì)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齊國(guó)地理狀況復(fù)雜,平原少,多鹽堿地和山丘,而且是一個(gè)典型的沿海國(guó)家,有很長(zhǎng)的海岸線,故此齊國(guó)具有勇于拼搏、銳意進(jìn)取的海洋文化個(gè)性。
其次,沿海國(guó)家的地理?xiàng)l件,使齊人打上了濱海民族性格的烙印。從齊地土著居民東夷人發(fā)明弓箭的史實(shí)中,也可知齊地先民具有善射、善獵、好戰(zhàn)的尚武傳統(tǒng)和粗獷強(qiáng)悍、英武剛毅的文化性格。齊人繼承了其先民的這種尚武精神,以勇猛好斗、爭(zhēng)強(qiáng)好勝蜚聲海內(nèi)外,崇尚勇武的精神上至國(guó)君下到百姓蔚然成風(fēng)。
第三,當(dāng)時(shí)齊國(guó)選臣用士皆以武功為標(biāo)準(zhǔn),即便是士卒也要必須達(dá)到“舉之如飛鳥(niǎo),動(dòng)之如雷電,發(fā)之如風(fēng)雨”的武技水平。這中自上而下的尚武之風(fēng)對(duì)后世齊民“勁勇而沉靜,樸純而少文”的性格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以至于“齊地方二千余里,帶甲數(shù)十萬(wàn)”。而這種尚武精神最終又成就了齊國(guó)“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業(yè),促使齊文化從一般的“尊賢尚功”走向了“霸主文化”。
總之,在尚武精神影響下,齊地武術(shù)文化表現(xiàn)出了大開(kāi)大合、放長(zhǎng)擊遠(yuǎn)、注重攻擊、勇猛激烈、粗獷奔放等霸氣十足風(fēng)格特點(diǎn);講究“一寸長(zhǎng),一寸強(qiáng)”的進(jìn)取精神和攻擊意識(shí)。這一系列的風(fēng)格特色,都是在齊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下而形成的,是齊文化的積淀和延續(xù)。
二、魯文化的崇禮思想
魯文化起源于西周初年,受封于魯國(guó)的周公旦,在那個(gè)非常講究宗法血緣關(guān)系的周代,因周公旦與周王室屬于同一血統(tǒng),所以決定了周公旦立國(guó)的文化思想路線不能不是西周的禮制,最終決定了魯文化的走向。
首先,從地理環(huán)境來(lái)講,魯國(guó)是個(gè)適宜農(nóng)桑的地域,客觀上要求推行周代的禮樂(lè)制度。西周所創(chuàng)立的“尊祖”和“敬宗”的宗法制度也只有在穩(wěn)定的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區(qū)域才能得以存在,而在那些游走不定的畜牧或商業(yè)社會(huì)中是談不上的。魯國(guó)既然是一個(gè)適合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國(guó)家,而且又承繼了周人的重農(nóng)傳統(tǒng),那么客觀上就要求其文化必定是崇尚禮儀的,如此一來(lái),就使魯國(guó)成為了西周禮樂(lè)文明的傳承者和實(shí)施者。
其次,魯文化中的禮樂(lè)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正統(tǒng)性。在眾多諸侯國(guó)中,魯國(guó)作為姬周嫡傳,不光全盤繼承了西周的文化傳統(tǒng),而且還具有優(yōu)越的地位和享有獨(dú)特的權(quán)力,故此魯人有一種天生的自豪感。同時(shí),魯國(guó)還享有天子之禮樂(lè)。由此可知,魯人對(duì)周禮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在推行周代禮樂(lè)制度時(shí),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第三,以周禮為基礎(chǔ)發(fā)展而來(lái)的儒家思想成為了中國(guó)社會(huì)的主流思想。經(jīng)過(guò)春秋時(shí)期的百家爭(zhēng)鳴之后,儒家思想最終于漢武帝時(shí)期上升為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的主流思想,從此傳承不輟。作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代表的儒家倫理,也因此為武術(shù)文化思想體系的構(gòu)建提供了主干和框架,在成熟的武術(shù)文化思想體系中儒家倫理道德是武人的第一生命,以至于習(xí)武的宗旨、戒律的制定、以及武術(shù)事件和人物的品評(píng),幾乎無(wú)一例外的都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依據(jù)和標(biāo)準(zhǔn)。
總之,由于魯文化直接傳承于西周文明,且具有中華文明的正統(tǒng)性和權(quán)威性;故此,魯文化在中華文明中占據(jù)了主導(dǎo)或領(lǐng)袖的地位。這種優(yōu)越感和自豪感深深地扎根在魯國(guó)人的思想意識(shí)當(dāng)中,使他們?cè)谌魏嗡季S和行動(dòng)中都積極主動(dòng)地到儒家思想中去尋找根源、支持和依據(jù),那么,以儒家思想為主干和框架來(lái)構(gòu)建武術(shù)倫理文化體系那就再自然不過(guò)了。
三、“崇禮尚武”齊魯武術(shù)文化的形成
齊魯文化并非齊、魯兩種文化的簡(jiǎn)單相加,而是在兩種文化的碰撞、匯合中,互相審視、互相選擇、互相滲透、互相交融之后而形成的一種綜合性文化。而齊魯武術(shù)文化在齊魯文化形成的過(guò)程中,也逐漸實(shí)現(xiàn)了尚武與崇禮的有機(jī)融合。
首先,齊文化的“兼容性”和“變通性”使它很容易就接受了崇尚禮樂(lè)的魯文化。先來(lái)看齊文化的“兼容性”,因?yàn)辇R國(guó)是沿海國(guó)家,社會(huì)開(kāi)放程度比較高,能夠?qū)ν鈦?lái)文化兼收并蓄。再來(lái)分析齊文化的“變通性”,齊文化具有很強(qiáng)的“變通性”,這種“變通性”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的積淀之后,最終形成了一種智者型的沿海文化。正是齊文化的這種“兼容性”和“變通性”,才促使其把魯文化中的尚禮思想融匯到了自己的文化當(dāng)中,并以此修正、完善了自己的武術(shù)文化體系。
其次,魯文化之“勇”與齊文化之的齊魯武術(shù)文化自覺(jué)的最高境界。“尚武”的高度契合,使“重禮教,尚信義”的魯文化有機(jī)的接納了齊文化的尚武精神。魯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推崇“仁者必有勇”,表述了“仁”與“勇”相結(jié)合的辯證關(guān)系。一個(gè)仁德之人,必定疾惡如仇,具有敢于同一切邪惡之人進(jìn)行無(wú)所畏懼斗爭(zhēng)的尚武精神。齊文化中的“尚武”就是“大勇”的一種具體體現(xiàn)。為了彰顯“大勇”精神,“尚武”就成為一條必不可少的途徑。由此可見(jiàn),崇尚禮樂(lè)文明的魯文化雖然反對(duì)濫用武力的“小勇”,但是卻極力推崇“見(jiàn)義勇為”的“大勇”。所以,“見(jiàn)義勇為”也就成為了齊魯文化影響下武術(shù)人的典型特征。
總之,“武”是用于制止暴力沖突的技藝,但是它的使用還必須由“禮”來(lái)平衡,即,“以禮統(tǒng)武”、“德武合一”,該出手時(shí)才能出手,而且不到萬(wàn)不得已絕不可輕易動(dòng)武。因此,齊魯武術(shù)文化在強(qiáng)調(diào)“尚武”精神的同時(shí)還突出了“崇禮”的倫理道德。
四、結(jié)語(yǔ)
費(fèi)孝通先生曾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來(lái)概括地域文化的“文化自覺(jué)”。“各美其美”就是,因各個(gè)領(lǐng)域都有自己獨(dú)特的文化,所以齊魯武術(shù)人就有責(zé)任和義務(wù)弘揚(yáng)自己優(yōu)美的武術(shù)文化傳統(tǒng);而在弘揚(yáng)自我文化的同時(shí),還要虛心學(xué)習(xí)其他地區(qū)武術(shù)文化的優(yōu)點(diǎn)和長(zhǎng)處,即“美人之美”;這樣各個(gè)民族、各個(gè)國(guó)家、各個(gè)地區(qū)的武術(shù)優(yōu)秀文化就通過(guò)互相包容、互相學(xué)習(xí),構(gòu)成了一個(gè)多元武術(shù)文化的和諧世界,從而實(shí)現(xiàn)了“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1]司馬遷.全本史記大全集(第二卷)[M].北京:華僑出版社,2011:224.
[2]唐韶軍.生存?生活?生命:論武術(shù)教化三境界[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1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