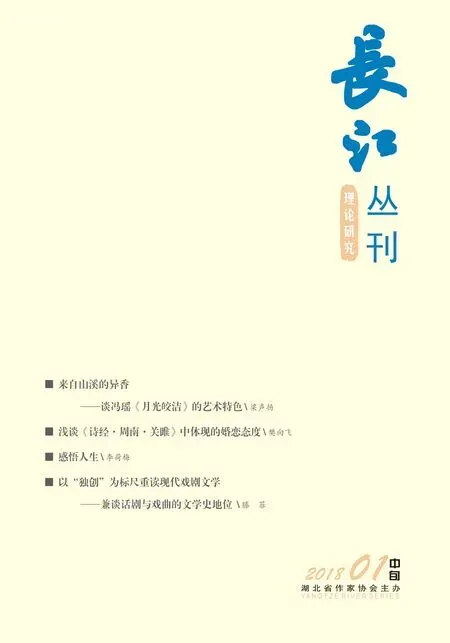傳統(tǒng)戲曲現(xiàn)代化的成功嘗試
——論莫言戲曲《錦衣》
王雪敏
在當代語境中,“戲曲”是指中國本土的傳統(tǒng)戲劇,與來自西方的“話劇”,“歌劇”,相并列組成我國戲劇的整體。中國戲曲在古代漫長的發(fā)展歷程中,形成了元雜劇,明清傳奇和清代后期以來的種種地方戲,它們在各自的時代盛極一時,最后都無一例外的走向衰落,被冠以“古典戲曲”之名。董健先生說:“一種藝術(shù)一旦成了‘古典’,其藝術(shù)結(jié)構(gòu)也就被封閉在一個相對固定的系統(tǒng)之內(nèi),名聲上是‘高雅’了,但其代價卻是失去了活生生的生存方式,也就失去了廣闊的生存空間——以活生生的面貌在舞臺上與廣大觀眾見面的機會。”①屬于“古典戲曲”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面對新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環(huán)境,甚至觀眾,我們必須找到適合新形勢的現(xiàn)代戲曲,莫言的新作《錦衣》延續(xù)一貫的民間立場,將傳統(tǒng)戲曲注入現(xiàn)代精神,這給當下迷茫困頓的中國戲曲指明一個值得學(xué)習(xí)的方向。
一、傳統(tǒng)戲曲樣式的延續(xù)
《錦衣》講了一個革命黨舉義攻打縣城的歷史事件,其中夾雜了公雞變?nèi)说墓砉止适拢呵宄┠辏澒傥劾魴M行,民不聊生,留日愛國青年秦興邦和季星官喬裝成夫妻潛回家鄉(xiāng)密謀起事。路遇大煙鬼宋老三在街頭賣女兒宋春蓮,季星官為春蓮不平。無奈二人被捕快識破偽裝,秦興邦逃走,季星官詐死潛藏。之后穿插了季星官的寡母,媒婆王氏及其做捕快的侄子王豹,還有高密縣令莊有理和莊雄才父子的重重糾葛。王婆、王豹因圖謀鹽鋪錢財,設(shè)計讓季母為遠在東洋留學(xué)的兒子先行娶妻,致使季母讓兒媳春蓮與一只公雞成親。而王豹與莊雄才均垂涎春蓮美色,幾次前來糾纏,春蓮誓死抗爭,危急時刻季星官潛回家中為春蓮療傷,兩情相悅,終成夫妻。不料為偷聽者王婆告發(fā),引莊氏父子帶兵前來捉拿,又正好被秦興邦和季星官所發(fā)動的義軍擊敗,王豹等爪牙則乘勢反水,捉住莊氏父子,故事結(jié)束。
在戲曲結(jié)構(gòu)和人物塑造上,《錦衣》全面向傳統(tǒng)戲曲回歸,單線的敘述,起承轉(zhuǎn)合的情節(jié)設(shè)置,類型化的人物設(shè)置,寫意化的動作和舞臺擺設(shè),以及最后的大團圓結(jié)局,傳統(tǒng)戲曲慣用的套路都有運用。另外,在戲曲形式上,《錦衣》再現(xiàn)了山東戲曲茂腔、柳腔的唱詞和旋律特色,唱詞通俗押韻,旋律婉轉(zhuǎn)凄切,易為大眾所接受,因為莫言懂得,民間戲曲只有在民間才能保持它真正的生命力。
二、笑中帶淚的揭露人性
縱觀莫言創(chuàng)作,無論小說,散文,話劇,莫言總是給它們披上一層喜劇性的外衣,撥開這層外衣我們看到的是作品深刻的批判性和悲劇性,是笑中帶淚的揭露真實的人性。《錦衣》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思考滲透在對人物形象的刻畫中。王豹是該劇著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此人最是見利忘義,順發(fā)鹽鋪剛死了掌柜,他就急忙趁火打劫,路遇穿戴講究的秦興邦,他以抓革命黨為名對其幾次三番威逼恐嚇,將秦興邦身上值錢之物搜刮一空才算罷休。但面對頂頭上司莊知縣及其兒子,王豹表面逢迎拍馬,心里卻一直做著取而代之的美夢,他趁知縣不在的時候坐上知縣的太師椅,模仿知縣升堂的威武氣派,被知縣抓個現(xiàn)行之后連滾帶爬的跑到知縣面前下跪磕頭,為自己開脫“小的怕老爺落座涼了屁股,先來給您熱熱窩兒”,知縣點破他的歪心思,王豹嘴上說不敢,心里卻不服氣,“我要真當上(知縣),不比你干得差呢!”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王豹將見風(fēng)使舵,隨機應(yīng)變的生存法則詮釋的淋漓盡致。在故事結(jié)尾,革命軍攻陷縣衙,王豹立馬反水,將槍口對向莊雄才,喊著“兄弟們,大清朝完蛋了,識時務(wù)者為俊杰,咱們也革命了吧!到新政府里混個小官做!”革命的正義與神圣被他這一戲劇性的舉動消解殆盡,民族大義在這種人眼里還不如一把太師椅來的實在,“名利”二字才是他們?nèi)松娜恳饬x,為追名逐利可以不擇手段、毫無底線,人性的自私貪婪在這里展露無遺。但莫言又是慈悲的,對生活在底層的勞苦大眾,哀其不幸。媒婆王氏曾是舊式包辦婚姻的受害者,她出身大戶人家,自信將來貴不可言,可媒婆李大嘴硬將她說給一個好吃懶做的二流子為妻,她也曾以死抗爭,得到的卻是丈夫的羞辱虐待。她深知媒婆這一職業(yè)如何顛倒黑白,但她沒有同情反而助紂為虐,將自己的不幸復(fù)制給更多無辜的青年男女,從中得到報復(fù)的快感,人性以這樣看似詭異卻又合理的方式被扭曲了,莫言還指出這種扭曲不是一時一地偶然發(fā)生的,是有傳承性的,王婆的人生不幸皆因媒婆李大嘴,這一人物關(guān)系的設(shè)置令人細思極恐,李大嘴之前是誰?王婆之后還會有誰?命運這樣代代延續(xù),不合理的也變成合理的了,但魯迅曾說過:“從來如此,便對么?”②莫言對種種畸形人物關(guān)系的安排,反映的是整個社會的病態(tài),當整個社會被這種病態(tài)所籠罩,人人都像戴著面具生活,戴的久了長到臉上,再想揭下來,就疼了。
三、當下戲曲努力的方向
縱觀莫言作品,戲曲元素幾乎成了每部作品的“標配”,比如在莫言的小說中經(jīng)常響起的家鄉(xiāng)戲曲“茂腔”,它給莫言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增添鮮明的地域色彩,也借助莫言的文字讓人們看到了這一民間戲曲形式的生存狀態(tài):鮮活的,也是艱難的。莫言小說中的戲劇性元素一開始只是作為文本的一部分出現(xiàn),到《檀香刑》,《蛙》,《霸王別姬》,《我們的荊軻》,戲劇性元素逐漸增強,最后獨立出來,到現(xiàn)在的戲曲《錦衣》,我們看到莫言一步步地將戲劇從邊緣推向文學(xué)的中央,莫言曾說:“戲劇創(chuàng)作方面,我是一個學(xué)徒。但我有成為一個劇作家的野心。”③《錦衣》等戲劇證明了他作為一個作家的戲劇能力。與一般作家相比,他在文體形式上變化多端,與一般劇作者相比,他能將深度思考更好的融入傳統(tǒng)戲曲,內(nèi)容與形式在他這里達到巧妙的和諧。站在戲曲現(xiàn)代化的角度,這是經(jīng)驗,也是教訓(xùn)。
近代以來,戲曲現(xiàn)代化之路走的曲折坎坷。清代及其之前的戲曲宣揚的無非“載道”、“衛(wèi)道”、“勸善懲惡”的封建思想,或把戲劇當作有閑階級的消遣娛樂。“五四”前后,西方近現(xiàn)代戲劇涌入,一方面沖擊本已內(nèi)憂外患的戲曲,另一方面又給傳統(tǒng)戲曲改良提供新思想和新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現(xiàn)實主義戲劇,新浪漫主義戲劇,浪漫主義戲劇,給古老的戲曲改良自己提供多樣化的借鑒。三十年代民族危機加劇,戲劇與政治的關(guān)系日趨密切,戲曲也不可避免的成為救亡的工具之一,1949年之后,戲曲本該重回現(xiàn)代化道路上來,但由于片面發(fā)展三種戲曲中的戲曲現(xiàn)代戲而壓抑剩下兩種戲曲,戲曲創(chuàng)作走向極端,最終產(chǎn)生“樣板戲”這樣的畸形兒。雖然之后的改革開放重新將戲劇扳回“現(xiàn)代化”軌道,并出現(xiàn)一個探索戲劇的熱潮,但這股熱潮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jīng)消退,商業(yè)經(jīng)濟大潮推動電影,電視,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占領(lǐng)文學(xué)藝術(shù)的陣地,把本來已經(jīng)邊緣化的戲曲擠到鮮人問津的角落。有人因此將戲劇衰落的原因歸結(jié)于,新藝術(shù)形式借放棄自身獨立性才獲得大眾喜好,假設(shè)此種觀點成立,有些思想性與藝術(shù)性兼具的藝術(shù)作品沒有刻意迎合大眾照樣受到大眾贊賞,這又做何解釋?莎士比亞的戲劇至今仍在世界范圍內(nèi)巡演,受到無數(shù)追捧,它們喪失自己的獨立性了嗎?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的先鋒戲劇倒是堅持了自己的“先鋒”,結(jié)果卻是走向兩個極端:一是過分強調(diào)哲理導(dǎo)致思考大于形象;二是過分追求新奇導(dǎo)致形式大于內(nèi)容。由此可見,戲劇的現(xiàn)代化不是內(nèi)容與形式兩張皮的拼湊,而是二者恰到好處的融合。以此標準去看莫言的《錦衣》,我們就能解開《錦衣》成功的密碼:一方面,它采用我國傳統(tǒng)的戲曲樣式,立足于民間立場,讓讀者或觀眾重拾對傳統(tǒng)文化的熟悉感,讓更多的人關(guān)注傳統(tǒng),關(guān)注戲曲,從而為戲曲培養(yǎng)堅實的大眾基礎(chǔ);另一方面,它深入探究近代中國的革命與社會問題,再現(xiàn)近代中國社會各種弊病的同時,揭露了人性的致命缺陷,這是戲曲現(xiàn)代化的要求,也是當下對戲劇“人”的精神的延續(xù)。
注釋:
①呂效平.戲曲本質(zhì)論[M].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序3.
②魯迅.狂人日記[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2:11.
③莫言.我們的荊軻[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