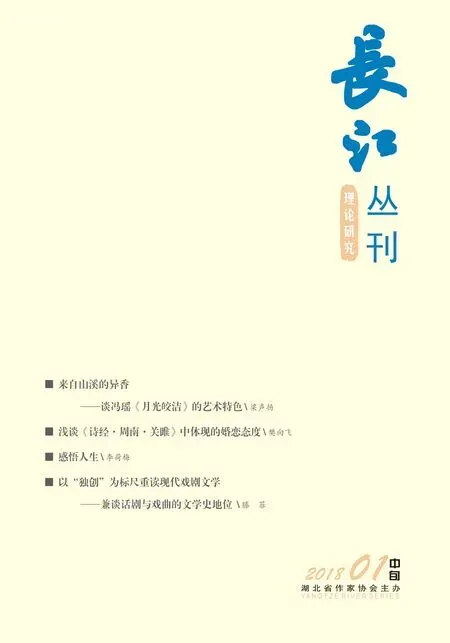以“獨創”為標尺重讀現代戲劇文學
——兼談話劇與戲曲的文學史地位
滕 菲
眾所周知,中國近代戲劇文學包括話劇和戲劇劇本,但是在悠悠的文學發展歷程中,受到主流與非主流文學趨勢的影響,一些主流文學樣式常常會擠壓非主流文學樣式,由此導致一些戲劇文學樣式被排擠在文學的邊緣,極度地受到忽視,其中國劇在二十世紀的遭遇就是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在現代,不少戲劇學者度戲劇文學有著極大的探究興趣,甚至將一生都風險在戲劇文學研究上,但是在重視戲劇文學的同時或多或少地對表演藝術產生忽視。在這樣一種重此失彼的態勢下,不少史論家將自己的研究目光逐漸地轉移到話劇上來,久而久之,話劇文學成為戲劇史的全部內容。但是,在這種發展情勢下,我們還需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現代戲曲的文學性真的比不上話劇嗎?現代戲曲與話劇相比真的沒有任何的觀賞性嗎?由此,在本文中,我主要立足話劇與戲曲的文學史地位,來以“獨創”為標尺重讀現代戲劇文學。
一、話劇與戲曲概述
中國是一個戲劇大國,傳統的戲曲藝術已經走過了將近800年的飄搖歷史,在其風雨飄搖的發展歷史中,其劇種在不斷地演變、擴展,直至今日仍在不斷地繁衍、生長。中國傳統戲曲創作著重強調形神兼備,尤其是寫意,極具抽象性。有的文學家將中國傳統戲比作是一位待字閨中的古典佳人,其曼妙的身姿、低吟的聲調,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與感染中,漫步走來,形成“離形取意”的特色。而較之歷史悠久的戲曲藝術來說,可以稱得上是后起之秀的話劇是一種舶來品,其來源于西方國家,是西方主要的戲劇品種。伴隨著中國幾千的大門被打開,話劇作為一種文學藝術形式被引入到中國,并在中國肥沃的文學土壤中生根發芽,直至1907年,極具現代性和民族特色的中國話劇產生了。話劇在其漫長的發展征程中,其盡管仍保留著西方戲劇的特色,將寫實作為自身的特色,但是在中國傳統戲曲的影響下,話劇與戲曲逐步交融,與中國的文學藝術建立了深厚的關系。正如我國著名的戲劇家和翻譯家,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創建人和藝術上的奠基人之一的焦菊隱先生在談及話劇與戲曲融合的時候所說道的:“以話劇之形,傳戲曲之神。”尤其是以林兆華、徐曉鐘為代表的話劇導演在繼承與發展焦菊銀先生的“話劇民族化”這一思想的基礎上,溝通了中國傳統戲曲與西方話劇,將戲曲美學潛移默化地滲透到話劇創作之中,實現了話劇與傳統戲曲的“詩化聯姻”。由此可以看出,話劇與戲曲在現代戲劇文學發展中并不是相互隔斷的,相互獨立存在的,他們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一定的發展歷史趨勢下是相互融合的,倘若將其涇渭分明地割裂開來,則無法實現虛實互補,為現代戲劇文學的發展開辟一片艷陽天。
二、重讀標尺:獨創
正如上文所談及的,話劇是舶來品,在中國文學土壤生根發芽的時期內,仍是以西方話劇創作為主的,也就是說當前我國的一大部分話劇創作仍是以西方話劇為主的,尤其是整個二十世紀,我國的大部分劇作家都是在西方話劇的影響下來進行文學創作的,可以說是模仿外國做話劇的學徒,在這一時期我們到底從中學到了多少經驗,創作出了多少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作品呢?這需要我們打開“獨創”的眼睛,與“獨創”的眼光來從近百年的琳瑯滿目,質量層次不齊的劇作中來進行探尋。
這里的獨創主要是指在吸收外來文學樣式的時候,不能照搬照抄,不直接復制、粘貼別人的,而是在吸收發展的過程中將自己的文學特色納入其中,在包容之中彰顯民族特色。也就是說在創作劇本的時候先查看一些浩瀚的劇作之中是否存在相似的作品。當代著名話劇導演林兆華在談及戲劇創作的時候說道:“田漢不行,夏衍不行,中國話劇有兩人,一人是曹禺,一人是老舍,曹禺在現代,老舍在當代。就這兩人來說,曹禺更體現了話劇的本源和經典價值。”故在此我們可以列舉曹禺的一些耳熟能詳的作品來對所謂的獨創進行分析。首先,曹禺的《雷雨》可以說是中國話劇史上演出次數最多的劇作,只要稍微對戲劇有所了解的人,只要一看到某些情節就會產生一種似曾相識之感。這是因為《雷雨》是曹禺話劇創作早期的作品,在這一時期曹禺處于學習、借鑒階段,他在這一時期廣泛地閱讀歐美劇本,在深受歐美劇本的影響下,曹禺在創作這部處女座品的時候無論是結果還是情節在一定程度上都或多或少地將所學習的內容直接遷移其中,歐美劇本的痕跡尤為明顯。而隨著其話劇創作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創作經驗的不斷豐富,其第二個劇本《日出》則顯得極具獨創性,甚至可以說是極具奇特性。由于人生經歷和人生閱歷的影響,一些人在品讀該劇作或者觀看該話劇表演的時候,在有限的經驗下,由于沒有活生生的參照其難以深刻地理解陳白露,直到生活經驗、人生閱歷不斷豐富之后,該劇中的每一個角色我們大都可以在現實生活之中窺見原型。這種超前的創作意識被帶入到劇作之中,可以說其極具獨創性。
但是在此需要注意一點,文學并不是科學,科學是有唯一答案的,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不存在似是而非的答案,而文學的判斷標尺往往帶有主觀性,沒有那么的絕對。那當前一些大火由小說改編而來的電視劇,當期廣受關注的時候,其劇本甚至是原版的小說就會受到質疑,抄襲這一字眼涌入我們的眼簾。抄襲明顯地將獨創的保持過于絕對化了,將獨創當做是原創。回歸到戲劇方面,關于原創的討論在戲劇史上還是少之又少的。從我們當前的用于評獎的專業標準來恒定何為原創,古典戲劇中所存在的原創作品可以說是浪里陶沙,少之又少。就拿西方的戲劇作品創作來說,不少作品中都蘊含著豐富的古希臘神話內容,除了古希臘悲劇《波斯人》這一作品之外,可以說無一是原創作品;英國文學史上最杰出的戲劇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最偉大的作家,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學家之一的莎士比亞在創作劇作的劇作的時候習慣于重復講述別人已經講過的故事,這其實也非原創;德國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學家歌德在創作其偉大的劇作《浮士德》的時候,其中的故事早已廣為流傳。這些劇作大師在進行文學劇作創作的時候仍是以耳熟能詳的劇作為基礎對其進行重新編制,而且這些劇作在劇作創作飛速發展的今天,仍廣受歡迎,甚至被奉為經典之作,而那些被奉為原創的劇作卻被蒙上了歷史的塵埃,為人們所遺忘。當前仍有原創和改版這一純技術之分的劇作評價當屬美國電影奧斯卡,但是其他的世界著名的電影評價卻沒有將此作為作品判定的標準。縱觀我國的現代戲劇藝術形式的發展,不少專家、學者大力倡導將“原創”作為評價的標準,戲劇評獎尤甚。這一現象使得我國前半年來習慣于改編,將優秀的內容、形式移植到文學樣式之中的做法改變得虎頭蛇尾,一些保留了傳統劇目的戲劇只能在“原創”標準的驅使下重新尋找新人來進行創作,最終導致“原創”流于形式化,這些形式化的“原創”其實就是偽原創。所謂的偽原創就是指內容、形式所有原創之意,但毫無原創精神。前山西省宣傳部長申維辰當屬偽原創的代表。
縱觀中國的道教和西方結構主義的相關理論內容,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人類所有的藝術產品都不是憑空想象產生的,也不是自發產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由人所創造的,而且其繼承發展都是在已有的藝術產品的基礎上不斷改創的。從這一層次,我們可以將原創視為改創,為其賦予一個明確的稱呼,即獨創。素有巴蜀鬼才之稱的我國著名的戲劇家、辭賦作家,國家一級編劇魏明倫曾在勸解青年劇作者的時候談及了三個內容,即獨立思考、獨家發現、獨特表述。這三個層面從一定程度上嚴格地界定了何為獨創,這與我們所談及的不在于拘泥于形式和內容的原創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例如,魏明倫所創的《巴山秀才》就是一篇極具獨創性的好劇目,雖然其內容主要取材于歷史,但是卻對這些內容進行改創,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內容,甚至是表述上都獨具新穎性,來源于歷史,但又“高于”歷史。
三、創作時期的選擇
在上文我們明確地提到,劇作創作是以歷史或已有的極具思考價值或歷史價值的內容為基礎的,要想劇作具有獨創性,需要在這些基礎之上,結合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來對其進行藝術加工,使其符合當下的實際需求,即在劇作的創作要順應創造時期的選擇,如此所創作出來的作品才具有獨創性。盡管曹禺發揮其才智創作了《雷雨》,但是他卻對該劇作不甚滿意,他在寫完該作品之后,通讀內容,發現整個作品“太像戲”,劇情發展的巧合過于戲劇化。“太像戲”這創作形式主要來源于19世紀歐洲國家廣為流傳的“佳構劇”,該形式深刻地影響了現代戲劇之父易卜生,而易卜生的創作深深地影響著曹禺的創作,由此可以推斷出,西方國家的創作形式過分地影響了中國戲劇文學的創作。在獨創這一尺度的衡量下,我們需要在盡量地擺脫西方國家的戲劇創作模式的影響,在創作初期,盡管不能過分地要求戲劇編創者完全地脫離西方國家的創作模式,但是其在借鑒的基礎之上需要將包含中國元素的內容的納入其中,這樣才能使得所創作的作品極具民族特色,這一創作呼喊得到了“國劇運動”學派的廣泛支持。除了在納入民族特色內容之外,要想所編創的作品極具獨創性,還需要在藝術與政治互動下,編制出極具現實性的劇目,如此在客觀與現實的融合下,使其劇目具有現實價值。以曹禺的《同安共苦》為例,該作品的創作盡管受到了“反右”的抨擊,但是它卻實實在在地是極具中國特色的現代主義話劇,在直面當時社會實際的基礎上,敢于揭開共產黨左右為難、進退兩難的境地,該主題深刻地揭示了當時的實際情況,新舊倫理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這種矛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是極為常見的,將極具歷史性的內容納入作品創作之中,可以為其作品內容賦予靈與肉,作品具有可讀性。在中國改革開放迅猛發展的態勢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戲劇不經意地滑入到了充滿誘惑和危險的市場之中,由此在呼吁現實回歸戲劇創作的基礎上,該需要將政治與市場的發展納入其中,以此所創作出來的劇目才具有獨創性。
總之,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中國的戲劇與西方的戲劇難舍難分,在借鑒西方戲劇模式的基礎上,仍需要將極具民族性的東西納入其中,使其本土化,將中國傳統的戲曲與來源于西方的話劇結合起來,將生活實際或社會實際作為創作的背景,如此作品才具有可讀性,讀起來才能發人深省,給予人深思的機會,這一借鑒與發展正是本文所提出的重點內容——獨創。在獨創這一標尺下所創作出來的作品能更好地滿足戲劇發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