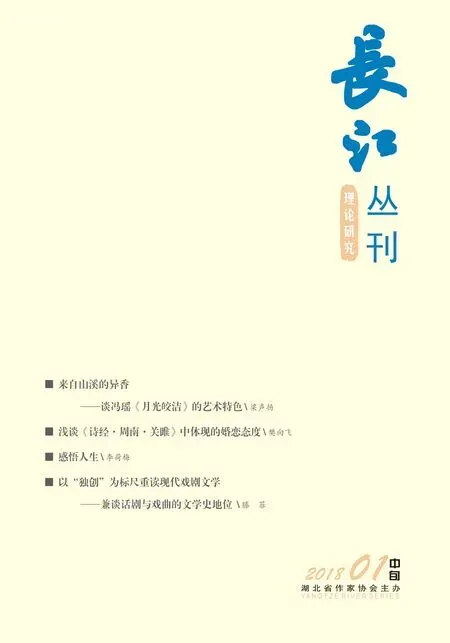從帛書《易傳》看春秋戰國《周易》使用者的變化
陳永敏
一、春秋時期《周易》為卜史之官所使用
《周易》在產生之始,是作為占筮之用的。據《周禮》所載,太卜、筮人掌《三易》之法。由此可見,《周易》主要是太卜、筮人所掌握的,具有嚴格的專門性和職能性。此種狀況在《左傳》多有表述,如《左傳·僖公二十五年》中,晉侯使卜偃筮勤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左傳·昭公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據此可知,“卜偃”“卜楚丘”應是當時太卜一類的官員,卜偃所說“公用享于天子”是《周易·大有》九三爻辭,卜楚丘解筮占時所說“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是《周易·明夷》初九爻辭。顯然,這都是春秋時太卜使用《周易》的明證。
就《左傳》《國語》所見,當時掌易者不僅僅是卜人,還有一些史官。如《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周史以《周易》見陳侯,《左傳·昭公七年》中記載史朝為衛國嗣君之事占解,《國語·晉語》中載董因為重耳筮之,得《泰》之八之事。由此可證,史官掌《易》之史實。
可見,春秋時期人們多從卜筮的角度使用《周易》,反映出當時《周易》的使用者主要是卜筮官和史官,他們作為國家的重要官員,使用《周易》為國家大事占定吉兇,專司職守。
二、戰國晚期《周易》為君主所使用
時至戰國,隨著義理易學深入發展,《周易》文本開始具有一定權威性,其政治功用更加擴大化,戰國晚期主要為君主所用,這點從成書于戰國晚期的帛書《繆和》《昭力》可清楚地看出,這是春秋至戰國《周易》流傳的顯著變化。
《繆和》篇孔子曰(引文中難字和借字,參考劉彬等著《帛書〈易傳〉新釋——暨孔子易學思想研究》,以通行字寫出[1]):“夫《易》,明君之守也。吾慧不達問,學不上與,恐言而貿易,失人之道。不然,吾志亦愿之。”又說:“夫《易》,上圣之治也。”又說:“夫《易》,圣君之所尊也。吾庸與焉乎?”劉彬先生認為:“夫《易》,明君之守也”,謂《周易》乃圣明君主守護不失的對象。[2]“夫《易》,上圣之治也”,“上圣”猶明君,指高明的圣王,謂禹湯文王。“治”,治理。此言《周易》是高明的圣王治理天下的寶典。[3]“夫《易》,圣君之所尊也。吾庸與焉乎?”謂《周易》是圣明的君主所尊崇的,我怎敢談論呢?[4]其說甚是。由以上可見,戰國晚期《周易》一書已經被定位為古代圣王治理天下之書,已經被當時君主所使用,而作為治理國家的重要寶典。
此種現象在《昭力》篇也有例證。《昭力》篇學《易》弟子昭力問先生說:“《易》有國君之義乎?”先生曰:“《師》之‘王三賜命’與《比》之‘王三驅’與《泰》之‘自邑告命’者,三者國君之義也。”[5]傳《易》先生分三節論《易》有國君之義:“《師》之‘王三賜命’”講作為人君要知人善任,賞賜臣下,使君臣相知;“《比》之‘王三驅’”講作為國君要能夠鞭策監督民眾,提前訓導告誡他們,做到“撫人以寬,教之以義,防之以刑,殺當罪而人服”[6];“《泰》之‘自邑告命’”講君主要把自己思慮的倫理道德與治國方略告知民眾,從而告誡、引導、引領他們,而不是“不教而殺”。此三節國君之義主要以“昔之君國者”、“昔者明君”、“昔之賢君”,也就是上古圣賢君主的做法來明示當時的君主應當如何做,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是沒有的,表明當時《周易》已引起國君重視,并作為治國之要書。
在孔子以德代占說的影響下,戰國時各家多從德義角度闡發《周易》,其功用開始主要集中在治國理政之上。《周易》的使用者已由卜史之官轉變為君主。
三、轉變的原因
綜上可知,《周易》主要使用者從春秋至戰國晚期發生很大變化。那么,其原因何在?
帛書《易傳》所含有的政治思想,歷來被學界肯認。“在帛書《易傳》這里,《周易》中的政治智慧并不是來自于神秘的卜筮,而是來自于先王的德思。”[7]這一點為《周易》由卜筮之用轉化為君主政治之用提供了合理的契機。
帛書《系辭》:“《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8]今本《系辭》同。《周易正義》孔穎達疏:“‘以言者尚其辭’者,謂圣人發言而施政教者,貴尚其爻辭之辭,發其言辭,出言而施政教也。”[9]由此可見,《周易》卦爻辭中含有“施政教”的圣人之言。有學者指出,此處“圣人之言即‘古之遺言’,亦即古代先王,尤其是周文王的仁德之教。”[10]
帛書《要》孔子曰:“《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予樂[其]辭也。”[11]劉彬先生指出:“古之遺言”,“古”為《系辭》所言的“中古”,應指殷周之際的中古時代,“言”應指古代圣人的一些義理性的遺教和圣道,這些遺教和圣道成為后來孔子創立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源。孔子認為《周易》卦爻辭中保留了一些這樣的“古之遺言”。[12]由此可證,孔子認為《周易》一書含有古代圣人的政治教誨與思想。
可見,《周易》之所以在戰國晚期被君主使用,孔子在其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孔子對于周代尤其向往,因此,對于《周易》中蘊含的“古之遺言”予以審視、解說就顯得尤為重視。孔子使中國易學的發展實現了由“古義”到“新義”的重大轉折,在易學史上意義極大。孔子中年時期視《周易》為卜筮之書,晚年則對《周易》的態度發生了重大改變。《要》篇載孔子說:“《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存)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于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恃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13]由此可以看出,晚年的孔子對于《周易》著重觀其德、義,他明確指出自己與史、巫等人學《易》的最終歸途不同。在這里,孔子不僅僅看到了《周易》文本的卜筮之用,更看到了文本下所隱藏的德義思想,所蘊含的先王之道。因此孔子對其進行解說,加以發揮,進而對整個戰國時代的易學產生重大影響。帛書《易傳》中《繆和》《昭力》提到的《易》,已不僅僅指文王所寫定的《周易》古經,而且還包含孔子所闡發、弟子所傳播的德義思想和圣王智慧,這也是當時君主使用《周易》的關鍵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