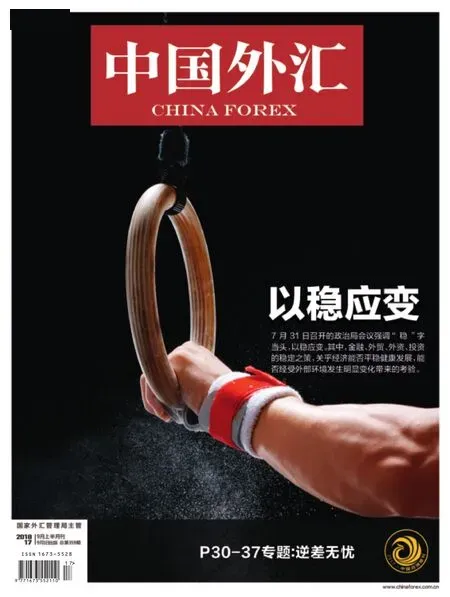上半年我國經常項目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文/管濤 編輯/靖立坤

當前,在國內經濟下行、外部貿易摩擦加劇的背景下,人民幣匯率震蕩加劇,引發了市場對于我國國際收支狀況的關注。根據外匯局公布的國際收支初步數據,今年二季度,經常項目由上季逆差341億美元轉為順差58億美元,上半年累計逆差283億美元。上半年,非儲備性質的資本項目順差(含凈誤差與遺漏,下同)784億美元,剔除估值影響后的外匯儲備(下同)增加494億美元。如何看待我國上半年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全年經常項目和總體國際收支狀況將會怎樣?防范國際收支風險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上半年經常項目少量逆差仍屬于基本平衡的范疇
經常項目逆差不等于對外經濟失衡。理論上講,經常項目差額與GDP之比是評估一國對外經濟平衡(即國際收支平衡)與否的重要指標。對外經濟平衡并不意味著經常項目收支為零,而是經常項目不論順差還是逆差,其差額與GDP之比都應該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以內。上半年,我國經常項目逆差與GDP之比為-0.4%,遠低于±4%以內的國際警戒標準。
經常項目收支趨向平衡是經濟再平衡的成績而非問題。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到2014年之前,我國長期處于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雙順差”、外匯儲備持續大幅增加的對外經濟失衡狀態(見圖1)。因此,早在2006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已指出我國國際收支的主要矛盾已經從外匯短缺轉為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并強調要把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作為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任務。自此,我國積極致力于“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自2007年9.9%的歷史高點觸頂回落,并自2010年起,基本穩定在4%以下;近年來,更是進一步回落至2%以內(見圖2)。這反映了我國經濟從投資和出口驅動轉向投資、消費、凈出口協調拉動的成效,同時也是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和消費升級的結果。但正如匯率趨向均衡合理以后會發生有漲有跌的雙向波動一樣,經常項目收支趨于基本平衡后同樣會出現時而順差時而逆差的情形,并不奇怪。

圖1 中國國際收支狀況(單位:億美元)

圖2 中國對外經濟恢復再平衡(單位:%)

圖3 中國外貿出口部門頂著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壯大(單位:%)

圖4 當前人民幣有貶值壓力卻無貶值預期(單位:人民幣元/美元;%)

圖5 日本經常項目差額構成及其與GDP之比(單位:%)

圖6 日本金融項目構成及其與GDP之比(單位:%)
經常項目收支平衡意味著人民幣匯率趨于均衡合理。1994年匯率并軌,尤其是2005年“7·21”匯改以來,人民幣雙邊和多邊匯率均出現了較大幅度升值。對此,我國轉變了外貿發展方式,從以價取勝轉為以質取勝,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在由1994年的2.8%升至2005年的7.3%的基礎上,繼續升至2015年的高點13.8%(見圖3)。今年上半年,人民幣雙邊和多邊匯率雙向波動,在震蕩中保持了基本穩定。在此背景下,我國出口較快增長,上半年增長13%,增速同比提高了5個百分點;但因進口增速高達20%,致使同期進出口順差同比下降了22%。從前5個月看,出口數量指數平均為107.6,與上年全年平均107.4基本持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日前發布的《對外部門報告》也指出,中國外匯儲備充足,且經常賬戶順差占比較大等外部失衡問題,自金融危機以來已得到大幅改善,人民幣匯率大致與基本面和理想政策所隱含的匯率相一致。
經常項目收支平衡對于實現經濟均衡、協調、可持續發展有諸多好處。一是可以減輕國內經濟對外需的依賴,降低外部沖擊風險。今年上半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拉動為負,但投資和消費拉動作用及時補位,保持了經濟在合理區間內的平穩運行。二是可以促進國際收支整體平衡,改善宏觀調控效果。長期以來,國際收支“雙順差”造成了我國外匯占款持續投放,制約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隨著經常項目收支趨于平衡,減少了外匯儲備積累(見圖2),擴大了國內貨幣政策空間。三是可以減輕外部壓力,爭取國際金融外交的主動。過去較長時間,我國經常項目順差占比過高,成為國際上指責中國貨幣操縱、制造貿易摩擦的一個重要借口。但從2012年起,隨著我國經常項目收支趨于平衡,促進了全球經濟再平衡,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匯率重估的壓力也隨之逐步消失,人民幣匯率已逐漸淡出了雙邊經貿關系的議題。
維持全年經常項目收支略有盈余、國際收支自主平衡的判斷
一是上半年經常項目雖然逆差但趨于改善。二季度貨物和服務貿易由上季逆差218億美元轉為順差305億美元,上半年合計順差為87億美元。受此影響,上半年經常項目逆差與GDP之比較一季度回落了0.7個百分點。從去年三季度到今年二季度的四個季度,我國經常項目順差合計為683億美元,與同期GDP之比為0.5%(1995和1996年,該比例分別為0.2%和0.8%)(見圖2)。
二是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加之主動擴大進口,我國貨物貿易順差有望繼續收窄,但仍將維持一定的順差規模。決定凈出口的“儲蓄-投資”關系是一個慢變量。上次我國年度出現經常項目逆差是1993年,當時國內經濟過熱,國家采取了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進行了宏觀調控。當前,國內投資、消費需求溫和增長,將抑制進口的增長空間。今年二季度,國際收支口徑的貨物貿易順差同比下降21%(一季度為下降37%),上半年順差累計減少27%。再者,我國是制造業大國,基礎設施完備、產業門類齊全、技術工人龐大,在貨物貿易方面仍擁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三是經常項目逆差無損國際收支在整體上的自主平衡。一季度我國國際收支是一逆一順,經常項目逆差341億美元,資本項目順差603億美元,剔除估值影響后外匯儲備增加了266億美元;二季度是“雙順差”,經常項目順差58億美元,資本項目順差181億美元,外匯儲備增加了229億美元。上半年整體上是一逆一順,經常項目逆差283億美元,資本項目順差784億美元,外匯儲備累計增加494億美元。進入6月中下旬以來,人民幣匯率加速回調,到7月底已跌破6.80,但香港市場一年期的無本金交割遠期(NDF)美元溢價僅為1%左右,表明市場并沒有很強的貶值預期(這類似于2013年底2014年初人民幣有較大升值壓力卻無較強升值預期的情形)。2016年底2017年初,當市場在爭議保匯率還是保儲備時,美元兌人民幣的升水幅度達到4%—5%(見圖4)。當前市場預期穩定,人民幣匯率調整沒有刺激資本外流。相反,今年6—7月,人民幣匯率累計下跌6%,境外機構卻累計增持中國國債1445億元,同比增長150%;“滬股通”和“深股通”項下北上資金累計凈流入570億元,增長28%。
打好防范國際收支風險的外匯政策組合拳
一是穩步推進匯率機制改革。市場之所以對我國經常項目逆差感到焦慮,主要是擔心匯率下跌預期下,國內資本外流加劇,有可能影響國際收支的總體平衡。而實際上,惟有匯率缺乏彈性,才有可能出現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或者“雙逆差”的局面。從中國的實踐看,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是有可能也是有效果的。匯率雙向波動、市場預期分化,有助于匯率發揮穩定器的作用,促進國際收支自主平衡,使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形成互為鏡像的對應關系,而根本無需人為去設計和操作。今年上半年,我國就形成了經常項目逆差、資本項目順差的匹配關系,剔除估值影響后外匯儲備資產不降反增。同期,沒有出臺任何加強管制的措施,反而是加速回歸監管政策中性,取消或暫停了前期對跨境資本流動采取的宏觀審慎或行政干預的措施。當然,市場化的匯率需要市場化的意識。各方要以平常心看待匯率的漲跌,增強對匯率波動的容忍度,控制好貨幣錯配風險。
二是繼續鼓勵國際資本流入。要實現彌補經常項目可能出現的逆差,對沖境內資產重新配置需求產生的資本外流,吸引外資流入是重要的政策選項。今年一季度,我國經常項目由順差轉為逆差,同比減少了498億美元,而最終卻實現了外匯儲備的增加,可以說各類外資凈流入同比增加794億美元功不可沒。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和外來證券投資凈流入同比分別增加了399億美元和370億美元。下一步,對外商投資企業要按照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進行管理,擴大國內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改善營商環境;同時,抓住人民幣債券和股票加入全球指數的有利時機,進一步完善國內市場的基礎設施和配套制度,擴大國內股票、債券、商品和外匯等金融市場的開放,更加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
三是有序拓寬對外投資渠道。近年來,作為傳統經常項目順差國的日本,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出現減少,甚至轉為逆差:從2008年起(2010年除外),該項目順差與GDP之比降至1%以下,2011—2015年還出現了階段性的逆差。但同期,日本的經常項目總體依然維持順差格局,2008—2017年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平均為2.5%(見圖5)。這是由于日本堅持用經常項目盈余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見圖6),而這些投資又以利潤匯回的方式彌補了貨物和服務貿易逆差,同期投資收益順差與GDP之比平均為3.2%(見圖5)。中國作為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對外凈債權國,投資凈收益長期為負主要是由我國對外資產負債歷史結構決定的:一方面對外負債以外商直接投資為主,融資成本較高;另一方面,對外資產則是以外匯儲備運用為主,投資收益較低。這導致兩者的軋差為負(并非中國對外投資虧損)。雖然通過開放國內市場,擴大資本流入,也可以對沖貨物和服務貿易逆差;但無論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還是借用外債或引進外來證券投資,都會有利潤、利息或股息紅利的匯出,都會受制于人。因而這種平衡具有一定的脆弱性。當然,放松資本流出限制,需要考慮市場的承受能力、宏觀調控能力和金融監管能力;同時,也需要培養理性的對外投資理念,不能把海外資產配置等同于炒外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