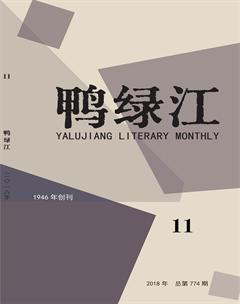直面
華偉章
南方的冬天,氣溫雖然不是特別低,但濕度很大,滲入肌膚有種刺骨寒意。我在一家茶室等她。我的心情并不像茶室的氛圍那么悠閑。她是我男人的情人。在她之前,他在娛樂場所逢場作戲有過其他女人,我多少察覺得到。但我知道,他和她的關系走得特別近,這對我的生活構成了威脅。天色很陰沉,像我的心情。她遲到了十來分鐘。她在茶室出現,不屑的目光朝我這里瞥了一眼,徑直走過來。她脫下外套,里面穿件淡黃色緊身毛衣,勾勒出迷人的身材,雙手攏了一下短裙,優雅地在我對面座位坐下,燈影里顯出一張年輕漂亮的臉龐。
這一刻,我心里感到不平衡。我三十四歲,自恃保養很好,而且又化了妝,還是顯出了年齡的差距。我要了一壺紅茶。
一個月前,我知道了她的存在。這就像陰影籠罩住我的心。我不了解這個陌生女人,最終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她模糊不清的影子一直在我頭腦中縈繞,給我壓抑的生活增添了不確定因素。我變得忐忑不安,心情糟透了。我清楚不能任由事情發展下去。我斟酌再三,決定和她深聊一次,希望能尋找到解決的辦法。我給她打了幾次電話,她敷衍幾句便掛斷電話。我給她發短信,她這樣回復我:見面真的有意義嗎?我記住她這句話。但我沒有領悟她這句話的意思。我急切地想見到她。我繼續發短信,她沒有再回復,我一直在等待。
今天中午,我終于接到她的電話,于是有了這次見面。我心里蒙上莫測感覺。我刻意打扮,去茶館的車上,心里還在琢磨:她會是怎樣一個女人,怎樣能讓她知難而退。我不知道最終的結果會是怎樣。此刻,她就坐在我面前,眉宇透出輕薄高傲,又有一種婉約神態。至少,她不是我想象中那種簡單風騷的女人。她的神情讓我心生怯意,身體里陡然升起嫉妒之火。
茶室里光線有點暗,用屏風恰到好處地隔離開來,既不顯得壓抑又留有個人空間。
“你喝茶嗎?”我努力平復心情,尋找談話的切入點,“冬天喝紅茶暖胃。”
她淡然地笑笑,算是回應,臉上略顯尷尬。她眼睛很柔美,嘴唇涂了唇膏,但并不艷麗。她小心翼翼端起杯子喝了口茶,像是掩飾內心的緊張。我覺察到了,也喝了口茶。我想盡可能放松,讓氣氛融洽一點。我說來點小吃。她婉拒了,光潔的臉上沒有太多表情。我禮節性地詢問:“你在這座城市生活得好嗎?”我看著她,更多是一種挑釁的意味。
她嘴角細膩地翕動,并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下意識地在尋找,或是有些不自在。我說我沒有帶煙。她鎮定下來,解釋說只在某些場合抽煙。我想象她喝得微醺,抽煙的樣子一定很誘人。她目光盯著我。
短暫的沉默。我終于迫不及待地問她:“你們認識多久了?”我心里詛咒:她不應該和他認識。
她知道我會問這個問題,低著頭,還是從包里掏出了香煙。她彈出一支點上,吸了一口,煙霧在她面前彌漫開來。她抽煙的樣子確實很優美。她手腕戴著一只玉的手鐲,纖細的手指嫻熟地夾著煙,白皙的手包括手腕像件藝術品。煙從她嘴唇間裊娜升騰起來。她神情松弛許多。她像在思考。少頃,她說:“其實,他是個很不錯的男人。”
我說:“這我知道。”我反感她這樣評價我的男人,像遭受到明顯的挑逗與侮辱。
“從某種角度說——真的。”她可能沒有意識到,似乎在很快地進入角色。
我很認真地看著她。
“他很有品位,且感情細膩。”她舉起茶杯,貼近杯沿吹了一下,又放下杯子。茶室光線有點暗。她毫不顧忌我的感受,下意識地說著:“他在做完那種事后,會讓我在他胸前躺幾分鐘,輕輕撫摸我的背,這種感覺很舒服,然后把床上的毛發整理干凈。一次,我病了,住了兩天醫院,他抽空送來一大束鮮花,這種感受比自己男人在病床前守候兩天兩夜還要好。他并不顯得粗暴,當然,他也有瘋狂時候。你應該了解男人。”
“是嗎?”
“是的。”
我瞬間陷入了感情的旋渦,眼前飄浮起他倆無數個無眠之夜。我心里抽搐,像被痛苦撕扯,吞噬著男人帶來的苦果。她抬起頭,莞爾一笑,意識到了什么,欲言而止。她說得沒錯,我想起性生活中被忽略的細節,眼睛里竟然被感動得有點濕潤。我說:“你們倆是怎么認識的?”我的口吻變得有些生硬。
“這很重要嗎?”她吸口煙,吐出煙霧,須臾,揶揄地說,“我們這種地方,來消遣的人,都有可能認識。我并不喜歡那種飛揚跋扈的男人。他們幾個人在包房唱歌,我喝醉了,他把我送回住處安頓好。第二天凌晨,我醒來發現,床頭柜上放著一杯水,杯底下壓著五百元錢。”
“是因為五百元錢還是因為那杯水?”我瞪大了眼睛。
“兩者兼而有之。”
“之后……”
“我們開始經常交往,他給我安置了住處。這你應該明白。我開始在娛樂場所收斂許多,除了陪唱喝酒,基本上不再做那種事情。”她臉上的笑很曖昧。
一種失落情緒在瞬間包圍我。我閉上眼睛又睜開,思緒忽遠忽近,回味著生活中被冷漠,被忽略的某些東西,卻在她的神情中發現。我的心像被什么攫住,意識到來自她的危險。我抑制住內心的不快,鄙夷一笑,調侃的口吻問她:“你今年幾歲?”
她明白我的潛臺詞。他已近五十歲,談不上帥氣,甚至其貌不揚,如果除去金錢、人的身份地位,擠在地鐵或公交車上就像一個猥瑣的男人。她轉過頭去凝視著窗外。我發現冰凍的玻璃窗有些朦朧。她像在回味生活,更像在躲避什么。她還過神來,轉過臉來說:“這很重要嗎?”她又這樣問了一遍。她將煙灰彈落在煙灰缸里,語氣里有了一絲玩世不恭。
“至少,這對我很重要。”我說,“我們已經結婚,一起生活了六年。”
“我明白你的意思。”她看出我臉上鄙夷的神情,手指捏著杯沿左右轉動,輕聲地說,“其實,男人和女人潛意識里都有流氓意識。男人喜歡不斷偷走女人的心,同時自己的心被別人偷走。”
我想是的。
她喝口茶,露骨地說:“有錢的男人都喜歡尋找刺激,幾乎變成一種體面的象征。什么倫理道德,撕破了都是虛假的。沒有經濟基礎的男人,只能在地鐵或公交車上猥褻地摸一下女人的大腿。男人都喜歡年輕漂亮的女人。當然,我可能說得有些絕對。”她笑了起來。
我感覺到了她挑逗的目光。燈影里,她臉上的妝化得恰到好處。我知道自己肚子已有贅肉,臉龐抹上一層白粉,皮膚依然有些松弛。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打擊。
“這只是一種買賣。”她直白地告訴我。
“這只是一種買賣?”我揣摩著她這句話的意思。
“為什么不呢?”她自嘲地說,卻直截了當。
“這很無恥。”我尖刻地說。
“是的。確實很無恥。特別有身份地位的,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他們憑什么趾高氣揚,擁有不該擁有的?榨取他們身上的血,算不了什么,無傷大雅……”她語氣依然溫婉,眼睛卻閃現慍怒。煙從她嘴唇吐出來,給人不真切的感覺。她的情緒很快平穩下來。
雖是隆冬季節,玻璃上凝起了一層薄霧,但朦朧的窗外仍然燈光絢麗,亮著尾燈的車輛不斷穿梭而過,不時有穿著時尚的人從窗前走過。
“你愛他嗎?”我試探性地問她。
“愛與性兩者之間很模糊。有時候,愛上一個人和遺忘一個人,幾乎時間與速度一樣快。”她毫不掩飾地說,又注視著我問:“你愛他嗎?”
我說:“我已經說過,他是我男人,我們結婚了。”
“其實,他是愛你的。”她停頓一下,忽然思索著說,并不像是矯情,“有時候,他喝過酒會喃喃自語。”
我撥開飄到眼前的煙霧。我不希望她告訴我這些,但心里還是得到些許安慰。我竭力保持鎮定,感覺自己像委曲求全。我給她的杯子續水,又給自己續上水。我知道熬夜的女人,喜歡咖啡或是濃茶。
她把煙蒂在煙灰缸里摁滅,眨巴著漂亮的眼睛,神情完全松弛下來。她掏出煙盒遞給我,我告訴她,我不抽煙。她說你做小姐的時候也不抽煙?我說我從來不做那種事情。她嘴角微微上翹,面容變得生動起來。她又點上一支煙,手托著下頜,眼睛飄移向窗外,像在自言自語:“其實,男人拈花惹草,不僅僅是男人的錯。女人對待婚姻,像沖進琳瑯滿目的商店,挑選自己的奢侈品,得到后并不一定珍惜;其實,男人是脆弱的,心理壓力很大,喜歡年輕漂亮的女人,更想得到溫存與體貼……他累了會到我這里來,我會脫光衣服,為他輕輕按摩。我們并不一定做愛。他會在我的安撫下酣然入睡。我能讓他撿回想要的感覺——結過婚的男人需要這些。”她轉過臉,唇彩閃著細碎的光亮。
窗外陰沉的天氣,感覺像要下雪。南方城市很少下雪。她說的話,尖酸刻薄,沒心沒肺。我想她遇到過許多男人,說的是真知灼見,至少是推心置腹的話。我心里像被什么狠狠地戳了—下。我記得剛和他認識,在一起吃飯的時候,會細致地把蝦殼剝去,將魚刺剔除,放進他碟子或塞進他嘴里;會端水給他燙腳,為他輕輕地捶背,心甘情愿服侍好他。結婚以后,我確實忽略了,這一切逐漸變得生疏……更多是翻看他的東西,密切地關注他的行跡。我為這一切激動起來。我想我愛他嗎?真切地愛他?能說不愛嗎?這正是我害怕的地方。我緊盯著她眼睛,想盡快將她從生活中抹去,一字一句地說:“你需要多少錢?”
她看著我。
“我一次性給你十萬元。”我下定決心說。
她嘴角蠕動了一下,并沒顯出太多驚訝,目光移向桌上深褐色煙灰缸。
“給你十萬,你離開他。”我重復了一遍我的訴求。我變得頤指氣使。錢不是太大的問題。我清楚娛樂場所的女人貪得無厭。
她明顯拒絕了,表情毋庸置疑。
“這只是一樁買賣,這個價格可以了。我給你十五萬。”我緊皺起眉頭,眼神是鄙夷的,“你想得到多少?”
她吸了口煙,灰藍色煙霧冉冉升騰,似一縷輕蔑。
氣氛有點緊張。我對她倨傲的神情很反感。那種捉摸不透的感覺,煙霧一樣浸入我肌膚。她的居心正是我擔憂的。我知道事情變得棘手,主動權掌握在她手里,比預料的要復雜難堪,心里被憤懣填滿。我清楚自己不能失去他,不惜手段,不能將他拱手讓給別人。“你想和他結婚?”我躊躇不決,謹慎地問著。
“我還沒有想要和他分手。”她轉過臉去,瞧著窗外說。她沒有明確答復,這是她聰明的地方,誰知道以后會發生什么?少頃,她轉過臉來,目光盯著我。
“為什么?”我按捺不住詢問。
“因為,他目前能夠包養我,我很享受這種感覺。”她回答得言簡意賅。
“你想得到更多?”我嫌惡地看著她。我下意識抬起手,又很快垂了下來。我很想在她臉上留下清晰的手印。我說:“你不感到自己很卑鄙?”
“至少,現在我們相處得很融洽。”
“可是,你傷害到了我。”
“這未必一定是我傷害了你。”
“是嗎?”我的聲音有些發顫。
“是的。你心里可能一直在詛咒我:骯臟、齷齪、卑鄙、無恥……這種事不是用自私能解釋的。”
她的聲音透過煙霧鉆進耳膜,我很想用“恬不知恥”形容她。我加重語氣威脅說:“這樣對你會有好處嗎?”
煙從她嘴里慢慢噴吐出來。她臉上沒有懼色,似乎看出我色厲內荏、虛張聲勢。她氣定神閑地反詰:“當然,他這個年齡,能混到今天,已經很不容易。這種事真要鬧起來,對他或者對你的傷害可能會更大。”
我心里充滿了憤懣。
她一針見血地說:“他身敗名裂,你還會愛他?死心塌地跟著他?”
我心里打了個冷戰。她的話擊中了我的要害。我不得不佩服她的心機。這一刻我對她恨之入骨。我眼睛里閃過一絲寒意。我很想能夠殺了她,至少讓她永遠消失。但我清楚這完全不可能。第一,我沒有那么殘忍;第二,殺害她也毀了我自己。“他不會和做小姐——你這樣的女人,真正過日子的。”我惡毒地說。
她反唇相譏:“所以,他和你一起生活后,又在外面聲色犬馬。”
我說:“我跟你說過,我從來沒有做過那種事情。”我恨不能將她生吞活剝。
“我能讓男人陷入溫柔,他愿意為此大把花錢。”她毫不掩飾地說,“我想這就夠了。”
空氣仿佛凝固了。
“其實,我和他分手,對你來說,未必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忽然,她這樣說。
我警覺的目光看著她。
她拿起水壺,在杯子里續水,又給我續滿水。她吸著煙。煙在彌漫。她漫不經心地說:“男人有錢后,女人是一種誘惑,對女人而言,同樣是一種誘惑。這不是我傷害你,或者你傷害別人,核心的問題卻是:你能夠改變現狀?我即便真的和他分手,他也很快會有別的女人。你明白嗎?這樣對你更不安全。至少,我還不想和他結婚,我能拴住他的心,除我之外,他不會有別的女人。這對你來說,并不是最壞的結果。”她看著我眼睛,臉上飄浮起一種笑意。
我感到體內一陣痙攣。從某種角度,她說的具有一定道理。但我還是恨她。我從她抹著粉底的眼瞼,還是窺見了淺淺的黑暈。我心里有種歇斯底里的東西。
茶浸成深色,像紅葡萄酒。
她轉過臉去,凝視著窗外。窗外像有第三個人存在。燈影里,她臉上有種光澤,有種凝神的神情,片刻,她嘴唇嘟囔著,像在對誰敘述:“在外面打工整天忙碌,盼到年底捏著幾個辛苦錢,打扮得花枝招展回家,誰知道你在外面干什么或者干沒干那種事情?我在這座城市寄人籬下,只有年輕這點資本。我想掙錢,我需要錢,幾年后,回家結婚,開家超市,或者拿出一部分錢做點生意。錢能改變人的命運!”她眼睛里忽地閃過一縷光亮。
我捕捉到了她眼睛里閃爍的東西,心底被一種柔軟的東西頂了一下。我驚詫于她有著與年齡不相符的成熟。我感覺對她是了解的,又有種莫測的陌生感。我相信她心里蘊藏著自己的故事。我不由自主地轉過臉去,瞧著窗外,目光穿透朦朧窗外越過漫漫暗夜。我腦海里浮現起貧瘠的家鄉。天是高遠的,縹緲而蒼茫,低矮簡陋的屋子里,爺爺長年病在床上,母親整天唉聲嘆氣,父親蹲在墻角抽著廉價旱煙。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懷揣一個個夢想,潮水般涌入城市,漫延到每個角落。我不清楚,他是夫妻關系不和,還是因為我的緣故,與妻子協議離婚,女兒跟隨前妻生活。我在法院門口偶然遇到她,她眼睛里有種怨毒的仇恨。我比他小十幾歲。我知道和他在一起,能擺脫貧瘠山區,擁有養尊處優的生活。
她轉過臉來,將煙蒂掐滅,扔在煙灰缸里。我瞧著她,忽然,夢囈般說:“離開他吧……”我像是在祈求。我知道,她不會理解“離開他”的全部含義。我想起她的短信回復:見面真的有意義嗎?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對結果早已胸有成竹。風吹在背景黝黑的窗上,發出很輕微的聲響。茶室里很靜。我清楚無法改變現狀。我明白這種故事,一直在發生,會變得寡淡無味。她并不想和他結婚,這還不算最糟的結局,至少目前為止,我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我瞧著她,有點悲哀,有些沮喪,心里五味雜陳。我不安的目光在她臉上逗留,想尋找恰當理由告誡她什么。我最終放棄了。夜深了。我站起身,并不友好地和她握手,窺視到了她臉上的慵惰神情。我買了單。
我轉過臉,忽然有須臾的恍惚,腦海瞬間閃現一個臆想:離開他!是的。離開他!為什么不呢?我渴望幸福生活,夢寐以求想得到,感覺像登上了一艘華麗的船,卻朝著希望的相反方向漂去。我第一次發現他襯衣胸口上,有女人擦過的淡淡口紅,心顫抖得像風雨中飄落的樹葉。我和他爭吵,心里變得壓抑,這種情緒遍布整個身體。我每次嗅到他身上不同女人的香水味,捕捉到他躲閃的變得無恥的眼神,憤怒得渾身哆嗦,像躲在別人看不見的痛苦陰影里。這種狀態,困擾著我的生活,壓迫著我的神經。我閉上眼睛,心里清楚,渴望得到的未必是最珍貴的,光鮮亮麗的背后未必是幸福。我腦海閃現他前妻怨毒仇恨的目光,飄浮起自己光著腳丫,在青山與綠水間奔跑,整個身心在呼吸新鮮空氣。我陡地很想離開他,離開這座城市——我能獨立生存!
走出茶室,寒氣襲人,城市的午夜顯得空曠而孤獨,迷蒙的霓虹燈困乏地閃爍著,像妓女疲憊的眼神。風直接灌進脖子里,涼意在朝全身漫延。我們倆沉默未語。出租車駛來,她鉆進車里,很快被黑暗吞噬。又一輛出租車駛來,我拉開車門……
一切如浸透在夜色里。
【責任編輯】 鐵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