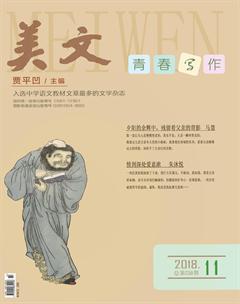閑話“三十而立”
安黎
在中國古代,自西周而始,明代而終,少男少女長到一定的年歲,都要舉行寓意已經(jīng)長大成人的儀式,謂之曰“成人禮”。成人禮有“冠禮”與“笄禮”之別:男子滿二十歲行“冠禮”,表示已進入成人行列,其姿其態(tài),宛若泅水者將頭顱浮出水面那般,被族群發(fā)現(xiàn)并接納,之后便可娶妻生子;女子則在年滿十五歲時行“笄禮”,預示自此以后,就可以離開家族,外嫁別家。
男子是否成人,要看其所戴的帽子;女子是否成人,則要以發(fā)髻來分辨。個頭像竹筍那樣一天天地拔節(jié),男孩子的嘴唇周圍冒出了胡須,女孩子的雙乳愈發(fā)地突顯。在生理的意義上,行完“成人禮”,人確實已進入了成熟期。然而年齡與身體的“成人”,并不意味著心理的成熟,更不意味著人的成長到此為止。
孔夫子對人成長節(jié)點的判斷,是“三十而立”。人活到三十歲才能夠站立起來,那三十歲之前,是一個什么樣的身姿呢?弦外之音是或臥或坐,或跪或蹴,或蜷縮或匍匐,唯獨不是站立。既然已“成人”,又為何又未“立”呢?借用孟子的話說,那是“非不欲也,實不能也”。
膝蓋尚且酥軟,脊梁尚且彎曲,腹腔尚且空洞,頭腦尚且搖擺,腳步尚且踉蹌……人自然就難以挺立。唯有累積了一定的閱歷,歷經(jīng)了一定的熱冷,儲蓄了一定的認知,鍛造了一定的能力,人才敢于站立于社會的潮頭,獨自面對和抵御不可預測的來自四面八方的風吹浪打。而在此前,總有父母寬厚的軀體,仿佛圍墻一樣地遮擋在自己的身前——既擋住了迎面撲來的飛沙走石,又擋住了自己瞭望遠方的視線。
“三十而立”的“立”,究其所指,顯然不是身體之立,而是人生之“立”。也就是說,人至三十,就不能仿佛巨嬰,繼續(xù)慵懶地躺在父母的襁褓里裝睡,依賴于吮吸父母的奶汁和汗?jié)n而茍活,而是不但要在身體上,徹底地扯斷父母臍帶的纏裹,而且要在精神上,掙脫父母手臂的托舉,從而自己處置自己的事務,自己面對自己的難題,自己療治自己的傷口。有了痛,不再輕易呻吟;有了悲,不再輕易流淚;有了心事,不再輕易外露;有了愛恨,不再輕易發(fā)泄……見多了,遇多了,明白了天高地厚,目睹了虎威狐狡,懂得了夏酷冬寒,盡管身體依舊在勉力前行,但心卻越縮越后。相應地,人不是越活越簡單,而是越活越復雜;不是越活越清晰透明,而是越活越云霧繚繞。衣服遮住身體,口罩戴在嘴上,人寧愿做一顆安分守己的果仁,固守于殼中;卻不肯破殼而出,將自己暴露于大庭廣眾之下。
果實的飄香,常常是以繁華的凋謝為代價的——花果如此,人亦如此。
之于人而言,昨日的幼童,今日的壯年漢子;昨日的黃花閨女,今天的家庭主婦。受之于生命交替的逼迫,人無論是否情愿,都要自覺或被動地走向生活的深水區(qū),接受浪花的愛撫,也接受大浪的沖擊。軟弱者,不善泳者,極易被浪花挾持,或半途溺斃,或隨波逐流;但堅強者卻猶如礁石,身千瘡百孔,心亦千瘡百孔,卻依舊巋然屹立。
人生之“立”,猶如筑屋的立柱之豎起。不是所有的木頭,都能充當立柱;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三十而立”。唯有打牢基礎,磨礪好自身的堅硬本領,才能支撐起整個屋宇的不斜不倒。說透了,“立”就是一種責任擔當,該自己挑的擔子要義無反顧地挑在肩上,不能因其沉重而偷懶和推卸。
所謂的“立”,就是要對社會負責,因為社會的優(yōu)劣與自己以及自己子孫的康樂息息相關;就是要對人性道德負責,因為自己人性道德之善惡,猶如溪流之清濁,關乎整條河流之生態(tài);就是要對自己的生命健康負責,因為人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著,而是千絲萬縷般地串聯(lián)著自己深愛的和深愛自己的諸多親朋;就是要對家庭負責,因為家庭成員居之有屋,飯之有食,穿之有衣,用之有度,老之有養(yǎng),少之有愛,等等,正是自己作為人子作為人父作為人夫作為人妻所要面對和擔負的天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