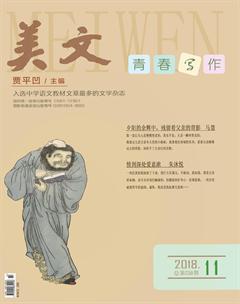向著各自心中的圣地
惠子嫣
中國鮮少出造詣極深的哲學家,更別說名譽世間的大哲人。但有一位值得尊敬,他叫周國平。
周國平從北大哲學系畢業,是言之無愧的頂級人才。畢業后,他研究哲學,復又開始寫作、寫詩,但他始終不張揚,以至年輕人都不大聽過他的姓名。
周國平在散文集《各自的朝圣路》與《人與永恒》中,均寫到了中國少出哲人的原因。
第一要義便是扎根在國人心中的“平衡”,這平衡在西方也有,但不盡相同。西方的平衡將激烈開放與秩序相組合,形成了動態的、有活力的、積極的平衡。而中國則追求家室圓滿,樂天安命的“中庸”平衡。正因如此,國人總缺少那么一點點至關重要的雄心。你或許會問,誰沒有雄心?難道馬云、馬化騰的雄心鐵腕不夠大?的確,但這雄心的成分卻與歷史長卷的苛刻要求大相徑庭,他們的雄心是空間的、地域的、而非時間上的,想名昭千古必是不易。
但有馬云總好過沒有馬云,問題也在于此,十四億人口中,“馬云”的數量仍屈指可數,這與中國當代教育脫不開關系。家長們大多數教授的是:“上個好大學,找個好工作,結婚生子,過完一生。”父母希望孩子們有好生活固無過錯,卻逐漸消磨了孩子的雄心,讓“摘星星”的夢想終成夢想,看不到遼闊的遠方,平凡與平庸不可劃等號,寧成窮困潦倒也不甘俗世的凡人,是不愿意過得安穩卻無所求的。
另一個原因,中國人缺乏信仰,這種信仰并非一定要是基督耶穌或釋迦牟尼,它是一個追求,一個準則,一個沒有條目的法度,它是河的第三條岸。我們的心里沒有神,也沒有朝圣路,我們太過在意要活在當下,腳踏實地,不敢往遠想。有人說,腳下的路比詩與遠方更重要,但沒有詩與遠方,走那么遠的路又有什么意義呢?
周國平說了一個故事。他自己曾對素食主義者感到不解,但和一位中國素食主義推崇者接觸后,他改變了想法。他們之所以素食,根本上是出于對生命的敬畏,將生命視為準則,將生命作為圣地,他們以素食這一方法為媒介,走上了敬畏生命這條朝圣路。每個人心里都應有一個圣地,不必相同,這個圣地或許并不存在,但它會成為精神乃至靈魂上的追求,是讓我們得以辨別正路歧路,善惡黑白的指明燈。
而這圣地也應是一個夢想,一個宏大遙遠卻可一步步觸手及之的夢想。心中有神,同時也有夢,既能砥礪前行不止,也不會半途迷失方向,這便是朝圣的意義。
缺乏信仰,追求平庸,如扎根國人心中的雜草,難以除盡。而我們卻對此毫無反應,仍平庸地過著每一天。我們或許真該仔細想想了,用心而非用大腦。
我們需要一個圣地,一個并非與眾不同、獨樹一幟,卻應是靈魂的圣地,可這卻談何容易。
有時我們或許應抬起頭,抽出半刻鐘,看看窗外的風景,為它真正的蔚藍感動一次,又或許應拾起一本書,《浮生六記》也罷,《隔水呼渡》也罷,《百年孤獨》也罷,一點點地在心中筑一座城,建一座足以令我們心悸的圣地。
筑此圣地固然困難,卻也簡單至極,用心思考,讓思想逐漸靜水流長。
周國平說:吟無用之詩,醉無用之酒,讀無用之書,鐘無用之情,鐘的此情,那第三條岸也并非望塵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