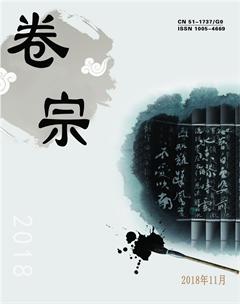論馬克思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法律建設(shè)的啟示
孫浩
摘 要:我國(guó)現(xiàn)階段法律建設(shè)深受西方影響,而西方法律與社會(huì)制度建設(shè)的基礎(chǔ)理論之一就是社會(huì)契約論。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經(jīng)典之一,對(duì)社會(huì)契約論的批判可以對(duì)我國(guó)現(xiàn)階段法律建設(shè)起到去除西方不良影響、加強(qiáng)對(duì)平等的保障的作用
關(guān)鍵詞:社會(huì)契約論;馬克思主義思想;法律建設(shè)
馬克思主義思想是社會(huì)主義理論的源泉,我國(guó)作為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應(yīng)當(dāng)用馬克思思想來(lái)思考解決社會(huì)發(fā)展中的問(wèn)題。在運(yùn)用時(shí)要將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手術(shù)刀來(lái)使用,正確學(xué)習(xí)其他理論思想的優(yōu)點(diǎn),剔除其弊病和缺點(diǎn),而不是完全的去否定和排斥其他理論。
馬克思對(duì)社會(huì)契約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社會(huì)契約論下構(gòu)建國(guó)家權(quán)力的過(guò)程和結(jié)果不是自由平等的。
具體來(lái)說(shuō),馬克思認(rèn)為,在社會(huì)契約論的背景下,人們通過(guò)契約,將自己的自然權(quán)利社會(huì)化為社會(huì)權(quán)利,進(jìn)而構(gòu)建國(guó)家權(quán)力與政權(quán),這個(gè)過(guò)程和結(jié)果都是是不自由的,個(gè)體之間也是不能平等的充分表達(dá)自己意愿的。這是馬克思對(duì)社會(huì)契約論進(jìn)行批判的核心。
馬克思認(rèn)為,資產(chǎn)階級(jí)社會(huì)是不自由,不平等的,首先是社會(huì)個(gè)人的不自由不平等,然后是社會(huì)關(guān)系的不自由不平等。所以,即使每個(gè)人在自由的“自然狀態(tài)”下,擁有平等的“自然權(quán)利”,在與社會(huì)簽訂契約完成自然權(quán)利的讓渡和社會(huì)權(quán)利的獲得過(guò)程中,也會(huì)因?yàn)橘Y產(chǎn)階級(jí)社會(huì)中個(gè)人生存狀態(tài)的不自由,社會(huì)地位的不平等和社會(huì)契約關(guān)系的不自由平等導(dǎo)致最后構(gòu)建的社會(huì)權(quán)利體系的不自由平等,而社會(huì)權(quán)利體系的不自由平等又會(huì)加重個(gè)人不自由平等,進(jìn)而循環(huán)往復(fù)。具體來(lái)說(shuō),馬克思認(rèn)為,資本關(guān)系分工相較于自然關(guān)系分工,帶來(lái)了更多的競(jìng)爭(zhēng)性,使得社會(huì)各個(gè)個(gè)體之間更加孤立,“盡管競(jìng)爭(zhēng)把每個(gè)人匯集在一起,它卻使各個(gè)人,不僅使資產(chǎn)者,而且更使無(wú)產(chǎn)者彼此孤立起來(lái)”,而這種孤立又使得競(jìng)爭(zhēng)進(jìn)一步加劇,“他們作為個(gè)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們有了一種必然的聯(lián)合,而這種聯(lián)合又因?yàn)樗麄兊姆稚⒍闪艘环N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是異己的聯(lián)系”,最終這種劇烈的競(jìng)爭(zhēng)使得“每一個(gè)人的個(gè)人生活同他的屈從于某一勞動(dòng)部門(mén)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各種條件的生活之間出現(xiàn)了差別”,也就是說(shuō),一個(gè)人的個(gè)人生活不再有自己決定,而是取決于外部各種條件,人失去了決定自己生活的自由。盧梭在《社會(huì)契約論》也提出,私有財(cái)產(chǎn)構(gòu)成自由的基本要素,是個(gè)人自由的根本保障,自由地?fù)碛胁⑻幹盟接胸?cái)產(chǎn)是人的自然權(quán)利,這一點(diǎn)也被后來(lái)的社會(huì)契約論者承認(rèn)和繼承。馬克思認(rèn)為這種將“財(cái)產(chǎn)”作為“自由”基礎(chǔ),由物質(zhì)來(lái)決定個(gè)人生活的理論使得資產(chǎn)階級(jí)社會(huì)中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一方面,馬克思認(rèn)為,無(wú)產(chǎn)階級(jí)在資產(chǎn)階級(jí)社會(huì)完全失去了自由,其與資產(chǎn)階級(jí)沒(méi)有平等的權(quán)利,其個(gè)人生活完全取決于外部各種條件。馬克思將把這樣完全受外界偶然性條件支配而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條件的個(gè)人稱(chēng)為“偶然的個(gè)人”,在資本主義社會(huì)里,這些“偶然的個(gè)人”沒(méi)有生產(chǎn)資料,也沒(méi)有私有財(cái)產(chǎn),唯一的“財(cái)產(chǎn)”可能就是自己的勞動(dòng)力,自然就不再擁有自由,那么無(wú)產(chǎn)者要是真有什么自由的話,也就是出賣(mài)自己勞動(dòng)力的“自由”。而在資產(chǎn)階級(jí)社會(huì)中即使有對(duì)無(wú)產(chǎn)者的自由進(jìn)行政治或法律上的保障,那也只是對(duì)他們“自由”出賣(mài)自己勞動(dòng)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對(duì)于資產(chǎn)階級(jí),馬克思除了認(rèn)為他們因?yàn)閾碛胸?cái)產(chǎn),使得他們比無(wú)產(chǎn)階級(jí)更“自由”這一不平等現(xiàn)象外,資產(chǎn)階級(jí)實(shí)際上也沒(méi)有真正的自由,馬克思將資產(chǎn)階級(jí)劃分為“有個(gè)性的個(gè)人”,因?yàn)橘Y產(chǎn)階級(jí)擁有并掌握著生產(chǎn)資料,相對(duì)于無(wú)產(chǎn)階級(jí)其能在更大程度上決定自己的個(gè)人生活,但是這一點(diǎn)除了加劇資產(chǎn)階級(jí)和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不平等外,不算是真正的自由,馬克思認(rèn)為:“各個(gè)人在資產(chǎn)階級(jí)的統(tǒng)治下被設(shè)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因?yàn)樗麄兊纳顥l件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是偶然的;事實(shí)上,他們當(dāng)然更不自由,因?yàn)樗麄兏忧鼜挠谖锏牧α俊保R克思從資產(chǎn)階級(jí)的內(nèi)部關(guān)系出發(fā)來(lái)說(shuō)明這個(gè)問(wèn)題,他將資產(chǎn)階級(jí)的內(nèi)部關(guān)系定義為物的關(guān)系:“不是表現(xiàn)為人們?cè)谧约簞趧?dòng)中的直接的社會(huì)關(guān)系,而是表現(xiàn)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guān)系和物的社會(huì)關(guān)系”,而“物”在資產(chǎn)階級(jí)社會(huì)中就表現(xiàn)為“私人財(cái)產(chǎn)”,說(shuō)明資產(chǎn)階級(jí)的內(nèi)部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就是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那么,資產(chǎn)階級(jí)個(gè)人的自由與財(cái)產(chǎn)有很大關(guān)系,資產(chǎn)階級(jí)個(gè)人的自由就受到個(gè)人的財(cái)產(chǎn)條件的限制,很顯然這不是真正的自由,這種“自由”的唯一后果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所以資產(chǎn)階級(jí)也沒(méi)有真正的自由。除了資產(chǎn)階級(jí)整體沒(méi)有自由平等,資產(chǎn)階層社會(huì)的社會(huì)契約關(guān)系也是不自由平等的,社會(huì)契約論中的契約關(guān)系實(shí)際上是將商品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推廣到社會(huì)政治關(guān)系中形成的,用商品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中的自由平等來(lái)等同于社會(huì)政治關(guān)系中的自由平等,但是這樣的“推廣”會(huì)將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和政治關(guān)系天然的聯(lián)系起來(lái),使得契約關(guān)系帶有資產(chǎn)階級(jí)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中不平等占有的特點(diǎn),使得無(wú)產(chǎn)階級(jí)在契約關(guān)系中沒(méi)有平等只有可言,正如馬克思說(shuō)的:“自由!因?yàn)樯唐防鐒趧?dòng)力的買(mǎi)者和賣(mài)者,只取決于自己的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jié)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xiàn)的最后結(jié)果。但是,一旦離開(kāi)這個(gè)簡(jiǎn)單流通領(lǐng)域或商品交換領(lǐng)域,工人就像在市場(chǎng)上出賣(mài)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gè)前途——讓人家來(lái)揉”。
而馬克思對(duì)真正的“自由”的敘述:是勞動(dòng)就是實(shí)現(xiàn)自由的方式,“勞動(dòng)尺度本身在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須達(dá)到的目的和為達(dá)到目的而必須克服的那些障礙所提供的,但是克服這些障礙,就是自由的實(shí)現(xiàn),而且進(jìn)一步說(shuō),外在的目的失掉了單純外在必然性的外觀,被看作個(gè)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實(shí)現(xiàn),主體的物化,也就是實(shí)在的自由,—而這種自由見(jiàn)之于活動(dòng)恰恰是勞動(dòng)。”通過(guò)勞動(dòng),人類(lèi)能夠消除外界環(huán)境對(duì)自己施加的障礙,使得自己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意識(shí)進(jìn)行,進(jìn)而逐步獲得自由。
馬克思對(duì)社會(huì)契約學(xué)說(shuō)在資產(chǎn)階級(jí)社會(huì)產(chǎn)生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做了深刻的批判,這對(duì)處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階段的我國(guó)具有極強(qiáng)的警示意義——即使人民真的擁有完全自由平等的“自然權(quán)利”和“自然狀態(tài)”,其實(shí)際社會(huì)權(quán)力也會(huì)因?yàn)楝F(xiàn)實(shí)社會(huì)對(duì)權(quán)利不平等的分配和不自由平等的社會(huì)契約關(guān)系變得不自由平等,要修正這種畸形的權(quán)利社會(huì)化過(guò)程,實(shí)現(xiàn)人民社會(huì)權(quán)利的自由平等,必須要做到以下三點(diǎn):1)不以財(cái)產(chǎn)作為個(gè)權(quán)利利的基礎(chǔ)。2)不以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為基礎(chǔ)構(gòu)建政治關(guān)系。3)保證公民的勞動(dòng)權(quán),使公民有能力去消除外界的生活障礙。
這三點(diǎn)反映到法律建設(shè)上就是:1)應(yīng)當(dāng)明文規(guī)定財(cái)產(chǎn)與權(quán)利分離,特別是政治權(quán)利。2)對(duì)于表達(dá)和行使權(quán)利有困難的全體,如貧困人口,應(yīng)當(dāng)特別立法以提供幫助。3)應(yīng)當(dāng)明文規(guī)定政治與經(jīng)濟(jì)分離,對(duì)人民代表大會(huì)中大實(shí)業(yè)家等資本代表和工農(nóng)代表的比例應(yīng)該立法向工農(nóng)傾斜。4)加強(qiáng)保護(hù)公民的勞動(dòng)權(quán),具體而言:(a)保護(hù)公民的勞動(dòng)資料獲取權(quán),即堅(jiān)持生產(chǎn)資料公有制。(b)保護(hù)公民的勞動(dòng)進(jìn)行權(quán),立法保障公民在教育,就業(yè)和失業(yè)時(shí)的利益,保障公民平等充分的進(jìn)行勞動(dòng)。(c)保護(hù)公民的勞動(dòng)產(chǎn)品分配權(quán),按需分配和按勞分配合理結(jié)合。(d)保護(hù)公民的勞動(dòng)產(chǎn)品所有權(quán),完善物權(quán)相關(guān)法律。
經(jīng)過(guò)馬克思思想這一“手術(shù)”之后,社會(huì)契約論下法律理想狀態(tài)是:以“人生而自由”為基礎(chǔ),以“自然權(quán)利換社會(huì)權(quán)利”為立法思想,在具體規(guī)定上注意公民權(quán)利與財(cái)產(chǎn),政治與經(jīng)濟(jì)的相對(duì)分離,并注重以保護(hù)勞動(dòng)系列權(quán)來(lái)保護(hù)公民的自由。這為我國(guó)的法律建設(shè)指明了方向,也將成為我國(guó)未來(lái)一段時(shí)間法律建設(shè)的重點(di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