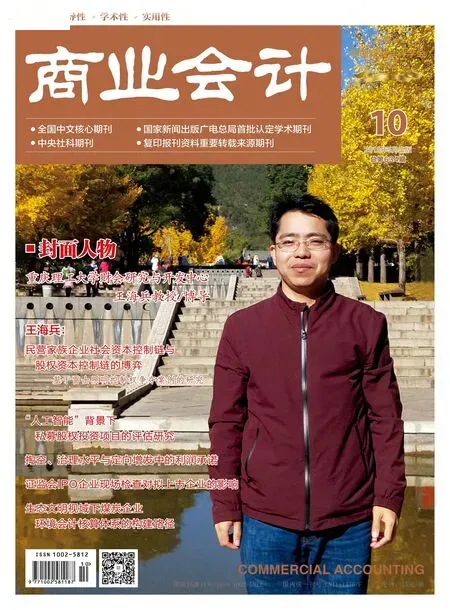民營家族企業(yè)社會資本控制鏈與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的博弈
——基于雷士照明控制權(quán)爭奪案例的研究
(重慶理工大學財會研究與開發(fā)中心重慶理工大學會計學院重慶400054)
一、引言
隨著黨的十九大的召開,我國進入新時代,民營企業(yè)面臨前所未有的進行改革與轉(zhuǎn)型的契機與優(yōu)勢。融資作為企業(yè)改革和發(fā)展的關鍵步驟之一,吸收外部股東的資本投入、打通資本市場通道是民營家族企業(yè)創(chuàng)始股東解決資金問題的核心途徑。同時,由于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的加入,近年來,我國民營企業(yè)在控制權(quán)問題上糾紛不斷,如國美電器、阿里巴巴等。我國民營企業(yè)家的傳統(tǒng)觀念與源自西方的現(xiàn)代企業(yè)理論的觀念相沖突,此外,民營企業(yè)大多數(shù)帶有家族企業(yè)印記,家族治理的情感導向與企業(yè)治理的理性導向,也有著潛在的沖突與矛盾,由此產(chǎn)生利益需求的沖突。因此,逐步建立規(guī)范的現(xiàn)代治理制度,摒棄傳統(tǒng)的治理觀念,解決企業(yè)治理和家族治理之間的沖突,合理配置公司控制權(quán),是民營企業(yè)走向制度化和規(guī)范化發(fā)展的必經(jīng)之路,也是民營企業(yè)健康發(fā)展的基礎。
一般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是股權(quán)控制鏈的范式,主要是以法律和法規(guī)為核心的正式制度為分析基礎。在現(xiàn)實中,以創(chuàng)始股東為核心形成的社會資本控制鏈等非正式安排也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也是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無法充分發(fā)揮治理效應甚至陷入與創(chuàng)始人之間控制權(quán)爭奪糾紛的主要原因之一。社會資本存在于個人或企業(yè)及企業(yè)成員所涉入的社會網(wǎng)絡中,它是協(xié)調(diào)、控制、穩(wěn)固公司內(nèi)外各種關系的重要工具,主要表現(xiàn)在企業(yè)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也是企業(yè)社會資本的主要來源。本文從社會資本控制鏈與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的角度出發(fā),以雷士照明控制權(quán)爭奪案為例,分析我國民營家族企業(yè)治理存在的問題,提出我國民營家族企業(yè)社會資本控制鏈與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耦合的路徑,促進民營家族企業(yè)與現(xiàn)代資本市場的整合與規(guī)范化,推動我國民營家族企業(yè)的改革和發(fā)展。
二、雷士照明案例分析
2016年12月,前雷士照明創(chuàng)始人吳長江案水落石出,被宣判其“挪用資金罪、職務侵占罪”罪名成立,雷士照明多次控制權(quán)之爭落下帷幕。雷士照明作為一家典型的民營家族企業(yè),幾乎折射了大部分民營企業(yè)從初創(chuàng)到公開招股上市等的成長歷程,同時,控制權(quán)之爭也反映了以創(chuàng)始人吳長江為核心的社會資本控制鏈與賽富、施耐德等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形成的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之間的較量,具備時效性和代表性。因此,本文選擇雷士照明控制權(quán)爭奪案例作為研究對象,剖析社會資本控制鏈與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對我國民營家族企業(yè)治理的影響,完善和規(guī)范民營家族企業(yè)的治理結(jié)構(gòu),促進我國民營家族企業(yè)健康發(fā)展。
縱覽雷士照明控制權(quán)爭奪事件全過程,創(chuàng)始人吳長江與賽富、施耐德等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之間主要經(jīng)歷了三次控制權(quán)博弈。
第一次控制權(quán)之爭:吳長江VS胡永宏、杜剛。
1998年底,吳長江和胡永宏、杜剛共同創(chuàng)立雷士照明,各自持股33.3%,三人分工協(xié)作,共同領導企業(yè)向前發(fā)展。2005年,雷士已在照明行業(yè)占據(jù)一席之地,頗具規(guī)模。2005年4月,吳長江與胡永宏、杜剛二人在公司發(fā)展戰(zhàn)略和收益分配問題上產(chǎn)生激烈沖突,胡永宏、杜剛二人聯(lián)合罷免了吳長江,將其驅(qū)逐出雷士照明。但在吳長江離開雷士照明數(shù)日后,全體經(jīng)銷商、供應商力挺吳長江,要求吳長江重回雷士掌權(quán)。最終,雷士照明第一次控制權(quán)之爭以胡永宏、杜剛二人各自以8 000萬元出讓股權(quán),離開雷士照明落幕。此次控制權(quán)爭奪,吳長江獲得雷士全部股份,但1.6億元股權(quán)轉(zhuǎn)讓費使公司陷入嚴重的現(xiàn)金流危機。為此,吳長江不得不引入外部資本,2006年至2011年先后引入軟銀賽富、高盛和施耐德等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吳長江的股權(quán)被稀釋,為雷士第二次控制權(quán)爭奪埋下了伏筆。
從雷士照明創(chuàng)立之初發(fā)展至今,吳長江擁有大量社會資本,在企業(yè)中擁有創(chuàng)始人權(quán)威,為其構(gòu)建社會資本控制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社會資本控制鏈具有利益共生性,吳長江尊重和維護利益相關者與團隊的利益,與供應商、經(jīng)銷商等形成密切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模式(趙晶等,2014)。因此,吳長江能夠憑借供應商、經(jīng)銷商等的支持重返雷士,開創(chuàng)了企業(yè)發(fā)展史的先河。
第二次控制權(quán)之爭:吳長江VS賽富、施耐德。
2012年5月,雷士照明突然對外宣告吳長江辭職,來自于軟銀賽富的閻焱和來自于施耐德的張開鵬分別出任公司董事長和CEO,由此展開了雷士照明創(chuàng)投雙方的博弈,在業(yè)界引起轟動。雷士照明上市后,吳長江仍持原有的治理觀念,獨斷專行,受到了機構(gòu)投資者的指責,矛盾逐漸積累,爆發(fā)了第二次控制權(quán)爭奪。吳長江被迫離職后,雷士照明的社會資本鏈出現(xiàn)斷裂,利益相關者加入爭奪。公司員工和各大供應商、經(jīng)銷商紛紛舉行罷工和停止供貨、進貨,這一舉動讓依賴以供應商、經(jīng)銷商和員工為核心的社會資本資源的雷士照明陷入生產(chǎn)經(jīng)營困境。為了恢復公司正常運營,公司董事會不得不就吳長江重回雷士的問題進行重新談判。最終,在第二次控制權(quán)爭奪中,吳長江再次憑借其穩(wěn)固的社會資本控制鏈(利益相關者)回歸雷士照明,重獲部分控制權(quán)。
吳長江在雷士照明上市后,仍將其視為個人企業(yè),無視現(xiàn)代企業(yè)治理制度的董事會。這也是很多民營企業(yè)家引入資本后,創(chuàng)始人和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產(chǎn)生矛盾的根源。“以人為本”的治理方式雖然讓吳長江鞏固了其擁有的社會資本控制鏈,但其違背現(xiàn)代企業(yè)治理制度,導致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無法融入企業(yè),用人治取代了法治,從而阻礙企業(yè)發(fā)展,損害利益相關者利益,這也是吳長江在第三次控制權(quán)爭奪中失敗的原因所在。
第三次控制權(quán)之爭:吳長江VS德豪潤達。
為了拓展雷士照明業(yè)務,2012年12月底,再次引入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德豪潤達,吳長江股權(quán)大幅降低,控制權(quán)再次易主。隨著德豪潤達董事長王冬雷入主公司董事會,參與雷士照明治理,吳長江與王冬雷的利益沖突日益凸顯。2014年8月,沖突徹底爆發(fā),王冬雷指責吳長江濫用職權(quán),謀取私利;吳長江則控訴王冬雷越權(quán)管理,企圖掏空雷士。8月底,雷士照明董事會正式做出罷免吳長江一切職務的決議,并于10月底完成了法人變更。與前兩次控制權(quán)爭奪不同的是,德豪潤達此時擁有的股東資源遠超吳長江,且其控制了維系雷士照明發(fā)展的幾乎所有關鍵資源,而吳長江利用私權(quán)進行關聯(lián)交易,損害了其在利益相關者中的形象。在此次爭奪中,王冬雷擁有的社會資本控制鏈和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高度契合,因此,大部分供應商、經(jīng)銷商等紛紛倒戈,支持王冬雷,吳長江再次失去雷士照明的控制權(quán)。2015年1月,吳長江涉嫌挪用資金罪被批準逮捕,在此次控制權(quán)爭奪中徹底失敗。
在雷士照明三次控制權(quán)爭奪中,不僅僅是創(chuàng)始股東吳長江與賽富、施耐德、德豪潤達等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的斗爭,更是以吳長江為核心的社會資本控制鏈與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擁有的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的博弈。吳長江依賴資本,卻又不甘受制于資本。可以說,吳長江身上淋漓盡致地體現(xiàn)了民營企業(yè)家傳統(tǒng)草莽式管理與現(xiàn)代管理公司治理制度及資本市場的碰撞和摩擦。雷士照明經(jīng)歷兩次停牌、復牌,市值大幅縮水,創(chuàng)始股東和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兩敗俱傷,為我國上市公司規(guī)范治理敲響了警鐘。
三、我國民營家族企業(yè)社會資本控制鏈與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的耦合路徑
雷士照明作為我國典型的民營家族企業(yè),其三次控制權(quán)爭奪的背后隱藏著我國大部分民營家族企業(yè)發(fā)展到一定規(guī)模后都可能存在的弊病。“創(chuàng)始人持有股份被逐步稀釋但始終擁有核心高管的決策地位”這一民營家族企業(yè)經(jīng)常存在的現(xiàn)象,也正是民營家族企業(yè)控制權(quán)紛爭的關鍵所在。企業(yè)實際控制權(quán)既受股權(quán)因素,又受非股權(quán)的社會文化因素影響(趙晶等,2014),且企業(yè)社會資本控制鏈對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呈逐漸替代的趨勢,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無法發(fā)揮治理效應,由此引發(fā)控制權(quán)之爭。因此,如何將企業(yè)社會資本控制鏈與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耦合,是解決企業(yè)治理和家族治理、創(chuàng)始股東和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保障和推動我國民營家族企業(yè)健康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關鍵舉措。
(一)加強公司治理機制,構(gòu)建資本控制網(wǎng)
雷士照明控制權(quán)之爭看似是創(chuàng)始人與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之間的斗爭,實質(zhì)上卻反映出我國民營家族企業(yè)治理機制普遍存在的缺陷:董事會未能發(fā)揮有效監(jiān)督與制衡機制、創(chuàng)始人與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未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等。真正的市場化是要靠制度來完善的,企業(yè)應通過設置不同的治理機制來處理和預防企業(yè)管理過程中的問題。雷士照明在治理過程中,創(chuàng)始人吳長江不拘于條條框框的約束,將個人權(quán)威凌駕于董事會之上,引來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的極大不滿。隨著民營企業(yè)引入外部資本和上市,股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社會化要求企業(yè)摒棄“野蠻式”生長,建立相應的治理規(guī)則。在現(xiàn)代企業(yè)治理中,實際控制人往往同時運用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和社會資本控制鏈實現(xiàn)對上市公司的治理。在雷士照明案例中,公司內(nèi)外部的社會資本(利益相關者)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創(chuàng)始人利用其所擁有的內(nèi)外部社會資本重返公司獲得控制權(quán),有悖于現(xiàn)代公司治理結(jié)構(gòu)安排。由于社會資本在企業(yè)治理中的大量運用,股權(quán)資本對公司治理機制的影響逐步減弱。以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為核心的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對企業(yè)的治理機制嵌入度不足,最終爆發(fā)控制權(quán)爭奪。民營家族企業(yè)在治理過程中,首先,應平衡和調(diào)節(jié)社會資本和股權(quán)資本的關系。將以創(chuàng)始人為核心的企業(yè)社會資本控制鏈和以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為核心的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契合,實現(xiàn)有效鏈接,構(gòu)建資本控制網(wǎng),產(chǎn)生企業(yè)治理協(xié)同效應和規(guī)模效應,提高企業(yè)治理效率。其次,董事會在民營家族企業(yè)治理過程中發(fā)揮監(jiān)督與制衡機制的作用。合理的董事會結(jié)構(gòu),不僅能夠平衡不同創(chuàng)始股東之間的利益關系,也可以協(xié)調(diào)解決創(chuàng)始股東與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袁建偉、李生校,2014),從而形成戰(zhàn)略聯(lián)盟、利益共贏的局面,促進民營家族企業(yè)與現(xiàn)代資本市場的整合。同時,還應建立與完善創(chuàng)始人與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的溝通機制,盡量促使創(chuàng)始人與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在利益目標、經(jīng)營理念和組織文化等方面保持一致,提升社會資本與股權(quán)資本的耦合度。
(二)合理配置控制權(quán),保護利益相關者權(quán)益
控制權(quán)配置的效率是決定公司治理效率的關鍵,企業(yè)實際控制權(quán)同時受到股權(quán)和非股權(quán)的社會文化的影響。社會資本控制鏈為企業(yè)帶來競爭優(yōu)勢的同時,也會影響公司的控制權(quán)配置。創(chuàng)始股東通過拓展社會網(wǎng)絡,構(gòu)建社會資本控制鏈,成為控制企業(yè)的重要途徑。因此,吳長江能夠利用其構(gòu)建的社會資本控制鏈回歸雷士,重獲控制權(quán)。但社會資本控制鏈的存在,導致機構(gòu)投資者無法獲得企業(yè)真正的控制權(quán)。同時,在創(chuàng)始人權(quán)威治理下極易發(fā)生控制權(quán)私利風險,損害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吳長江在雷士照明治理過程中,濫用其擁有的控制權(quán)進行違規(guī)擔保、關聯(lián)交易等,損害了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導致員工、供應商等紛紛倒戈,最終失去一手創(chuàng)立的雷士照明。是否能夠調(diào)節(jié)社會資本和股權(quán)資本的關系,合理配置公司控制權(quán),實現(xiàn)公司發(fā)展的利益平衡是民營家族企業(yè)治理風險的主要來源。大量調(diào)查數(shù)據(jù)表明,民營家族企業(yè)的經(jīng)營決策權(quán)與管理權(quán)高度集中于家族成員手中尤其是創(chuàng)始人手中。但是,隨著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的引入,創(chuàng)始股東股權(quán)稀釋,企業(yè)股權(quán)結(jié)構(gòu)由初始的創(chuàng)始股東絕對控股向創(chuàng)始股東與機構(gòu)投資者股權(quán)制衡過渡。股權(quán)制衡結(jié)構(gòu)既是一種特殊的產(chǎn)權(quán)安排,又是一種具有權(quán)利制衡作用的治理機制。在股權(quán)制衡階段,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參與企業(yè)治理,與創(chuàng)始股東在經(jīng)營管理、戰(zhàn)略決策等方面容易產(chǎn)生分歧,引發(fā)控制權(quán)爭奪,不利于公司健康發(fā)展。在民營家族企業(yè)成長過程中,創(chuàng)始股東需要妥善處理與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在企業(yè)控制權(quán)和決策權(quán)層面的分配問題,控制權(quán)主體相互監(jiān)督制衡,保護各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quán)益。優(yōu)化權(quán)力配置,形成核心控制權(quán),是實現(xiàn)創(chuàng)始股東和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互惠相容、確保治理轉(zhuǎn)型成功的關鍵與基礎。
(三)完善相關法律法規(guī),規(guī)范企業(yè)治理行為
在現(xiàn)實中,以社會資本網(wǎng)絡為核心的軟控制在民營家族企業(yè)治理中能夠起到緩解融資約束、提高企業(yè)的環(huán)境適應能力等作用,但目前我國對于社會資本控制鏈的監(jiān)督和規(guī)范制度仍不完善。在我國民營家族企業(yè)治理中,社會資本控制鏈普遍存在于民營家族企業(yè)中,以社會資本為代表的關系機制和聲譽機制,將會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法律保護機制,穩(wěn)定創(chuàng)始股東對企業(yè)的控制權(quán);另一方面,社會資本控制鏈的存在,給大股東提供了一條規(guī)避監(jiān)管、提高控制權(quán)私利的“隱形”路徑。社會資本的運用應嚴格遵守相關規(guī)章制度,規(guī)避社會資本積累引發(fā)的代理問題激化,將對外部股東的合法權(quán)益的損害最小化。在雷士照明案例中,吳長江利用其社會資本控制鏈回歸雷士,擾亂雷士照明的公司治理制度,破壞了公司治理中的股東、董事會和高管間權(quán)利相互制衡機制,侵害各利益相關者利益。因此,應制定與完善相關法律法規(guī)制度,提高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對公司治理的嵌入度,促使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發(fā)揮好監(jiān)督者的角色;同時,規(guī)范民營家族企業(yè)創(chuàng)始股東的治理行為,特別是社會資本的運用,依法治企,規(guī)范企業(yè)治理行為,提高民營家族企業(yè)的治理效率。
四、研究結(jié)論與啟示
我國民營企業(yè)經(jīng)過30余年的發(fā)展,在我國資本市場中占據(jù)重要位置,對我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當前經(jīng)濟新常態(tài)的背景下,民營企業(yè)面臨前所未有的進行改革與轉(zhuǎn)型的契機與優(yōu)勢,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的引入逐漸成為推動民營家族企業(yè)治理轉(zhuǎn)型的重要力量。但由于社會資本控制鏈普遍存在于民營家族企業(yè)中,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往往難以發(fā)揮治理效應,導致創(chuàng)始股東與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在企業(yè)利益分配、戰(zhàn)略決策等方面產(chǎn)生分歧,以創(chuàng)始股東為核心的企業(yè)社會資本控制鏈和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擁有的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博弈升級,引發(fā)控制權(quán)之爭。本文從社會資本控制鏈與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的角度出發(fā),對雷士照明控制權(quán)爭奪案進行了研究,分析我國民營家族企業(yè)治理存在的問題,提出我國民營家族企業(yè)社會資本控制鏈與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耦合的實施路徑。
我國民營企業(yè)公司治理普遍存在董事會未能發(fā)揮有效監(jiān)督與制衡機制、民營企業(yè)家依法治企觀念淡薄等問題,導致社會資本控制鏈與股權(quán)資本控制鏈難以契合。因此,加強公司治理機制、合理配置控制權(quán)、構(gòu)建資本控制網(wǎng),是解決企業(yè)治理和家族治理、創(chuàng)始股東和外部機構(gòu)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保障和推動我國民營家族企業(yè)健康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礎。同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guī)制度,特別是社會資本的運用,規(guī)范企業(yè)治理行為,促進民營家族企業(yè)與現(xiàn)代資本市場的整合與規(guī)范化,推動我國民營家族企業(yè)的轉(zhuǎn)型和升級。當前,我國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也存在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在控制權(quán)上的配置問題,兩種資本所掌控的非正式控制資源,將對公司治理機制和控制權(quán)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基于戰(zhàn)略資本管理和雙重控制鏈并存的現(xiàn)實考量,我國“混改”不能只是傳統(tǒng)財務資本的簡單疊加,而應該對依附于國有資本的政府關系資本和依附于民間資本的社會關系資本進行評估、整合和利用,通過法律制度上的頂層設計和商業(yè)倫理文化的融合重構(gòu),使之受控、適配并發(fā)揮協(xié)同治理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