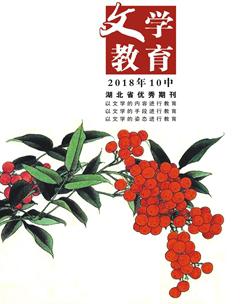《中國有條黃柏河》的生態觀淺析
鄧敏
內容摘要:本文從敘述主線入手,從敘述手法、人物塑造、環境描寫等方面對文本內容進行了分析。同時,對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的黃柏河水利建設,水利人與自然的關系、生與死、責任與堅守的哲理思辨作了一個簡單的分析,利用生態美學的觀點闡述了作者所想要表達的生態觀,闡釋其情感的豐富性和立場的堅定性。
關鍵詞:人與自然 意志 生態美學 文學性與現實性結合
冬如女士的這部作品以黃柏河60年的水利建設和歷史變遷為主線,其中又穿插了許多為黃柏河水利建設做出貢獻的人物,他們帶著鮮明而獨特的性格,或活躍于黃柏河的水利建設過程之中,或沉靜于黃柏河六十年的流淌之中。他們帶著特殊卻又平凡的故事,于工作,于親情,于愛情之中留下了別樣的印記。
讀罷作品,我悲痛于被大石塊砸死的十七歲生命——民工秦昆;我感嘆于心系建設工人,說出“死人是大事!”的枝江縣縣委副書記張忠民;我感動于分別六年再次相見最后又天人永隔的王昌鵬與葉枝之間的愛情……從作者筆下的人物身上,我看到了國家困難時代水利建設的窘境;看到了水利人團結一致,承擔責任的決心;看到了人定勝天的意志和天災人禍對水利人和百姓的折磨……
首先,從敘述手法上來說,這部作品一改單線敘述模式,以黃柏河的水利工程建設為主線,同時穿插了對水利人的刻畫和人物故事的敘述。作者穿插使用第一、二、三人稱。如果說第一人、二人稱自然地拉近了距離,同時便于作者發表評論和感慨,那么第三人稱的使用就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以適當的距離感呈現出了一定的文學色彩。比如在第五章“浴血奮斗”中對于昌鵬和葉枝孩童時代的描寫就展現出一定的文學性:
昌鵬可不一樣,孩童時代就跟山里的女孩兒葉枝呆在一起,兩人在山上放牛、溜樹、砍柴、尋豬草,你追我趕度過了兩小無猜的好時光,還練出了一雙“飛腳”。
這簡單的幾句話,卻有極強的畫面感,裝點以合適的文學想象。作者一改前幾章冷靜的筆調,對王昌鵬和葉枝的兒時相遇相伴的時光進行細膩的刻畫。在這段敘述中,作者更像一個旁觀者,帶著活潑的筆調寫出。上半段的回憶連接下半段的現實,亦真亦幻,著實有一種朦朧之美。
從內容上來看,作者在敘述黃柏河六十年的歷史進程中,展現了幾個特殊的年代里“天”和“人”時而和睦相處、時而對抗的矛盾。作者想要表達的,是民生與水利之間的關系,是水利建設工程一路走來,水利人人定勝天的意志和天災人禍對于百姓的挑戰和折磨。作者選擇了“三年困難時期”和“十年文革”兩個特殊的時期。她寫到了1960年代的陳品芳夫婦,描寫了在那個缺糧缺物資的年代背景里,陳品芳夫婦用河里的水煮野花椒吃的場景。那個又冷又餓的夜晚只是三年困難時期的一個小小縮影。作者還寫了水利的奇跡——黃柏河流域上的第一個大型工程東風渠,是在“文革”時期到處停工停產的背景中誕生的。
作品中始終有一定的哲學思辨意味——關于人與自然矛盾關系的思考。人與自然關系的探尋,到底是以人不遵守自然的規律而對自然進行改造從而受到懲罰為結果,還是以水利人敢于嘗試、勇于奉獻的精神和帶著人定勝天的意志和大刀闊斧的決心進行黃柏河水利工程建設為終點?在黃柏河的水利工程建設過程中,有許多次意外發生。東風渠正式通水當天晚上普溪河渡槽的垮塌,是我們不愿意看見的悲劇,而在第五章提到的天福廟基坑深處地質結構變異一事,則又似是對心情迫切的建設者的一次戲弄。作者在對指揮長閻錦華心情的描寫之中,似又陷入了自己的疑問:“我們能停止前進的步伐呢?——放棄現有壩址,讓宜昌人民在1974年冬季大干水利的意義和實際利益蕩然無存。”一面是殘忍的天災人禍,一面是水利人和普通民眾對建設水利工程的熱情和勇氣。是向自然妥協,還是在和諧相處的基礎上邁出改造自然的步伐,所謂的決心和意志在現實面前是否還有其存在的意義?
回望過去,再看今日。這部作品在最后的幾章中寫了黃柏河流域的水生態問題。作者不僅堅持了“生態平等”的原則,明確表達了政府對于黃柏河水資源保護的鮮明態度,而且還提出了“經濟與生態背向發展”這一現實問題,毫不含糊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在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中,人們為了實現利益的最大化,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作者在第十六章問道:
夷陵區在短短十年內由窮縣變富縣,在經濟建設上一躍而為宜昌之老大靠什么?
作者正是以生態學的觀念重新審視自然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作品中所體現的“生態自我”不僅僅是人類的“自我”,更是整個生態環境的“大我”。作者在表現了對現實生態問題高度關注的同時,亮出了自己的生態主義立場——萬物皆有靈性。如此下去,人類終歸步其后塵。
從人物塑造來看,本部作品運用語言描寫、動作描寫、神態描寫等塑造了一系列立體化的人物。福斯特將其稱為“渾圓人物”。即非靜止的、概念化的,而是立體的、復雜的、矛盾的。以這部作品最動人的人物形象葉枝和王昌鵬為例,在作品的第三章中,首次提到葉枝和昌鵬:
她一上山就跟野兔一樣,漫山遍野地跑,眨個眼睛,就把一起尋豬草的昌鵬遠遠地甩在后邊了……他一著急就滑倒了,葉枝卻不知躲在哪兒“咯咯咯”地笑……從地下爬起來,捂著腿上的傷口在樹林里尋找,卻怎么也找不著,又著急,又喊。
這段對兩人初識的描寫運用了動作描寫和神態描寫,從聽覺、視覺、動覺多個角度刻畫了兩個天真爛漫、活蹦亂跳的小孩形象。“葉枝的手掌心里已經結上了厚厚的繭,昌鵬就拿住了葉枝的手,把那只手拿起來,貼向自己的臉,兩個人的身體也靠近了,近得互相聽得到對方的心跳。”這里將兩個人物的濃烈而又含蓄的愛意點綴得恰到好處。第八章的結尾處,昌鵬永遠離開了葉枝,“顫抖的手指”、“吐出一口鮮血”、“三番五次克制自己沒有倒下去”,這一系列對于葉枝的描寫隨著作者敘述節奏的加快讓生命的隕落始于激烈,歸于平淡,然而平淡中更見其悲痛。
而作品中第十一章對郭德明等人的刻畫則有別于對葉枝和王昌鵬兩人的刻畫,體現了“功能性人物觀”的觀點:人物作為一個行動的單位對整個故事進展具有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