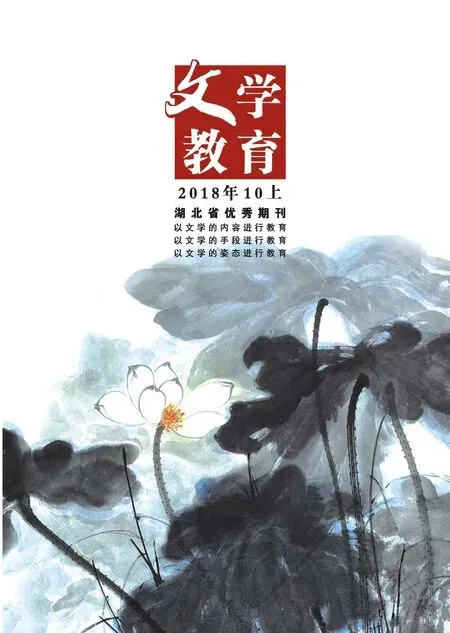變“如同雞肋”為“津津有味”:談說明文的教學
馬志倫
當下說明文教學“如同雞肋”,原因一是高考作文幾乎沒有適合說明文寫作的題目,由于說明文的寫作僅靠一個命題或者是一段材料是很難寫出來的,它需要寫作者的仔細觀察,需要掌握翔實的資料,隨后進行分析歸納整理才能寫好。原因二是高中課本中的說明文選文日趨減少,比如上海現行的高中語文課本,算得上是“純粹”說明文的只有《南州六月荔枝丹》(作者:賈祖璋)和《走向21世紀的機器人》(作者:王磊)兩篇,占整個高中教材139篇中的1.4%。也許是認為說明文,特別是科技類說明文的內容一直在更新,用不了多久就會“過時”。說明文的邊緣化使得它在教學中的地位變得不太重要,一般教法也只是了解內容,理清層次,講解說明方法,并沒有把它當作是一種夯實閱讀與作文功底的文字來予以重視,這實在是一種教學資源的浪費。
其實,說明文教學完全可以做到“津津有味”,這是因為說明文尤其可以作為建立作文基礎的有效抓手。
首先是說明材料的運用(說明文的材料選用既要豐富又要有效)。
豐富便是有些材料可以是借用別人的,更可以是通過自己的仔細觀察得到的。比如法國科普作家法布爾的《蟬》(出自《昆蟲記》),寫蟬的成長過程(蟬的地穴和蟬的卵),就是通過自己的觀察,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才細致地說明了蟬的生長規律:“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個月陽光下的享樂,這就是蟬的生活。”
有效便是在運用某些材料時要加以求證。有的要經過追根溯源,比如《打開知識寶庫的鑰匙——書目》(作者:陳宏天)在說明書目的來歷和作用時講道:“書目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遠在西漢時期就出現了正式的完整的書目。自漢代以后,歷代官修史書,都要撰寫書目,反映藏書的情況。清代編著出規模宏大的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宋元以后版刻書籍盛行,私人藏書家也多起來了,許多藏書家把自己的藏書編成書目,流行于世。這種私人藏書書目數量很多,是對官修書目史志目錄的補充。”看似短短的一段話,卻是在有充分依據基礎上的概括(西漢時期的劉向、劉歆父子編寫的《別錄》和《七略》是記載漢代藏書的總目錄,開我國目錄學之先河;其后有唐代元行沖等編撰的《群書四部錄》;宋代王堯臣等編成的《崇文總目》等)。還有的要通過新發現對原來的說法作補充或修正,比如賈祖璋在《南州六月荔枝丹》一文中,糾正了唐代白居易對于荔枝說法的不準確以及錯誤(白居易在《荔枝圖序》中用比喻的筆法來描寫荔枝的形態:“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殼如紅繒”的說法不確切,因為繒是絲織物,絲織物滑潤,荔枝殼卻是粗糙的,用果樹學的術語來說,荔枝殼表面有細小的塊狀裂片,好像龜甲,特稱龜裂片,裂片中央有突起部分,有的尖銳如刺,這叫做片峰,裂片大小疏密,片峰尖平,都因品種的不同而各異。“膜如紫綃”則是誤將殼內壁的花紋當作膜的花紋了。“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的說法是可取的。
說明文的材料運用有很高的要求,這是由說明文的內容需要科學性這一特點決定的,而且還需經過仔細的推敲與篩選。說明文中的材料選用的方法值得注意,就是收集與整理,分析與歸納,最后形成恰當的有說服力的證據(這與議論文的寫作異曲同工,都需要用辯證的思維考慮問題,并用辯證的方法解決問題)。
其次是說明過程中的邏輯性(一般認為說明文要有知識性、科學性和趣味性)。
說明文注重寫作層次,所謂層次并非只是順序的安排(例如由外到內,由表及里等),還有是須按照人的認知規律來進行引導。《南州六月荔枝丹》從荔枝的外表寫起,進而深入至內部,先從簡單入手,再表現復雜的一面,體現出人們認識事物過程的合理性。說明文中還不乏思辨性。如在《建筑——凝固的音樂》(安懷起),就有這樣一段充滿哲理的文字:“不管是哪一種藝術作品,如果只有變化而無重復,就容易陷于零亂;而如果只有重復沒有變化,作品就必然單調無味。”變與不變既對立又統一,使得一篇說明文字同時具有深刻的思想,讓人回味不盡。
近年上海語文高考中的社科類現代文閱讀選文,不少就是說明文。高考說明文,大多選擇的是事理(事物道理)的說明文(以分析事物的因果關系、介紹科學道理為主的說明文稱作事理說明文,事理說明文主要回答“為什么”的問題)。說明對象大多是抽象的文化或科技現象(社會發展變化中出現的新事物、新現象、新發展等)。大多按照事理邏輯來闡釋、解說對象的特征。在做說明文的題目時,一要抓住文章的標題明確說明點(說明文的標題往往揭示了說明的中心)。二要抓住文章的結構歸納說明點(一般說明文往往都會圍繞一個主要問題或內容進行說明,而有的說明文則需要我們把小說明點歸納起來,構成全文的說明點)。三要抓住說明的順序弄清說明點(事物、事理的本身是有其順序的,人們認識事物、事理也有一定的順序,因此理清了文章的順序,也就有助于弄清說明的中心)。涉及的考點包括說明文的寫作結構、寫作手法、寫作意圖等。
考試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教學的檢驗,既然說明文已經列為高考的一個選項,那么在教學中,我們就必須予以重視。
首先是在選材中應該留有說明文的相當位置,閱讀篇目不僅要有自然學科的,還需有人文學科的。人文學科的說明文,經典的要數呂叔湘的《語言的演變》,在結構(由總到分)和手法(分析綜合)上堪稱是說明文的寫作典范,更可貴的是字里行間顯露出來的思想光芒,在我們了解了語言的相關知識的同時,還懂得了研究事物所需的方法,便是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問題(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永遠在那兒運動、變化、發展,語言也是這樣)。對比那些相對恒定的人文學科的知識介紹,自然科學領域的相關知識的介紹,隨著新的發現需要及時更新,但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歷史,對它的介紹并非毫無意義,更何況滲透于其中的科學思想,永遠不會過時,好似我們今天來說哥白尼的“日心說”,單從“太陽是宇宙的中心”而論,“日心說”是錯誤的,但誰也不能否定,正是因為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說”,有力地打破了長期以來居于宗教統治地位的“地心說”(盡管“地心說”相比“占星術”有了巨大的進步),實現了天文學的根本變革。哥白尼的歷史功績在當時來說,是確認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行星之一,從而掀起了一場天文學上根本性的革命,是人類探求客觀真理道路上的里程碑。其深遠影響則是哥白尼的學說是人類對宇宙認識的革命,它使人們的整個世界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其次在教學中可以將說明文作為寫作的基礎訓練,因為說明文更注重條理性,在闡述一個事物時,往往是按照時間的發展順序或是空間的方位布局,而無論是時間的發展順序或是空間的方位布局,本身蘊涵著邏輯性,這對于提高學生的寫作思維(即不僅僅停留在“寫出文字”這一層次,而是要往“認識事理”這一層次發展)是很有益的。如果在寫作中,能體會進而運用說明文寫作的條理性,那么,作文時就會按部就班,寫出條理清楚的文章,更不必說,說明文的立意(科學性)以及文字(準確性)都是寫作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閱讀與寫作具有相關性,閱讀能力的提升,勢必會帶動寫作能力的提高;同樣,寫作能力的提升也會推動閱讀能力的提高。說明文教學可以成為獲此結果的一條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