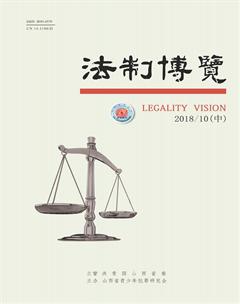比例原則在民法上的適用
左靜玫
摘要:近幾年,我國的民法研究人員更加關(guān)注對比例原則基本原理的應(yīng)用,且對于民事案件的審理,也進(jìn)一步使用與借鑒了這一原則中的基本原理。這就表明:在民法上已可使用比例原則,且這一原則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法司法人員與民法學(xué)者。本文主要對比例原則在民法上適用的原則、可行性及價值進(jìn)行闡述。
關(guān)鍵詞:比例原則;民法上;適用
中圖分類號:D923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8)29-0070-03
比例原則被譽為“公法皇冠”,在本質(zhì)上其能夠平衡強勢利益和弱勢利益。在民法中融入比例原則存在一定的阻礙,包括:跨部門法律“移植”的正當(dāng)性質(zhì)疑等。在人類文明史中,比例原則的觀念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中,并長期存在于稅法、刑法及戰(zhàn)爭法等法律領(lǐng)域中。比例原則的基本理念為只有符合相應(yīng)條件下,即可對個人自由與私法自治進(jìn)行干預(yù),對于一個更高的利益而言,這種干預(yù)手段直觀重要,干預(yù)主要適用于實現(xiàn)所欲求的目的而采取的最為和緩的手段。
一、比例原則在民法上使用的原則
在實踐層面上,比例原則具體作用在國家公權(quán)力會對私人自由與權(quán)力造成影響的活動范圍,其會對行政產(chǎn)生拘束,并對司法與立法進(jìn)行拘束,其中在行政拘束方面,比例原則最初已濫觴在行政法范疇的警察法中,以此來約束不合理的警察權(quán)力的行駛,從而對個人的權(quán)力與公共的利益加以維護(hù);在立法拘束方面,若制定法為依據(jù)不允許過度的要求,則這樣行為已經(jīng)違反了憲法,并沒有法律效應(yīng);在司法拘束方面,法官在個案中應(yīng)對比例原則加以利用,對為獲得某一目的需不需要使用的限制基本權(quán)利的手段、是否存在更加和緩的替代性手段、這一最為和緩手段帶來的不利益和所追求的目的之間是不是相互均衡的進(jìn)行審慎權(quán)衡,以此來明確是否正當(dāng)?shù)母深A(yù)了基本權(quán)利。
比例原則指由若干個子原則而組成的復(fù)雜的標(biāo)準(zhǔn)結(jié)果,并非單一性的原則,主要包括:必要性原則、適當(dāng)性原則、均衡性原則,其中適當(dāng)性原則指對基本權(quán)利進(jìn)行干預(yù)所應(yīng)用的手段應(yīng)符合目的達(dá)成的要求,若手段的選擇和目的沒有關(guān)系,則并不符合適當(dāng)性的要求;必要性原則的要求指對于多個能夠?qū)崿F(xiàn)目的的手段的選擇,需選用干預(yù)比較少的基本權(quán)利的手段;均衡性原則的要求指干預(yù)基本權(quán)利與其所希望實現(xiàn)的目的之間屬于相對稱關(guān)系,兩者的效果構(gòu)成一定的比例,所以我們也將這一原則稱之為狹義的比例原則。在實際案件中,這三個子原則的判斷應(yīng)依據(jù)相應(yīng)的位階順序,也就是現(xiàn)對所應(yīng)用的手段是不是有利于目的的實現(xiàn)進(jìn)行考量,再對有沒有干預(yù)到基本權(quán)利的方式加以考量,最后對這一最輕干預(yù)手段和所希望實現(xiàn)目的之間在效果上有沒有處于均衡狀態(tài)進(jìn)行判斷,僅當(dāng)上一位階的要件符合以后,方可審查下一位階,若上一位階的要件并不符合,則不需要考慮下一位階,我們將這一情況稱之為比例原則在實際適用中的三階理論[1]。
比例原則主要是借助目的與手段之間存在的聯(lián)系進(jìn)行考察,從而對國家行為有沒有具備合憲性進(jìn)行檢視,最終對人民的權(quán)利與自由加以有效保護(hù)。對于比例原則而言,必要性原則與適當(dāng)性原則中的判斷,具體指對客觀目的的取向進(jìn)行考量;均衡性原則的判斷,具體指對價值取向進(jìn)行考量。當(dāng)已對最為和緩的干預(yù)手段進(jìn)行明確后,需對其與所希望達(dá)到的目的間加以進(jìn)一步的權(quán)衡,對這一手段對相對人帶來的負(fù)擔(dān)有沒有高于這一目的所保護(hù)的利益進(jìn)行明確,若高于,那么則違均衡性原則的要求,不可繼續(xù)追求這一目的。
二、比例原則在民法上適用的可行性
隨著人們越來越重視保護(hù)公民的基本權(quán)利,從而促使比例原則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所以對于這一原則在民法上適用和其可行性的討論,需對民事權(quán)利與基本權(quán)利間的聯(lián)系進(jìn)行探究,有關(guān)學(xué)者提出:民事權(quán)利與基本權(quán)利之間的根本性區(qū)別為:(1)義務(wù)主體不同,基本權(quán)利中行使公權(quán)力的國家是唯一的義務(wù)人;民事權(quán)利的義務(wù)人為其他平等的民事主體,主體為私人;(2)保護(hù)強度與廣度間具有一定區(qū)別,基本權(quán)利可應(yīng)用于多個領(lǐng)域中,且剛性十分的強,但平等私人間的權(quán)利卻沒有這種剛性;(3)義務(wù)主體的道德要求具有一定的差異,在“國家-人民”的憲法關(guān)系中,人民的地位在國家之上,人民可向國家提出高于道德的要求,然而國家卻無任何權(quán)利要求私人必須給予弱者特殊的照顧。
民事權(quán)利與基本權(quán)利間確實存在一些差異,兩者的功能也大不相同,然而并不能夠就此判定兩者之間壁壘分明。事實上,兩者的主體擁有同一性,且內(nèi)容上存在諸多交集,如:憲法與私法都承擔(dān)著一個使命,就是保護(hù)人格權(quán),所以現(xiàn)代法治國家均在民法與憲法中對人格權(quán)進(jìn)行了分別規(guī)定。對于民事權(quán)利與基本權(quán)利間具有十分復(fù)雜的關(guān)系,所有把其簡單化或是絕對化的做法、觀點都是不可取的。相關(guān)學(xué)者認(rèn)為這兩者間具有價值、內(nèi)容及主體上的聯(lián)系。基本權(quán)利的主要作用為對人的尊嚴(yán)與自由進(jìn)行維護(hù),民事權(quán)利也是如此。國家也可借助立法來過度限制與干預(yù)主體的私權(quán),其中存在的價值問題為怎樣對國家權(quán)利的范圍加以恰當(dāng)?shù)叵薅ǎ瑥亩鴮θ说淖饑?yán)與自由加以更好地維護(hù)。為此,在形式上基本權(quán)利和民事權(quán)利是分立的,且無法對其在深層的價值問題上的流動性與貫通性進(jìn)行遮掩。基本權(quán)利不僅能夠?qū)夜珯?quán)進(jìn)行防御,并具備客觀規(guī)范價值功能需在民法內(nèi)對整個法律秩序加以發(fā)揮[2]。
有關(guān)學(xué)者對以上論述進(jìn)行了反駁,其他們認(rèn)為:即使基本權(quán)利和民事權(quán)利的內(nèi)容與主體相同,但在本質(zhì)上著兩種權(quán)利依就存在一定的區(qū)別,即:基本權(quán)利指制約與約束國家的公權(quán)力,民事權(quán)利主要是確保私人主體之間的平等;這一觀點看似十分的具有說服力與道理,側(cè)重于國家公權(quán)力僅僅是在基本權(quán)利范疇或是公法范疇中發(fā)揮一定的作用,但在民事權(quán)利范疇中公權(quán)力沒有沒有任何用處。為此,兩者是平行作用在多個范疇的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全權(quán),兩者無任何交集。雖然民法具備多種獨立性,然而其依就需服從政治制度的基本決定;對于民法規(guī)范的創(chuàng)設(shè),主要是由國家機(jī)關(guān)進(jìn)行制定,并非私人意志所創(chuàng)設(shè)。所以說,民法規(guī)范屬于國家立法權(quán)利的產(chǎn)物,只要是國家的權(quán)利,均存在比例原則的適用。
通過在民法中引入比例原則,從而對國家權(quán)力過度干預(yù)民事主體的自由空間進(jìn)行防止與限制。事實上,大量的民法制度中已涵蓋到了比例原則的基本思想,對不允許過度的基本要求加以呈現(xiàn)。同時,對于顯失公平、重大誤解等民法范疇中均在多種程度上呈現(xiàn)出比例原則的思想與要求。且在比較法中,民法范疇中比例原則的適用已是一種普遍做法[3]。
比例原則的適用盡可能的否定了相關(guān)行為的法律效力,這就與私法自治的理念相背離。同時,法院是使用比例原則的主體,但其并沒有明確的對是不是滿足當(dāng)事人所想要實現(xiàn)的目的進(jìn)行判斷。此外,若私人的法律行為意義上的行為與公權(quán)承擔(dān)者的行為相一致,需被一樣的規(guī)則所約束,這就是自由的終點。之所以這樣的主要原因為:原則上的公權(quán)承擔(dān)者在同一環(huán)境下需對所有的相對人加以平等對待,不可存在差異或是歧視,然民事主體卻不受這一要求的限制。一個人可與一個有意締約者締約,或是對一個有意締約者的要約進(jìn)行拒絕,且無需對理由進(jìn)行闡述。然而,這種權(quán)利的行駛未得到對方的同意、未與其加以協(xié)調(diào),這就使得事實上的單方強制形成,對于這一情況,可以使用比例原則來加以一定的矯正。所以,若兩者的地位存在極大的差異,那么地位高的一方將可借助合同自由與私法自治來得到自己不正當(dāng)利益,這就導(dǎo)致民法上的利益平衡機(jī)制受到破壞,對于這一情況,立法者必須有效的干預(yù)合同自由[4]。
三、比例原則在民法上適用的價值
(一)比例原則和私法自治
私法自治指權(quán)利主體具有一定的權(quán)利,其可以結(jié)合自己的意志對其私法上的事務(wù)加以自主地與自己負(fù)責(zé)地安排,其關(guān)鍵意義為提供了一種受到法律保護(hù)的自由,個人具有自主決定的權(quán)利,而法律秩序的主要目的為:讓個體實現(xiàn)其意志的目的提供權(quán)利支撐。從而可知,私法自治理念具有十分強烈的理性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氣息。相關(guān)設(shè)想為:一個理性的人可最為合理的布置自身的利益,而擁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可借助平等協(xié)商與自由談判來最適宜的配置兩者的利益,從而有效的維護(hù)社會秩序和社會利益。然而,這一設(shè)想已被證實是不現(xiàn)實的。在機(jī)會與資源的占有上,個體是無法實現(xiàn)平等的,更多的資源被強勢一方所壟斷;個體要能夠生存,就必須屈從于他人,并對一系列苛刻條件進(jìn)行接受,進(jìn)而難以實現(xiàn)契約自由化與人格平等,貧富差距不斷增大,將涌現(xiàn)出諸多社會矛盾。若完全讓多種力量開展自由競爭,將無法確保出現(xiàn)可承受的結(jié)果。最終衍生出一系列嚴(yán)峻的社會問題,國家干預(yù)已無法發(fā)揮作用,破壞了社會的穩(wěn)定秩序。市民要求國家對自身的基本生存提供一定的保障,且在其競爭失敗是可對其進(jìn)行相應(yīng)的安置,這就使得國家逐漸介入到民法范疇中,干預(yù)并調(diào)整了市民生活和其關(guān)系[5]。
當(dāng)前,威脅到私法自治構(gòu)成的來源有:(1)國家公權(quán)力;(2)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私人。其中國家公權(quán)力另行政手段與立法手段等,不間斷且廣泛地應(yīng)用于到民法事務(wù)與民法范疇中,這就讓私法自治的范疇在本質(zhì)上一直具備各種國家強制;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私人會在一定程度上濫用自己有具備的優(yōu)勢地位,這就對相對人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進(jìn)而對私法自治的有效實現(xiàn)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6]。
(二)民法基本原則和比例原則
在民法體系中民法基本原則屬于比較特別的構(gòu)成部分,其集中體現(xiàn)了民法的本質(zhì)、特點,呈現(xiàn)出市民社會、市場經(jīng)濟(jì)的根本需求,陳述了民法的基本價值取向,可判斷高度抽象且最為常規(guī)的民事行為價值與標(biāo)準(zhǔn)。民法基本原則由于其內(nèi)容具有不明確性、適用上的靈活性,這就導(dǎo)致民法典能夠適應(yīng)當(dāng)前的社會關(guān)系與社會條件。在對比例原則在民法上適用的意義與價值進(jìn)行探究時,必然需要對其同民法基本原則間的聯(lián)系進(jìn)行分析,如果有關(guān)民法基本原則能夠?qū)嵺`中的問題加以完全應(yīng)對,這就表明比例原則在民法上并沒有適用的必要。因法律關(guān)系具有多樣性,所以誠信原則的內(nèi)容一定要保持模糊,這能夠當(dāng)社會價值體系的不斷變化,其也就隨之發(fā)生改變,以此來適應(yīng)這一變化,并對個案中當(dāng)事人的利益訴求加以及時地處理,然而其卻對當(dāng)事人行為自由的因子加以一種隱藏不合法的干預(yù),這就讓交易的不可預(yù)測性與不安定性留下了不安定因素。故此誠信原則有利也有壞[7]。
(三)利益衡量理論和比例原則
利益衡量理論的內(nèi)涵指在法律規(guī)定存在漏洞或不周延條件下,法官可依據(jù)案件的實際狀況,對自己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權(quán)進(jìn)行行駛,也就是:在事實上,利益平衡指在司法過程中法官用于評估利益的取舍及價值,以此來判斷應(yīng)對哪一種利益進(jìn)行優(yōu)先保護(hù)。由于利益衡量是在彼此沖突的權(quán)利間加以平衡與對比,這就能夠?qū)δ囊环N權(quán)利可以優(yōu)先保護(hù)進(jìn)行明確。為此,在功能上比例原則和利益衡量理論具有相同點。利益衡量理論適用的前提為兩種及兩種以上權(quán)利間存在沖突;現(xiàn)如今,社會關(guān)系愈加繁瑣,且利益訴求也變得多種多樣,這就必然呈現(xiàn)出權(quán)利間的沖突。同時,比例原則的教義學(xué)功能指讓權(quán)衡過程恰當(dāng)化、權(quán)衡內(nèi)容具體化,這
就讓多種相互沖突的法益與利益能夠處于平衡狀態(tài)均衡,且利益衡量的參考框架就是比例原則,可以對法官的自由裁量加以恰當(dāng)?shù)闹萍s,使得當(dāng)事人與法官能夠清楚的看到預(yù)期[8]。
四、結(jié)語
綜上所述,比例原則在民法上的適用具備可行性及關(guān)鍵的實踐價值、理論意義,其對維護(hù)私法自治不被過度濫用與干預(yù)的防火墻進(jìn)行了構(gòu)建,為法官對行為人是否存在違反誠信原則的判斷提供了理由與工具,比例原則與利益衡量理論間為彼此補充與相輔相成的聯(lián)系。同時,比例原則能夠保證有關(guān)主體的自由與權(quán)力不被過度干預(yù),這就能夠?qū)λ椒ㄗ灾蔚膬r值加以維護(hù)。為此,在今后的民法典中,需把比例原則明確規(guī)定作一項基本原則。
[參考文獻(xiàn)]
[1]鄭曉劍.比例原則在民法上的適用及展開[J].中國法學(xué),2016(02):143-165.
[2]張翔.機(jī)動車限行、財產(chǎn)權(quán)限制與比例原則[J].法學(xué),2015(02):11-17.
[3]摩西·科恩-埃利亞,易多波·拉特,劉權(quán).比例原則與正當(dāng)理由文化[J].南京大學(xué)法律評論,2012(02):35-57.
[4]鄭曉劍.比例原則在現(xiàn)代民法體系中的地位[J].法律科學(xué)(西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2017,35(06):101-109.
[5]邱靜.論比例性原則在私法關(guān)系中的運用——以英國和歐洲人權(quán)法院案例為視角[J].當(dāng)代法學(xué),2016,30(01):112-120.
[6]王靜波.探析比例原則在民法上的適用及展開[J].法制博覽,2018(05):202.
[7]楊翱宇.論比例原則在民法中的地位[J].河北法學(xué),2017,35(12):82-96.
[8]柳婷婷.比例原則在權(quán)利不得濫用原則中的司法適用[J].湘南學(xué)院學(xué)報,2018,39(01):3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