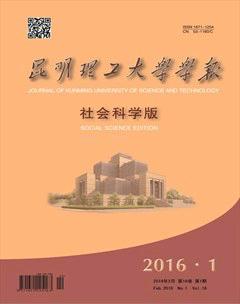糾纏于權力與權利之間
蘭榮杰
摘要:公開審判既是被告人的權利,也是社會公眾的權利,甚至包含國家的諸多權力利益。綜合權衡之下,刑事審判應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在具體操作中,則以比例原則為核心,注意公正審判、公眾知情權、被告人負擔、政府利益等多元訴求的平衡。以此觀之,中國當下刑事審判實踐中存在不公開范圍界定不清、不當限制公開對象、公開程度被人為限制或過度公開等現(xiàn)實問題,有必要以公開審判的基本屬性及比例原則為依據(jù)加以規(guī)范。
關鍵詞:審判公開; 權利; 權力; 比例原則
中圖分類號:D925.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1-1254(2016)01-0035-09
Entanglement Between Right and Power: Public Trial in China
LAN Rongjie
(Law School,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right to a public trial belongs not only to the accused and the general public, but concerning multiple government interests as well. A careful balance requires that criminal trials be open to the public with applicably prescribed exception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shall prevail in practice, balancing multiple interests including the defendants burden and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the publics right to information together with the government interests. Criminal trials in China sometimes are inappropriately restricted, either in terms of the constituents of audience or degree of openness, and sometimes are displayed to an excessive degree furthering extrajudicial purposes. Necessary regulatory actions shall be taken to bring the current practice bac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public trial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Keywords:public trial; right; power;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一、 公開審判權:誰的權利/權力?
我國《憲法》第125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guī)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刑事訴訟法》第11條沿襲《憲法》的表述,但進一步將不公開審理的立法授權限定在《刑事訴訟法》本身,杜絕了非基本法律授權不公開審理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行文與《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相關條款略有差異,后兩者將公開審判權視為被追訴者的權利①,而前兩者似乎并無該意思。筆者認為,這并非是一種文字表述上的偶然差異,而是立法者反復推敲的謹慎選擇,深刻體現(xiàn)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對審判公開的定位更為模糊和寬泛:不僅限于被告人的權利,很大程度上也是公眾的權利,甚至也屬于法院權力的范疇。
(一)作為被告人權利的公開審判權
不管是基于歷史起源還是現(xiàn)實功能,公開審判權都應該是一種被告人的訴訟權利。通說認為,公開審判權概念在歐洲的提出源自對中世紀秘密審判——比如英國的星座法庭、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法國的秘密逮捕令的反思[1]。不過也有論者提出,作為一項法定權利的公開審判的歷史起源已經(jīng)無從查證,不僅因為歷史過于久遠,更因為公開審判自遠古以來一向被認為理所當然,幾乎不成為一個問題
Harold Shapiro,Right to a Public Trial,41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782 (1952).
。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公開審判對于被告人權利保障至關重要,一是使得出庭證人在公眾的圍觀下更難作偽證
法律史上的“巨人”,如布萊克斯通、邊沁和威格摩爾都有關于這一功能的經(jīng)典表述。參見2 ?Jones' Blackstone 1983 (1916); 2 Bentham, 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 355 (1827); 6 Wigmore, Evidence Sec. 1834 ?(3rd Ed. 1940).,
二是使得法官、陪審員、公訴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在公眾的監(jiān)督下加強自我約束,避免恣意裁判或其他濫權行為。具體到中國刑事訴訟而言,由于證人出庭率極低,前一項功能體現(xiàn)不多;但考慮到公檢法三機關的“流水作業(yè)”傳統(tǒng),以及“配合多于制約”的現(xiàn)實,公開審判的監(jiān)督功能可能更為突出,是保障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的關鍵性程序機制。既然如此,公開審判首選是對被告人的保護,是避免強大的國家權力不當侵害被告人權利的一種制約機制。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對于審判公開的限制應當遵循最小化原則,即除非有明顯更為重要的價值受到現(xiàn)實威脅,而且僅在沒有合理的替代方案時,法院才得進行不公開審理;不僅如此,不公開的程度和手段也僅以保護該更重要利益的必要為界限,不得隨意增加
比如,歐洲人權法院和美國最高法院就采用這一標準。參見Campbell and Fell v united Kingdom (1984) (Appl. Nos. 7819/77 and 7878/77, 28 June 1984;Press-Enterprise Co. v. Superior Court of California, 464 U.S. 501 (1984).。
然而,一場公開的審判并不總是對被告人的保護。拋開被告人隱私曝光不說,刑事審判作為一場“貶黜人格的典禮”[2],也必然導致對被告人尊嚴和名譽的貶損。在相對更為注重社會評價的東方社會,尤其是在“面子”文化最為濃厚的傳統(tǒng)社區(qū),被告人面對的旁聽人員的多寡,不僅直接影響其尊嚴貶損的程度,甚至還會影響其悔罪態(tài)度、改造意愿乃至重返社會的難易程度。極端情況下,一場圍觀者眾且群情激昂的審判對被告人的懲罰效果,可能絲毫不亞于正式的自由刑或財產(chǎn)刑。不僅如此,在洶涌的民意和輿論壓力面前,裁判者也容易失于公正,或是主動投民意之所好,或是被動迎合,總之都難免對被告人的偏見(或偏袒)。正是因此,審判公開與不公開,可能都是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應基于個案差異作出不同選擇。審判公開的具體程度和方式,也應符合比例原則,僅以實現(xiàn)正當之價值為限,不得刻意或明顯地附加懲罰或羞辱等法外功能比如德國《法院組織法》僅規(guī)定“法庭的直接公開”,如果將刑事審判置于法院以外的群眾集會場所,或者經(jīng)由擴音器播放至大街上,學界通說認為都構成對審判公開原則的不當擴張。[3]。
(二)作為公眾權利的公開審判權
從權利的本質出發(fā),權利享有者得以自愿放棄。既然如此,若公開審判僅僅是被告人的權利,其當然有權要求閉門審判。不過,正如美國最高法院所說,“盡管被告人在一些情況下有權放棄公開審判,但并不擁有強制法院閉門審判的絕對權利。”
Singer vs. U.S., 380 U.S. 24, 35 (1965).
原因在于,刑事審判是否公開、如何公開的問題不僅涉及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同樣也涉及社會公眾對政府事務和公共信息的知情權,尤其是對與社會治安和個人福祉息息相關的警察事務及司法程序的知情權。作為保障現(xiàn)代民主政治良性運行的基礎之一,公民知情權既是對政府日常行為的監(jiān)督,也是批評權、選舉權等其他政治權利的前提條件
Anthony Lewis, A Public Right to Know about Public Institutions: The First Amendment as Sword, 1 Supreme Court Review 1 (1980).
。在刑事訴訟中,不管從傳統(tǒng)還是現(xiàn)實來看,公民行使知情權最便捷、最容易的方法之一即是旁聽刑事審判。正是因此,要求法院公開審判不僅是被告人的權利,同樣也是社會公眾的權利。
公眾不僅是刑事審判的旁觀者,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相關者。當一個社區(qū)發(fā)生犯罪,社區(qū)成員的憤怒和怨恨通常隨之而來。針對罪犯的一場公開審判恰好成為一種“解壓閥”,“為社區(qū)成員的關切、敵視和怒氣等提供一個適時的出口。”
Richmond Newspapers Inc. vs. Virginia, 448 U.S. 555 (1980).
一旦該出口闕如,人類的天性會讓公眾四處尋求發(fā)泄怒氣的機會,而這甚至意味著原始的私力救濟。換句話說,公開審判也有消弭社會對立情緒、修復被犯罪破壞的社會關系的功能。社會公眾,尤其是犯罪所在社區(qū)的成員,有權期待一場公開的審判,并親眼目睹正義得到實現(xiàn)。但也必須看到,公眾要求公開審判的權利并不等于直接塑造判決的權利。民意必須止步于對司法程序的監(jiān)督,而不能進一步侵犯法官的獨立裁判權。由此之故,審判公開的具體方式和程度必須注意約束民意的烈度,避免過于洶涌的民意破壞公正審判這一最為根本的價值。
一般案件中,被告人和公眾對公開審判的訴求是一致的,即都要求審判公開。但與被告人不同,公眾在公開審判中并無利益受損之虞,因此,一般不會有閉門審判的需求。如此一來,當被告人因為保護特殊利益的需要而主張不公開審判時,必然就會同公眾的公開審判權發(fā)生沖突。解決的方向依然在于比例原則,即權衡雙方利益的大小,首先注意尋找兩全其美的替代方案;確實需要犧牲一方權利時,也必須以保護更大利益為必要。質言之,解決沖突所獲的收益必須大于付出的成本,而且成本必須最小化,且與收益成合理的比例關系。
(三)作為法院權力的公開審判權
刑事審判公開與否和如何公開的問題,同樣涉及明顯的國家利益。一方面,公開且公正的審判有助于培養(yǎng)和提升公民對司法的信任,從而惠及法治國家建設的大業(yè);另一方面,對罪犯的公開審理和處罰也具有強大的教育功能,是實現(xiàn)刑罰之一般預防目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更何況公眾的圍觀也可能促進被告人認罪伏法,間接地協(xié)助案件糾紛的解決。換句話說,在國家的眼里,被告人除了是訴訟的當事人,也可能是實現(xiàn)訴訟外國家目的之工具;公眾除了是旁觀者,同樣也是國家希望教育和拉攏的對象,甚至還是國家解決刑事糾紛的幫手。由此可見,國家在個案中的訴求并不必然與被告人或公眾利益一致。
此外還必須看到,由于國家有責任保護被害人、未成年人等弱勢群體,因此,在涉及被害人隱私、未成年人等特殊問題的個案中,以及涉及國家秘密事項時,不公開審理可能更為符合國家利益。在極端情況下,代表國家介入刑事訴訟的公檢法機關的利益可能有別于整體的國家利益,也與被告人或公眾的利益相沖突,導致在個案審判是否公開、如何公開的問題上產(chǎn)生分歧,而擁有權力的公檢法機關通常都能壓制被告人或公眾的利益訴求。
嚴格說來,國家立法對公開審判原則及其例外的確定,正是國家追求自身利益的體現(xiàn)。正是因此,不管是公開審判還是閉門審判,嚴格遵循立法的司法操作即是對國家利益的維護。只不過限于成文法的粗疏,當法律規(guī)范的文本不足以妥當覆蓋具體爭議的時候,還可能需要追問立法的原旨,甚至在必要時訴諸公認的訴訟理論。換句話說,法院在審判公開問題上的決定,不僅要受成文法律規(guī)范的約束,還要受到立法原旨和訴訟理論的拷問。
綜上所述,公開審判權具有復合屬性,糾纏著被告人、社會公眾、國家乃至辦案機關的多重利益,而且相互之間還存在沖突的可能。在綜合權衡各方利益之后,基本方向應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具體操作中則以比例原則為核心,一方面追求最大化公開,但以不影響公正審判、不對被告人施加不當負擔為限;另一方面,追求最小化不公開,即不公開的理由僅限保護更大利益,不公開的范圍和程度也僅以保護該更大利益的必要為限,且不公開的成本和收益之間合乎比例。
二、 公開審判的案件范圍
根據(jù)最大化公開、最小化不公開原則,不公開審理的案件應當盡量壓縮,且僅以保護更大利益為限。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183條和第247條,法定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包括三類,一是有關國家秘密的案件,二是有關個人隱私的案件,三是審判時被告人不滿十八周歲的案件。此外,如果案件涉及商業(yè)秘密,且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法院也可酌情決定不公開審理。不過,對于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和商業(yè)秘密三類例外情況的具體定義和標準,《刑事訴訟法》并未予以明確,因此也導致實踐中的混亂甚至個別案件中的濫用。
(一)國家秘密的例外
根據(jù)《保守國家秘密法》第2條的規(guī)定,國家秘密指“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確定,在一定時間內(nèi)只限一定范圍的人員知悉的事項”
《保守國家秘密法》第9條將國家秘密進一步明確為七種:一是“國家事務重大決策中的秘密事項”;二是“國防建設和武裝力量活動中的秘密事項”;三是“外交和外事活動中的秘密事項以及對外承擔保密義務的秘密事項”;四是“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中的秘密事項”;五是“科學技術中的秘密事項”;六是“維護國家安全活動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項”;七是“經(jīng)國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門確定的其他秘密事項”。此外,政黨的秘密事項中符合上述規(guī)定的,也屬于國家秘密。。
必須承認,這一定義的操作性并不強,也存在擴大解釋和權力濫用的空間。具體到刑事訴訟領域,該法第9條規(guī)定,“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項”屬于國家秘密,但未進一步明確所指范圍和標準,而是授權公安機關自行確定。作為其結果,公安機關普遍將刑事偵查形成的證據(jù)材料視為國家秘密,禁止辯護律師、犯罪嫌疑人家屬及社會公眾獲悉或傳播。
鑒于立法上對何為“國家秘密”的模糊處理,刑事審判實踐表現(xiàn)出明顯的不規(guī)范性和擴大解釋傾向。首先,對于案件性質可能涉及國家秘密的諸多罪名,包括刑法第一章規(guī)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第十章規(guī)定的軍人違反職責罪,第282條規(guī)定的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和非法持有國家絕密、機密文件、資料、物品罪,以及第398條規(guī)定的泄露國家秘密罪等,各地法院通常是一概不公開審理,盡管這些罪名并不必然涉及國家秘密
比如叛逃罪,雖然規(guī)定在《刑法》第一章,但從罪狀的文義理解,不掌握國家秘密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也構成叛逃罪。。
換句話說,實踐中對國家秘密的界定可謂“簡單粗暴”,一是看罪名中是否包含“國家秘密”字眼,二是看是否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和軍人職責問題。不過也有例外情況,尤其是當公開審判的社會效果被重點考慮的時候,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也會公開審理
比如新疆就曾對分裂國家罪、煽動分裂國家罪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進行公開審理。參見《伊犁州公開審判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涉案19人》,http://www.xjks.gov.cn/Item/2335.aspx,2015年10月20日訪問。。
其次,對于普通刑事案件,只要案情或偵查手段可能涉及國家秘密,如果有關保密信息可能需要作為證據(jù)使用,各地法院往往也不公開審理。比如,在涉及特情偵查和技術偵查的案件中,一些法院的做法是禁止將涉密證據(jù)在公開的法庭上出示,也有一些法院則直接選擇不公開審理。總體而言,在涉及國家秘密的問題上,各地法院的普遍做法是從寬解釋,寧可“錯關(不公開審理)”,不可“錯放(公開審理)”。
(二)個人隱私的例外
對于個人隱私的定義和范圍,我國法律長期未予明確。《刑法》和《民法通則》兩部實體性基本法律均未明確涉及隱私概念。1979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首開先河,在第111條規(guī)定涉及“個人陰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但并未具體解釋何為陰私。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52條將陰私修正為隱私,但依然未明確其具體含義。實際上,法律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是在民法意義上理解和使用隱私概念,但民法上對隱私的界定相對寬泛,不僅包括“個人不愿為他人所知曉的私人信息”,還包括“個人不讓他人無端干預的私的領域”[4]。顯然,刑事訴訟中對隱私的界定不能如此寬泛,尤其不能以被告人的選擇為主要判斷標準,否則可能導致很大部分案件都不公開審理。但問題在于,刑事訴訟理論界和實務界并未形成統(tǒng)一、規(guī)范且明確的隱私概念,更多依靠一線法官在辦案過程中依據(jù)慣例和個人理解來確定是否公開審理。
就刑事審判實踐看來,各地法院對隱私的理解通常限于性關系,即只認定與性相關的個人信息需要特別保護,至于生理缺陷、心理疾病、生活習慣、社會關系乃至個人財產(chǎn)等民事意義上可能被視為隱私的信息,在刑事審判中一般不能成為不公開審理的理由。實際上,真正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一是案件性質涉及性關系,比如強奸案、猥褻案、聚眾淫亂案、賣淫案及傳播性病案等。二是案情涉及性關系,比如因婚戀糾紛引發(fā)的兇殺案、重婚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等。必須承認,這種以性關系為實質必要條件的隱私定義,很大程度上與公序良俗原則產(chǎn)生混淆,其保護的法益甚至主要不是當事人隱私,而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這樣一種錯位的定義,既可能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意和理論界的共識,也可能導致對訴訟參與人隱私權利的保護不足。
(三)關于一案多罪的處理
《刑事訴訟法》對不公開審理范圍的界定是“案件”,但對“案件”的具體解釋,實踐中又存在不小分歧。一是理解為案號,即一個案號對應一個案件,其下可以包含一人多罪、多人一罪或多人多罪等情形;二是理解為罪名,即一個罪名,尤其是一個犯罪事實,對應一個案件,其下可以包括多名被告人;三是理解為被告人,即一名被告人對應一個案件,其下可以包括多個罪名。多數(shù)情況下,上述分歧無傷大雅;但在不公開審理問題上,這一分歧卻會導致混亂。最常見的問題是:如果一個被告人被控多個罪名,其中部分罪名不應公開審理,是否全案不公開?就審判實踐看來,各地法院的處理各有不同,如成都中院審理的王立軍案件,一共涉及叛逃、濫用職權、受賄和徇私枉法四個罪名,其中前兩個罪名涉及國家秘密,因此,法庭審理時并未公開,而后兩個罪名則實行公開審理[5]。與此相反,天津一中院審理的周永康被控受賄、濫用職權及故意泄露國家秘密案,雖然也僅有最后一個罪名涉及國家秘密,卻全案不公開審理[6]。
必須承認,如果只對部分罪名不公開審理,必然會給法院的庭審組織帶來不便。比如,盡管針對特定罪名的法庭調(diào)查和法庭辯論可以單獨進行,但被告人在進行最后陳述時,卻難免需要涉及所有指控罪名。又比如,各個罪名之間可能存在事實和證據(jù)上的交叉,庭審也可能需要不斷恢復法庭調(diào)查。如果庭審在公開與不公開之間頻繁切換,除開對司法效率的影響,也可能損害法庭的莊嚴性,并帶給訴訟參與人及旁聽群眾諸多麻煩。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對于一案多罪案件“一刀切”地不公開審理的做法,也有相當?shù)暮侠硇浴5豢煞裾J的是,在公開審理的個案及制度價值面前,至少在多數(shù)案件中,以上種種不便可能都是完全可以接受而且應當接受的成本。
(四)關于部分程序不公開審理
盡管《刑事訴訟法》并無部分不公開審理的規(guī)定,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68條卻規(guī)定,當證據(jù)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或者商業(yè)秘密時,既可以將整個案件不公開審理,也可以僅對相關證據(jù)的法庭調(diào)查不公開進行。嚴格說來,后一種做法更為符合最小不公開原則和必要性原則,可以避免法院以“搭便車”的方式,借口部分證據(jù)不宜公開而將本應公開的其他內(nèi)容封閉處理。不過就審判實踐而言,考慮到部分程序公開在操作上的麻煩,更多法院傾向于全案不公開審理。即使對部分公開的做法,實踐中亦有不少混亂和爭議。
首先是不公開的程度。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刑事訴訟法》第183條和247條規(guī)定的不公開審理,本意是指不對公眾公開,即不開放旁聽,但不包括對當事人和律師等訴訟參與人保密。不過在審判實踐中,一旦證據(jù)涉及秘密偵查或技術偵查細節(jié),一些地方僅允許法官及檢察官查閱,既不允許在法庭上公開出示,也不允許辯護律師私下核實。更為極端的做法是根本不作為證據(jù)移送,僅允許法官和檢察官到偵查機關核實。誠然,這些證據(jù)不會在裁判文書中載明,但對法官心證的影響卻無可置疑,因此本應交由辯方質證。如此變相剝奪被告人質證權的程序,顯然有違公正審判的基本原則。
其次是不公開的環(huán)節(jié)。《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審判公開僅限庭審環(huán)節(jié),并不涉及庭前會議程序。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82條的本意,庭前會議僅限于討論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jù)排除等程序事項,不宜涉及案件實體問題。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84條卻有所突破,將庭前會議的討論內(nèi)容從程序事項擴張到對證據(jù)材料的審查,希望通過征求雙方意見事先確定庭審爭議焦點,以便使庭審更具針對性和效率性。綜觀域外司法經(jīng)驗,一般并不禁止庭前會議討論證據(jù)。但問題在于,我國庭前會議并不對公眾公開,甚至連被告人都不當然擁有參與的權利。一旦允許庭前會議進行實體審理,難免存在架空庭審程序的嫌疑,甚至成為變相不公開審理的陳倉暗道
比如,前鐵道部長劉志軍受賄和濫用職權案,案卷多達477本,庭前會議持續(xù)一天,庭審卻只有三個半小時,以致有人質疑辯護律師“沒有真辯”,甚至可能“配合演戲”。參見南方周末:《庭審僅三個半小時引發(fā)爭議劉志軍案律師自辯:我不認為在表演》,http://www.infzm.com/content/91556,2015年10月20日最后訪問。。
三、 審判公開的對象及方式
“魔鬼都在細節(jié)中”,正是在個案操作層面,法院權力更可能濫用,公開審判權更可能遭到扭曲、架空或規(guī)避,也更容易引發(fā)坊間學界對公開審判權的爭議。
(一)對誰公開?
根據(jù)最高人員法院《人民法院法庭規(guī)則》第8條,凡公開審理的案件,我國公民俱得旁聽。不得旁聽法庭審判的人員主要包括三類:一是醉酒的人,二是精神病人,三是未經(jīng)法院批準的未成年人。換句話說,除非因年齡、生理等因素而存在擾亂法庭秩序的現(xiàn)實危險,我國公民當然具備旁聽資格。審判實踐中,多數(shù)法院并不會事先審查旁聽資格,只要是公開審理的案件,幾乎都會對所有進入法庭的人員開放。筆者的個人經(jīng)驗也證實,一些案件庭審時明顯有未成年人旁聽,但法院并未專門履行批準手續(xù),似有以默許代替審批之意。以此觀之,至少在普通案件中,刑事審判公開原則落實得較為全面和徹底。
不過媒體記者能否自由旁聽是一個模糊問題。《刑事訴訟法》及最高法院的相關規(guī)定并不特別區(qū)分普通公民和媒體記者,畢竟后者在法律上也屬公民,當然具有自由旁聽的權利。尤其是隨著網(wǎng)絡“自媒體”的興起,公民和記者之間的界限已經(jīng)日漸模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jiān)督的若干規(guī)定》第3條還進一步要求優(yōu)先滿足記者的旁聽需求,甚至可在旁聽席上專設媒體席。但在司法實踐中,不少法院不太歡迎未經(jīng)接洽的記者徑行旁聽,有時會要求或建議記者先行通過當?shù)匦麄鞑块T或法院政治部辦理采訪手續(xù),也有法院通過制發(fā)旁聽證等“技術手段”變相阻止記者旁聽。即使法院迫于法律規(guī)定不得已允許記者以普通公民身份旁聽,一般也會禁止記者對庭審進行錄音、錄像或攝影
參見《人民法院法庭規(guī)則》第10、11條。。
相比之下,對于事先獲得采訪許可的記者,法院不僅可以允許錄音錄像,也可提供判決書、庭審筆錄甚至案卷材料等資料,還可安排法官專門接受采訪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jiān)督的若干規(guī)定》第5條。。
個別案件中,一些官方媒體甚至能夠在偵查階段介入采訪,披露一些嚴格說來屬于偵查秘密的案件信息,因此也引發(fā)“媒體審判”“未審先判”等爭議
近年比較典型的案例,包括薛蠻子聚眾淫亂案、郭美美賭博案和房祖名容留吸毒案等。在這些案件中,早在偵查階段,一些媒體就憑借特殊渠道對犯罪嫌疑人、證人和偵查人員等人進行采訪,并播放犯罪嫌疑人悔罪認罪的錄像,因而引發(fā)不少爭議。。
(二)如何公開?
在傳統(tǒng)意義上,所謂審判公開就等于開放旁聽。既然如此,評價法院落實審判公開的程度,首先要看合乎條件的旁聽者能否順利、方便地進入法庭進行旁聽。我國當下的絕大多數(shù)案件中,法院都不會對旁聽者進入法庭有任何實質性限制。在城市法院,唯一的制約條件可能是通過安檢;而在偏遠地區(qū),很多法院連安檢程序都常常省略。在安檢逐漸日常化的今天,多數(shù)公民都能理解并配合。但也必須看到,尤其是在中西部農(nóng)村地區(qū),嚴格的安檢程序還是可能導致部分群眾對于“衙門深深”的猜忌、惶恐或不滿。也正是因此,有學者認為“檢查身份證是對人格的一種損害,會降低公民旁聽意愿。”
南方都市報:《庭審旁聽在中國》,http://www.nandu.com/nis/201405/14/215341.html,2015年10月20日最后訪問。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觀點在國際上亦廣泛存在。比如,德國法院就曾作出判例,認定對證件的檢查、沒收或者影印均可能造成對旁聽者的嚇阻,因此是對審判公開的不法限制,得以成立上訴第三審的理由。[3]
但筆者認為,考慮到法院作為矛盾集中地的現(xiàn)實,以及多地法院發(fā)生安全事故的教訓
最近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湖北十堰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四名法官被當事人持刀刺傷。[8],
即便安檢措施難免有負面效果,依然有堅持和完善的必要。當前因為安檢引發(fā)的猜忌、惶恐或不滿,更多是現(xiàn)代社會管理手段與傳統(tǒng)生活方式及觀念的必然碰撞。解決問題的方向不是放棄社會管理,而是期待人們的觀念跟上社會管理的步伐。
除直接旁聽外,現(xiàn)代通訊技術的發(fā)展也為審判公開提供了新的可能。相當一段時間以來,當限于法庭空間太小而無法滿足大量公眾的旁聽需求時,有條件的法院會采取視頻直播、錄像轉播等方式間接公開
比如,早在50年代,所謂“新中國第一大案”即劉青山、張子善案件公審時,就通過廣播向全國聽眾直播。90年代末重慶綦江虹橋垮塌案,庭審也是通過中央電視臺向全國直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公開的六項規(guī)定》[法發(fā)(2009)58號文]也要求,當法庭空間不足以滿足旁聽需求時,可通過視頻、錄像等方式滿足公眾和媒體了解庭審實況的需要。。
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則讓審判公開更為全面、徹底和便捷。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年底的部署,全國法院需要依托互聯(lián)網(wǎng)建立司法公開三大平臺,即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和執(zhí)行信息公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推進司法公開三大平臺建設的若干意見》[法發(fā)(2013)13號]。。
具體到刑事訴訟中,主要涉及前兩個平臺:一是審判流程公開,包括在網(wǎng)上發(fā)布開庭公告,以及通過視頻、音頻、圖文、微博等方式適時公開庭審過程。比如,廣受關注的薄熙來案件一審,濟南中院就通過微博直播的方式適時發(fā)布庭審情況,獲得坊間學界的普遍好評。一些法院更為徹底,直接在官網(wǎng)提供庭審視頻入口,觀眾不僅可以收看過往案件的庭審錄像,還可適時觀看所有正在公開審理的案件庭審。二是裁判文書公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lián)網(wǎng)公布裁判文書的規(guī)定》要求,除個別例外情況外,各級人民法院的所有生效裁判文書一概需要在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13)26號]。刑事案件例外不公布的情況包括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及其他不宜公開情形。。
就審判實踐來看,由于最高法院未對流程公開尤其是庭審公開設定硬性要求,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直播庭審的案件總數(shù)還不算多,覆蓋面也不夠廣,而且往往取決于受案法院的自愿選擇,因此,難免出現(xiàn)人為決定不公開的情況。相比之下,得益于各級法院的強力推動,尤其是將裁判文書公開情況與目標考核掛鉤以后,多數(shù)法院都能及時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公開裁判文書。如此一來,至少在相當部分案件中,公眾和媒體甚至不需要親身走進法庭就可以方便且直觀地旁聽庭審、獲悉判決。法官直接面對的或許只是區(qū)區(qū)數(shù)名旁聽人員,但在攝像頭的背后卻可能是成千上萬名關注者。法庭的空間界限被打破,公眾與法庭的物理距離被高度壓縮,審判公開也從純粹的法庭旁聽時代進入無限可能的網(wǎng)絡時代。
(三)關于變相不公開
審判公開雖有監(jiān)督司法之本意,但在多數(shù)案件里面,法官并無濫權的意圖和行為,因而無需擔心因公開帶來的公眾和輿論監(jiān)督。但在少數(shù)敏感案件中,比如重大職務犯罪案件、重大涉黑案件或涉眾犯罪案件(如非法集資罪)等,法院迫于各種案內(nèi)外因素的影響,可能不愿公開庭審情況,尤其是不希望對特定的被告人近親屬、利害關系人或市場化新聞媒體公開,以期保證審判的順利進行,并實現(xiàn)法院期待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必須承認,這是當前我國尚待完善的刑事司法體制依然存在的現(xiàn)實,不管我們在理論上和情感上如何難以接受。具體到操作層面,由于《刑事訴訟法》對不公開審理案件范圍的限制極為嚴格,一些法院可能“有心無力”,不得已只能照章辦事。另一些法院卻可能采取“技術手段”變相限制旁聽,“以公開之名行不公開之實”[7]。具體而言,一般有以下一些常見“技術手段”:
1.刻意安排小法庭,通過空間條件強行限制旁聽人數(shù)。一些社會關注度很高的案件,按理應當安排旁聽席位較多的大法庭
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公開示范法院標準》(2010年10月15日法[2010]383號文)第4條中確定的準則。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中也明確要求,各級法院應該根據(jù)申請旁聽者的人數(shù),在既有條件范圍內(nèi)盡量安排符合旁聽人數(shù)的法庭。,
但為達到變相限制旁聽的目的,有些法院刻意選擇小法庭,提供區(qū)區(qū)幾個旁聽席位,致使多數(shù)有旁聽意愿者無法入內(nèi)
有意思的是,這種不太光彩的小伎倆在其他一些國家亦有出現(xiàn)。比如,德國法院就有判例認定,若法院以避免審判受到干擾為由將旁聽席椅子搬走,使旁聽席任意變小,即屬于對公開審判的不法限制。[3]。
當然,若真是限于法庭空間,法院還可通過視頻、網(wǎng)絡等手段實現(xiàn)間接公開,同樣也能滿足公眾的旁聽意愿。但對一個處心積慮限制旁聽的法院而言,只要沒有上級法院的明文要求,顯然都不會作此選擇。
2.事先安排內(nèi)部人員占座。按照樸素的公平原則,當法庭旁聽席有限,少于有意旁聽者的數(shù)量的時候,最佳辦法是實行“先來者先得”
比如,美國最高法院就采用這種辦法。有些案件影響重大,有意旁聽者眾多,很多人需要提前數(shù)天就在法院門口排隊等候,以致于一些富有的律師專門雇人幫忙排隊,酬金可高達50美元一小時。有意思的是,鑒于公眾和媒體的普遍抱怨,美國最高法院于2015年10月決定禁止律師雇人排隊,要求所有希望旁聽庭審的律師必須自己排隊。參見Washington Post: Supreme Court tells lawyers: Stand in line yourselves. You can't pay others to hold a spo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courts_law/supreme-court-bar-bans-line-standing-for-hearings/2015/10/06/a309e0e6-6c15-11e5-aa5b-f78a98956699_story.html, 2015年10月20日最后訪問。,
或者經(jīng)由抽簽決定
這是德國法院的做法。[3]。
只有對被告人或被害人的近親屬,以及一定數(shù)量的新聞記者,才有必要給予優(yōu)先旁聽的權利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jiān)督的若干規(guī)定》第3條。。
不過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如果案件較為敏感,法院可能優(yōu)先安排公檢法機關的內(nèi)部人員旁聽,有時甚至安排對案件毫無興趣的“居委會老太太”事先占座,導致真正有意旁聽者無席可坐,甚至連被告人近親屬都難以旁聽,從而變相實現(xiàn)對不受歡迎的旁聽人員的排斥。也許正是考慮到這些做法的爭議,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中提出,要建立旁聽席位信息的公示與預約制度,似乎意在避免過多的人為操控和暗箱操作。
3.變相不提前公告開庭。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82條的規(guī)定,對于公開審理的案件,法院應當在開庭三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最高人民法院進一步規(guī)定,開庭公告不僅要張貼于法院公告欄,還需要在法院網(wǎng)站、電話語音系統(tǒng)、手機短信平臺、電子公告屏和觸摸屏等審判流程公開平臺上發(fā)布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推進司法公開三大平臺建設的若干意見》第5條。。
不過一旦法院有心限制旁聽,可能就不在網(wǎng)站、公告欄等常規(guī)渠道發(fā)布開庭公告,而是通過無人關注的隱蔽渠道發(fā)布,“拍照存檔即表示已經(jīng)公告了,卻不讓群眾看見”[7],實質上無異于“捉迷藏”。
4.定向發(fā)放旁聽證。根據(jù)《人民法院法庭規(guī)則》第8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嚴格執(zhí)行公開審判制度的若干規(guī)定》第10條的規(guī)定,在個別案件中,因為審判場所、安全保衛(wèi)等方面的限制,法院可在必要時采取發(fā)放旁聽證的方式確定旁聽人員。但對旁聽證的發(fā)放條件、范圍和具體標準,上述兩個規(guī)定并未予以明確。可想而知,一旦面臨敏感案件,法院不愿意開放旁聽,就可能在旁聽證發(fā)放程序中做文章,通過變相指定旁聽人員范圍,限制不受法院歡迎的利害關系人、當事人家屬以及新聞媒體旁聽權利。
(四)關于過度公開
如前所述,對于被告人而言,審判公開是一柄雙刃劍,違法不公開或者過度公開都可能對被告人不利。審判實踐中,既有法院通過所謂“技術手段”變相不公開,也有法院在特定案件中刻意擴大旁聽人群,造成庭審過度公開。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加強人民法院審判公開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就規(guī)定,“對群眾廣泛關注、有較大社會影響或者有利于社會主義法治宣傳教育的案件,可以有計劃地通過相關組織安排群眾旁聽,邀請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旁聽,增進廣大群眾、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了解法院審判工作,方便對審判工作的監(jiān)督。”由此可見,在最高人民法院看來,刑事審判不僅是解決被告人的罪刑問題,同時也是一場教育人民群眾、宣傳法治理念的課堂,甚至還是展現(xiàn)審判工作、宣揚法院成績的舞臺。因此,當作為“劇本”的案情和作為“主角”的被告人都比較合適的時候,法院往往會積極推動超常規(guī)地公開審判。具體而言,通常有以下三種方式:
1.召開公審公判大會,即通過在廣場、劇院、體育館等大型群眾集會場所公開開庭,將本應“劇場化”的庭審“廣場化”[9]。毋庸諱言,這種廣場司法固然有震懾犯罪、教育群眾的現(xiàn)實功能,但卻嚴重傷害被告人的尊嚴,使審判本身變成一種額外的懲罰,也給被告人未來的改造和再融入社會造成巨大的阻礙。不僅如此,在洶涌民意的高壓下,被告人和律師都可能不敢辯護;法官和檢察官為迎合民意,多半也傾向于一力求有罪、求重刑。然而有意思的是,《刑事訴訟法》并未對此有所涉及,僅在第252條規(guī)定執(zhí)行死刑時不得示眾。最高人民法院也從未正式禁止過公審公判大會,僅在1988年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禁止將已決犯和未決犯——尤其是死刑犯——游街示眾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堅決制止將已決犯、未決犯游街示眾的通知》,1988年6月1日。,
并在2003年為治理超期羈押問題禁止“為了營造聲勢而延期宣判和執(zhí)行”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推進十項制度切實防止產(chǎn)生新的超期羈押的通知》,2003年12月1日。。
在2007年頒布的《關于加強人民法院審判公開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最高人民法院一方面強調(diào)“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案件,庭審活動應當在審判法庭進行”,另一方面又允許巡回審理的案件“根據(jù)實際條件選擇適當?shù)膱鏊保坪跻廊徊扇∫环N有明確傾向意見但又不禁止例外操作的態(tài)度。
2.召開觀摩庭,即根據(jù)個案特點,針對性地邀請?zhí)囟ㄈ藛T旁聽觀摩。比如,邀請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觀摩法院的優(yōu)質庭審或大案要案,邀請學校師生觀摩侵害青少年利益的犯罪案件,邀請國家機關或國有企事業(yè)單位工作人員觀摩職務犯罪典型案例,或者邀請政法系統(tǒng)代表觀摩示范庭審并相互切磋學習等。總體而言,雖然觀摩庭的規(guī)模普遍小于廣場式的公審公判大會,旁聽人員一般也不至于太過情緒化,但被告人必然還是會感到不同于正常庭審的圍觀壓力;何況,因為觀摩人員的在場,法院顯然希望按照既定的腳本推進,不希望被告人“臨陣變招”打亂計劃,故而難免會對被告人施加一定壓力。
3.電視直播或節(jié)選。必須承認,即使到了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電視節(jié)目在中國社會的信息傳播和議題設置方面依然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在中老年人群體及傳統(tǒng)社區(qū)中。正是因此,盡管許多法院已在嘗試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直播庭審,但對于庭審效果最具放大效果的媒介,可能還屬電視,特別是收視率最高的中央電視臺及一些省級衛(wèi)視頻道。所以,一旦某個庭審被整體或部分搬上電視尤其是新聞節(jié)目,很可能會迅速獲得全國性的關注,盡管這對于被告人而言并不見得是好事。不過在近幾年來,全國性電視臺已經(jīng)不再全程直播全案庭審過程,頂多只是以新聞報道的形式簡單選取幾個環(huán)節(jié),雖然也是對被告人的一種附加傷害,但至少也算一個可喜的進步。實際上,最高人民法院的態(tài)度也傾向于從嚴把握,比如在2007年《關于加強人民法院審判公開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就規(guī)定電視直播或轉播庭審需要由高級人民法院批準。
參考文獻:
[1]
岳禮玲.刑事司法與人權保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79-80.
[2]羅杰·科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M].潘大松,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251.
[3]克勞斯·羅科信.刑事訴訟法[M].吳麗琪,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43-444.
[4]王澤鑒.人格權法:法釋義學、比較法、案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224.
[5]搜狐網(wǎng).王立軍案17日不公開審理叛逃濫用職權罪[EB/OL].(2012-09-18)[2015-10-20].http://news.sohu.com/20120918/n353454060.shtml.
[6]廈門網(wǎng).天津一中院:周永康案涉國家機密不公開審理[EB/OL].(2015-06-11)[2015-10-20].http://news.xmnn.cn/a/gnxw/201506/t2015 0611_ 4513034.htm.
[7]苗有水.公眾關注的大要案應成為審判公開的典范[N].人民法院報,2015-01-27(2).
[8]張恒,紅思佳.十堰4名法官辦公樓內(nèi)被捅傷[N].京華時報,2015-09-10(16).
[9]舒國瀅.從司法的廣場化到司法的劇場化——一個符號學的視角[J].政法論壇,1999(3):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