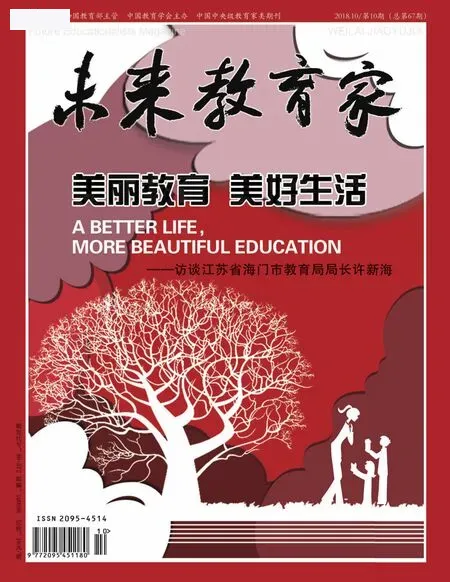教育不是什么
葉存洪/南昌師范學院江西教育評估院院長

葉存洪
“教育是什么”?這是一個宏大而深遠的話題,我很難說清楚道明白。于是試圖逆向地做些思考——“教育不是什么?”根據自己的理解和認識,述之一二。
教育不是奧運會
體育比賽中,所有項目都要決出勝負。現在的教育太像奧運會了,每次考試,要分出前三后四;每項活動,要決出三六九等,試圖以此激發學生的昂揚斗志。殊不知,這樣的做法會帶來問題的另一面,那就是,學生會在同伴中尋找“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勵志”口號——“眼睛一睜,開始競爭”“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就是這一現象的殘酷寫照;“殺了第一名,我就是第一”就是這一做法結出的一枚苦果。要知道,當教育變成“贏者通吃”的時候,教育就嚴重異化了!在這一白熱化的競爭中,整個“教育”過程布滿了速度主義的霧障,充斥了對“贏”的追逐和對“終點”的迷信,學生心態扭曲,“平和”“淡定”愈行愈遠。
學生日復一日地在這種環境中成長,名為同學,實為對手甚至敵手。成績好的學生高冷,瞧不起成績差的同學;成績差的學生自卑,不敢高攀成績好的同學;中等生兩頭不靠,自生自滅。相比較于一些國家實行的“走班制”教學組織形式,我們的學生基本上被固定在一個行政班里,與他們朝夕相處的,不過是一個四五十人的小圈子。而就是這樣一個小圈子,還被人為地“撕裂”,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人們曾用最美的語言形容過的同學情誼今天看來越來越淡了。
我們來看兩則國外的材料,我無意說“月亮都是外國的圓”,但“他山之石”或許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啟發:在日本中小學校,學生各項活動多以團隊為單位進行評價,他們有意回避對個體業績作過多的渲染,甚至都不太愿意提及與競爭相關的字眼,而是更多地鼓勵合作。他們也開運動會,但比賽項目多是集體項目,如拔河、集體舞、團體操、“兩人三腳”、接力等。在芬蘭,對學生學習成果的評估,“從本質上來講,是鼓舞人心的,是支持性的”,評估完全是診斷性的,“目的是找出在不同的學習結果中,以及整個學校體系中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因此,學校和學生能集中精力學習,而沒有被互相比較的壓力”。
教育需要競爭,但競爭不能泛化。今天的社會,早已不是個人英雄主義時代,任何一個大的工程,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兵團式作戰的結果。前些年,人們熱議“硬實力”“軟實力”,其實,比軟硬實力更重要的,是“合作力”。學校各項活動甚至競賽,應更多地采用“達標”的方式,即設置條件和標準,學生只要達到這個標準,就能獲得獎勵。這樣,可以鼓勵學生與“標準”競賽,不斷地挑戰與超越自我,而不是非得在同伴中尋找“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合作力”才有滋生的空間。
教育的重要意義在于不斷推進孩子們的社會化。社會化是具體的,找到同伴并成為日后踏入社會的同盟者或志同道合的朋友,正是教育的本義之一。杜威一句“教育即生長”,道盡了教育蘊涵的美好。你看,在陽光的映射下,在雨露的滋潤中,大樹、灌木、小草錯落有致、各得其所,自然自由自在地生長,這種狀態,想想都是令人愉悅的。我們要教育學生尊
教育不是肆意“創新”的地方
在基礎教育領域,不時出現一些驚世駭俗的言論。對此,華東師范大學鐘啟泉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對教育話語揉捏得汪洋恣肆,已經到了非常令人吃驚的程度。”如果說,社會公眾針對教育說些外行話或許能夠理解,那么,業內人士有違教育規律甚至教育常識的話語和行動,就讓人大跌眼鏡。鐘啟泉教授不客氣地指出,“更為可怕的是,在這其中充斥著我們最優秀的中小學校長、特級教師這些教育人士的身影”。的確,在行內人士的“豪言壯語”里,有不少有違常識的表述,正是這些言論,陷教育于無限的被動和尷尬。比如,“說法”有:“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課堂教學要追求大容量快節奏”“學生是上帝,家長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此條多見于私立學校),等等。“做法”有:一所中學開設三百多門校本課程,說明校長的課程領導力和教師的課程開發力很強;“推門聽課”,說明教學管理常態化、科學化,等等。
限于篇幅,僅就其中的幾點談些個人理解。比如,“為了學生的一切”,出發點非常好,這是教育工作者努力的目標和方向。問題是教育的作用真有那么大嗎?在近代,我國教育界就熱議過教育作用的問題,有“教育萬能論”,也有“教育無能論”。過猶不及,最后大家更多的是認同教育既重個性,包容差異,取長補短,共同提高;教育學生趕超標準,挑戰自我,真誠合作,理性競爭。惟有這樣,才能真正建立起“人人關愛集體,人人被集體所關愛”的和諧、溫馨的集體。置身其中,大家才能心情舒暢,其樂融融,這樣的校園生活,才能讓學生終身留戀、無盡回味。不是無能的,但也決不是萬能的。“為了學生的一切”加上“學生是上帝”一類的口號著實把家長寵得驕嬌二氣,再加上教育工作者總想“種別人的田”,大包大攬,結果稍不周全,還會引起家長的一片指責,被動萬分。再比如,以為“大容量,快節奏”就是有效教學,就是高效課堂。殊不知,教育其實是一種慢的藝術,和農業是一樣的,春天播種,然后經風歷雨,以及夏的酷熱和干旱,才能有秋的收獲,任何圖“多快好省”的做法,最后可能都會導致揠苗助長。
哪怕是開設了數百門校本課程,也千萬不要忘記了基礎教育的“基礎”定位。還有,德智體美勞的“排序”問題,五育是人的全面發展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人為地排出“座次”,容易割裂人的全面、有機發展。再比如“互聯網+”,似乎未來學校和教師都會窮途末路,這種自我革命的意識固然可嘉,但教育常識告訴我們,任何新技術都不能代替課堂教學,教學過程一定是人際互動的智慧碰撞。最后,“劃片招生,就近入學”,這或許是教育公平的靈丹妙藥,但如果教育資源不均衡,這種“胡同決定命運”的做法恰恰是一種致命的不公平。
教育常識是有關教育的最基本且簡單的事實性的知識和道理,和生活中其他常識一樣,照理說是容易做到的。但錢理群一語道出了它的難度:“教育難,難就難在回到常識。”回歸教育原點,是對常識的尊重和敬畏,也是對教育規律的守護和遵從。背離教育的行為和語言,看似高深莫測,若聽憑它們泛濫,最終受損害的是教育的專業性。
教育不是游離于生活之外的東西
在人類社會初期,教育和生產生活融為一體,教育在生產生活中進行,生產生活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教育逐漸從生產生活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出現了專門的教育機構和專職的教師、學生。這本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教育與生活漸行漸遠。表現在受教育對象上,教育是“小眾的教育”,是有錢人、有閑人的教育,是“少爺小姐的專利”;表現在內容上,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表現在教育性質上,教育被看作是“消費品”。
英國教育家斯賓塞在《什么知識最有價值》中對古典主義教育“虛飾大于實用”進行了嚴厲批評,認為這種教育既不能滿足個人的需要,又不能充分發展個性。“從遠古直到現在,社會需要壓倒了個人需要,而主要的社會需要是對個人加以約束……所考慮的不是什么知識最有真正的價值,而是什么能獲得最多的稱贊、榮譽和尊敬,什么最能取得社會地位和影響,怎樣表現得最神氣。”這一切已不適應變化了的社會。他從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思想出發,認為真正的教育應以個人“為完滿的生活作準備”為目的,教育的任務就是教會人們怎樣生活。這就是斯賓塞著名的“生活預備說”。
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杜威,公開聲明他與斯賓塞把教育看做生活的準備的主張完全不同。他認為,教育就是兒童現在生活的過程,而不是生活的準備。因此,要把教育與兒童眼前的生活融合起來,教兒童學會適應眼前的生活環境。在他看來,最好的教育就是“從生活中學習”,學校教育應該利用現有的生活情境作為其主要內容。這就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主張。

到了杜威的中國學生陶行知,將老師的觀點“翻了半個跟斗”,提出“生活即教育”,主張過什么生活就受什么教育。他在《生活教育》一文中寫道:“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營,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因而生活教育是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教育要通過生活才能發生力量而成為真正的教育。
通過以上的梳理,不難發現,不管是斯賓塞的“生活預備說”,還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盡管各自的學理不同,但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反對教育對生活的脫離,都關注教育與生活的聯系。
因為考慮“安全”、追求“應試”、講究“高效”,今天的教育似乎與生活漸行漸遠了,學校教育教學活動與日常生活脫節;課程目標只注重知識的傳遞,忽視學生主體性和創造力的培養;課程內容繁難偏舊,遠離學生的生活世界和社會實際;教學方法“死記硬背”、單一“你講我聽”,學生被有形、無形的圍墻與世隔絕。我們的學科教學從間接知識到間接知識,把所謂“效率”強調到瘋狂的程度,以至于實驗變成了看課件、變成了“黑板上種田”。這種被康德稱作“空對空”的思維、被叔本華稱作“不生產”的思維,最嚴重的后果便是年輕一代思維缺乏悟性、創新能力降低。
通過參觀歐美國家的一些學校,我們發現,幾乎每一所學校都有木工教室、廚藝教室,學生學做手工、學習廚藝,直通生活。近年來,國內也有一些學校積極探索教育生活化。如南昌十九中“校內社會實踐活動”,高中一二年級,學生每學年有一周不“上課”,而是在校內各崗位參與實踐。杭州新世紀外國語學校開展“新六藝”教育(茶藝、園藝、棋藝、書藝、樂藝、手藝),學生在為期一周的學習過程中親身體驗,增強感性知識。社會實踐活動以其實踐性、體驗性彌補課堂教學的不足,為學生搭建了展現自我、發現自我、實現自我的平臺,使學生學習渠道多樣化、學習方式生活化。當然,這些還只是初步的,如何由“一周”走向“日常”,還有很多路要走。不必擔心少上了幾節課會影響“分數”、影響“升學率”,幾節課真的沒有那么重要,很多時候,生活出教育,實踐出真知。
教育不是逐利場
我最近重溫了兩句話,一句是溫家寶同志說的“企業家的身上要流著道德的血液”;另一句是日本企業家松下幸之助說的“公司即是道場”。如今一些成熟的企業越來越趨向于追求超越“利潤”的目標,如萬科“建筑無限生活”,華為“豐富人們的溝通和社會”。如同《第五項修煉》一書的作者彼得·圣吉所說的:“人類的工作觀因物質的豐足而逐漸改變,也就是從‘工具性’工作觀(工作為達到目的之手段),轉變為較‘精神面’的工作觀(尋求工作的‘內在價值’)。”吉姆·柯林斯在《基業長青》一書中認為,如果你想建立一家偉大的公司,一家基業長青的公司,就需要有超越利潤的目的,應將此作為一種恒久的企業生命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是一種對人類狀況和命運的關注態度,它含有某種慈悲和期盼。
我一直在想,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更多地面對的是,無生命的原材料和同樣無生命的產品,只是在終端——銷售、售后服務等環節才與人(消費者)發生聯系,他們都如此重視修行求道,那么,我們全程以人為工作對象的教育工作者,又該作何思考呢?
毋庸諱言,今天一些學校在辦學過程中存在著“反教育”行為。比如,置教育方針和學生身心健康于不顧,為了分數、升學率,將“應試”教育做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只要學不死,就往死里學”;追錢逐利,將學校辦成“學店”,某民辦學校董事長說:“9月1日一車車新生接進來,在我看來,那就是一臺臺運鈔車”;從食堂、校服、保險以及各種名目的教輔資料中拿“明折暗扣”;學校不能“亂收費”,就變著法子讓家長委員會出面收費……雖然只是個別學校、個別校長教師所為,但它對整個教育系統聲譽的“殺傷力”卻不可小視。
教育是培養人的偉大事業,應該保持圣潔的思想,站在道德的高地,扛起人性的大旗,肩負起神圣的職責。教育工作者應該認認真真地思考幾個問題——“辦教育干什么”“辦什么樣的教育”“怎樣辦教育”。當今教育中的很多問題源于沒有真正想明白就稀里糊涂地去做,結果越是努力越是錯得“深遠”,以致于“兢兢業業地誤人子弟”。我很贊成“合掌經營”的提法,合掌是佛教禮節儀軌,雙掌輕合,十指貼連,以傳達恭敬、謙和、推讓、友好之意。再由“手中合”到“心中合”,以心照行,以行顯志,察辦學育人之理,審形勢政策之宜,行仁義中正之道,乃真教育家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意思是,若是舉國上下逐利,國家就危險了。學校擔負著傳承人類文明、培育國家未來合格公民的重要使命,決定著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因此,教育家身上應該流淌著道德的血液,惟有如此,才能源源不斷地輸送給學生,讓道德的血液充盈整個民族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