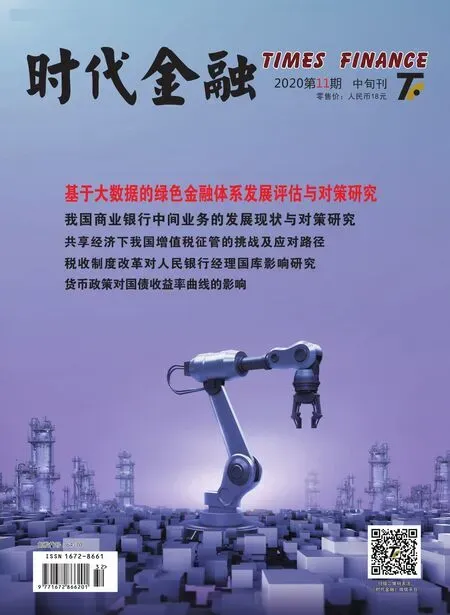湖南省某縣A村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現狀調查
甘江霖王 楠俞群俊
(1.昆明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云南 昆明 650000;2.昆明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云南 昆明 650000)
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城鎮化步伐愈加快速,各類建設用地需求大大增加,以種種理由和方式征用農業用地的情況也愈加突出。在這個進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個無法忽視的群體——失地農民。失地農民是指在農村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城市建設征占農用地(包括耕地、林地、園地、牧草及其他農用地等)所產生的失去土地集體所有權或經營權的原農業人口,既包括由于征占農用地產生的已經農轉非的原農業人口,也包括征占農用地后目前仍是農業戶籍人口的人員。[1]對于失地農民來說,失去的不僅僅是土地,更是不可或缺的生存資料和生活資料,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問題也無法回避。
一、A村的基本情況及失地農民現狀
A村距離縣政府5公里。全村面積4.126平方公里,地勢平坦。有農戶463戶,鄉村人口2036人,其中農業人口2036人。勞動力1921人,從事第一產業人數1786人。全村耕地面積1018畝(此地為6擔=1畝),全村人均耕地面積0.5畝。201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7663.00元(數據來源于A村村委會)。
隨著A村經濟不斷發展,土地逐漸被征用,大批失地農民涌現且呈逐年上升趨勢,成為尷尬的邊緣群體。自2014年11月初次征地到2018年4月截止,共征地約700畝,其中耕地約600畝,耕地占總征地面積的85.71%。失地農民約1400人,土地全部被征用約有900人。
二、調查概況
本次研究選取地點為A村,A村為該縣第一批被征用土地的自然村,老年人口多,農業人口比重大,收入較低且來源單一,具有代表性。
在該村采用隨機偶遇的方式進行調查問卷發放,并通過現場被調查者自填的方式進行調查。針對調查難度較大的老人、文盲、殘疾人、精神病人等特殊人群,筆者采取了詢問助填、看護人以及幫扶工作人員間接幫填的調查方式,以確保統計結果的客觀真實。
本次調查共計發放問卷204份,回收問卷200份,其中有效問卷200份,無效問卷0份,問卷回收率為98.04%,回收問卷有效率為100%。
在200名調查者中,男性被調查者有110人,占樣本總量的55%,女性被調查者有90人,占樣本總量的45%。關于被調查者的年齡分布,主要為低于18歲16人,占樣本總量的8%;19-45歲56人,占樣本總量的28%;46-59歲74人,占樣本總量的37%;60歲及以上54人,占樣本總量的27%。
從被調查者的文化程度來看,文盲48人,占樣本總量的24%;小學文化的48人,占樣本總量的24%;初中文化的66人,占樣本總量的33%;高中及中專的22人,占樣本總量的11%,大專以上16人,占樣本總量的8%。可見,被調查者的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及以下水平,整體素質偏低。
而從被調查者的月平均收入來看,200元/月4人(2%),201-500元 /月 10人(5%),501-1000元 /月 72人(36%),1001-2000元/月66人(33%),2001-3000元/月28人(14%),3000元以上20人(10%)。這也反映出A村村民大多數人收入較低,經濟收入參差不齊的現狀。
三、A村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一)政策宣傳有效方式單一,農民參保積極性低
通過當地政府、村干部宣傳來了解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被調查者共有141人,占樣本比例的70.05%。通過鄰居、親朋好友介紹講解占樣本比例的56.5%,但這種道聽途說的方式,容易錯誤理解養老政策。其中42.5%的被調查者和38.5%的被調查者通過電視、廣播、報紙、網絡得知,但這一渠道主要是發布全國的基本養老信息,對省市縣的養老方案僅供參考意義,并不準確。由此可見具體的養老保險政策的宣傳集中依賴于政府組織宣傳,宣傳方式過于單一。并且據實地采訪了解到,隨著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政策在這十幾年間的不斷推進實施,該縣社保局及其相關單位也根據當地情況制定了多種政策宣傳方案,如印發宣傳單由村委會工作人員進行發放講解、以村為單位定時播報城鄉居保信息、在該縣政府門戶網站及新媒體平臺(智慧人社)不定期發放宣傳訊息等。但是這些宣傳方案仍存在大量弊端,例如,宣傳缺乏針對性(失地農民與普通農民的區別,參保人年齡段的區分以及參保人文化程度對政策的理解力等),宣傳內容浮光掠影,不夠深入。
由于失地農民對養老保險政策的獲知渠道有限,缺乏了解(見圖1),對政策解讀認知能力差,再加上經辦機構工作人員宣傳養老政策時存在疏忽懈怠,造成失地農民參保積極性低或者參保中斷的情況屢見不鮮。

圖1 對某縣失地農民養老保障的政策了解程度
(二)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偏低
在調查過程中,對目前的養老保障水平存在非常不滿意的失地農民占比為49%,不滿意的失地農民占比為34%,只有6%的失地農民是非常滿意,11%的失地農民是基本滿意。在不滿意與非常不滿意的166人中,高居榜首的不滿意原因是保障水平低(認為“保障水平低”的占被調查者總數的75.5%),其次是繳費水平高,占被調查者總數的48%。
另外,政府雖支持自主選擇繳費檔次,鼓勵多繳多得,但是當個人繳費100元時,政府補貼30元,補貼額度是個人繳費的30%,而隨著繳費金額不斷上升時,補貼額度占個人繳費的比值逐漸下降。當個人繳費達到3000元時,政府補貼60元,比值為2%。因此,最低的個人繳費檔次100元似乎成為了“性價比”最好的選擇。懷著這種想法而不考慮未來的養老狀況投保,削弱了“多繳多得”的投保積極性,也降低了未來領取養老金時自身的養老保障水平。這一觀點在調查中得到證實:在被調查的失地農民中,94%的失地農民選擇了100元的繳費檔次。
(三)再就業困難,養老保險續保存隱患
在調查者當中有130人認為再就業是非常困難的,占樣本容量的65%;56人認為不困難,占樣本容量的28%;14人認為不困難,占樣本容量的7%。

表1 被調查者土地征用后所從事職業類型及其學歷狀況
表1顯示,A村農民在土地被征用后,83位被調查者選擇“其他”選項。據調查了解到,選擇“其他”選項的失地農民多是以去本地建筑工地做零工為主,工資收入低、工作量大、工作條件差、生活艱辛、狀況堪憂。另有38人選擇失業在家,在就業崗位飽和的市場經濟下,文化素質低,缺乏特殊技能的失地農民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只能選擇在家待業。
失地農民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較低:46歲以上有128人,占比64%,這個階段其文化程度37.5%是文盲,29.69%是小學文化。此外,在再就業困難原因分析中,35%的被調查者是因為掌握的技能少無法就業,其次是年齡偏大(32%),再次文化程度低(23%)。三者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由于失地農民多以年齡偏大的勞動者為主,他們文化程度低,掌握技能較少,增加了就業難度。還有,很多失地農民只能從事低端、低技術、低職業、高替代率的工作,這就進一步加劇了就業的不穩定與就業再失業事件的頻發。可見沒有政府就業政策的扶持,失地農民很難獨立完成就業,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就更加艱難。不排除A村越來越多的失地農民因為基本生活無法得到保障而選擇放棄參保的可能性。
(四)傳統家庭養老功能弱化
土地收入是農民的主要收入,家庭勞動力衰老無法耕種土地后,將土地交由自己的子女耕種,子女再由耕種所得收入拿出一部分來贍養父母。這實際上是用土地使用權的轉移換取養老的方法。我國農村多數采用的就是這種家庭養老的傳統模式,主要依靠子女贍養以及失地老人自己之前的積蓄,本次問卷調查中未參保的失地農民有29.17%的人是選擇打算依靠子女養老。而在已參保的176名被調查者中,除了16名為單位職工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解決自己的養老問題,另外160名失地農民依舊打算依靠子女養老。可是土地的被征用直接打破了這種養老模式。在對A村失地農民的調查中了解到,失地農民在征地之前雖會繳納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但養老保障水平偏低,無法滿足老人晚年的基本生活需求,所以失地老人基本還是會依靠子女養老。然而越來越多的家庭人口數日漸減少,一方面是因為自實行計劃生育以來,家庭人口數銳減;另一方面是因為年輕一代多數外出工作或讀書,基本在外地生活,很少在家。家中只剩下年齡較大、文化較低、無特殊技能的老一輩,減少了子輩贍養父輩的機會,削弱了家庭養老功能。當前,又面臨著土地被征用,縣城就業機會有限等問題,越來越多的失地青年選擇外出務工,更加削弱了傳統家庭養老的功能,失地老人群體也日漸龐大,養老保障問題日益嚴峻。
四、存在問題的對策建議
(一)拓寬溝通渠道,加強參保宣傳與教育
基層政府部門可有針對性地開展相關工作,充分發揮互聯網+、新媒體等手段及時快速地傳播養老政策。除此之外,社保機構還可完善“智慧人社”客戶端功能,新增政策答疑區,由專門的社保專業人員負責準確解答群眾的問題并接受意見反饋,根據群眾的呼聲,及時調整宣傳工作方向。再者,還可通過精準扶貧這一渠道,在一對一幫扶過程中,幫扶人可合理利用自己的工作優勢加深失地農戶對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的內容及含義的理解,讓當地失地農民感受到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的科學性與親民性,認可該制度實施的必要性,進而提高失地農民的參與程度和參保的積極性。
(二)提高失地農民的養老金待遇,增加政府補貼
繳費檔次選擇過低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在于政府財政補貼的激勵性偏低。因此可針對失地農民這一特殊群體,補充完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增加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條例,結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物價變化等因素,加大政府財政對失地農民基本養老保險的補貼力度,鼓勵失地農民積極選擇更高檔次的養老保險繳費。同時,政府還可以積極引入商業保險參與到失地農民養老保障體系建設中來,主動承擔其兜底責任。以政府名義購買公共服務為基礎,以失地農民所獲取的征地補償款為補充,繳納商業養老保險金,通過商業保險企業及其特殊制度的運行為失地農民在年老時提供額外較高水平的補充養老金,保障失地老人的老年生活。
(三)完善失地農民就業保障機制
A村所屬縣份是“中國湘西黃牛之鄉”“右旋龍腦樟種源地”以及“侗藏紅米種植地”,可以利用這些地域特色,組織失地農民承包土地,養殖黃牛,種植龍腦樟與侗藏紅米,在政策扶持下,形成“市場+公司+基地+農民”的產業化結構,解決失地農民就業難題。具體到A村,可以考慮如何精準地嵌入京東、淘寶、蘇寧易購等電商平臺,拓寬自己的銷售渠道,從而充分帶動再就業。與此同時,政府應在完善失地農民的就業保障機制方面退出更多舉措——在了解市場客觀需求的基礎上,結合失地農民自身條件、個人工作期望,有針對性提供免費再就業教育和勞動技能培訓,為失地農民長久的生活提供一技之長作為保障。
(四)重視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努力構建農村多功能養老服務社區
一方面需要強化家庭養老的功能,雖然家庭養老保障的功能正在逐漸弱化,但是政府要積極發揮其主導作用,通過道德教育、輿論宣傳、法律強制等手段,將其對家庭養老的保障作用發揮到最大值。另一方面,當地政府要加大基礎設施資金投入,因地制宜的建設養老生活配套設施,努力構建農村多功能養老服務社區。A村由五個小組構成,居住地分散,土地的征用致使村民聚居地更加支離破碎。因此需要通過行政手段劃分合理區域給失地農民建房置屋,將各家各戶有效聚集起來,建成被征地農民住宅小區并且建立一定的聯絡機制,便于管理。還可以考慮引入一些專門從事老年事業的協會、養老院或合作醫療專業機構對該地區進行規范化管理,既豐富失地農民的老年生活,滿足其精神需求,減輕他們的孤獨感,又能讓他們的子女更為放心,平衡好工作與生活,減輕其后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