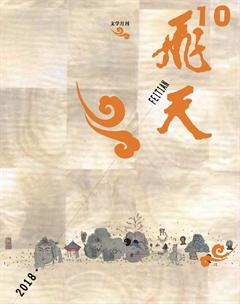涼州“義馬”傳
劉艷
一、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李學輝的新長篇小說《國家坐騎》,2018年4月由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正如小說開篇第一段文字:“光緒十九年的涼州咳嗽了一聲,便把除夕唾到了城門邊上。三三兩兩的人們走出城外,又陸續返城。他們走一陣,停一陣,嘴里喚呼著祖先的名字,邀請他們回家過年。到得家里,他們在清掃干凈灑水焚香的堂屋門前停住,磕磕腳上的塵土,在旁邊的盆里凈了手,倒縮著進屋,在供桌前轉身,燃三炷香,跪下磕頭,掛在墻上的祖先們面無表情,依舊像往常一樣冷峻。”小說開篇,就將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做了限定。故事開啟于光緒十九年(1893年),整個小說故事的時間限定是在1893年到1927年,在清朝沒落而終于走向覆滅、軍閥割據混戰以及史有記載的涼州大地震等這樣一系列的歷史動蕩和自然災害頻仍的歷史時間段,又是發生在涼州。所寫,又是“義馬”的故事,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彌漫小說全篇。
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對馬的喜愛和崇拜由來已久,古涼州又是良駒出產和盛產之地。正所謂涼州自古產好馬,而李學輝在了解武威當地流傳的涼州口述史時,注意到了很多可用的素材。“他注意到在1927年涼州大地震之前,遍布涼州城鄉的馬神廟就有20多處,從事養馬職業的人更是眾多,而這些與近代史的轉折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關聯①”。這是“義馬”形象和故事得以產生的前提和基礎。這樣一個故事,就不可能發生在陰性色彩濃重的“江南”地區,
《國家坐騎》里,敘寫的是近現代歷史轉折時期的涼州。“鐵馬掌銹跡斑斑”,馬戶、馬神廟、圉人、相馬師,等等,投射出的都是涼州自古以來的風俗物事,硬朗、凜冽,有著大西北的粗獷和閉塞及春風不度。可以從自然環境、獨有的地理地域特色、獨特的物事人情等方面來看這個長篇所展示的濃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小說故事開始在光緒十九年除夕,小說第四節“正月初六的涼州城胖了起來”。正月初六是馬日。在馬政司、廟祝主持下,八旗騎兵和馬戶們共同完成了馬日的活動,游馬、祭馬,所有的祭拜活動結束后,馬政司的官員們和所有人想的是,韓驤妻子是否可以誕下“神駒”(7-11頁)……“馬戶們不嫉妒,也不敢羨慕。這是場賭局。若生得龍駒,韓驤就會游手閑蕩,和龍駒一樣,成了供養人;若生下的孩子不能稱為龍駒,韓驤則會像牛一樣,供馬戶們役使,不得反抗”(13頁)。為韓驤妻子把脈的相馬師懷揣的是《馬經》,把脈時他依據的是賈思勰《齊民要術》里的相馬篇,并且高聲誦讀(15-16頁)。涼州有馬場,而且與祁連山相依“涼州的牧場稱馬場。傍祁連山的叫大馬場,離涼州城近的叫小馬場。小馬駒們在小馬場出生,斷奶后,便放逐到大馬場”(18頁)。半人半馬的“義馬”的養成,需要涼州這里自古以來養馬的歷史、現實和規制,就連從一個由相馬師先把脈和出生后敲骨測定是“神駒”(實為人嬰)降臨人世,到真的“義馬”“國家的馬”的養成,也離不開涼州這里特殊的地域和自然環境。涼州的風、雨、雪、飛禽、走獸,鷹、兔,訓練義馬下水的“天馬湖”,訓練義馬而義馬最后竟然咬死了狼的地方——祁連山。
《國家坐騎》所書寫的是涼州“義馬”傳,除了涼州這里的自然、地理、傳統和歷史文化習俗等方面的地域文化特征,小說家還將筆觸伸展到與馬有關的歷史典籍及其古今傳承那里,《齊民要術》是相馬師的珍藏和依憑、《三國演義》《相馬經》是圉人說故事和所信奉的依據(116頁)。很多評論家強調《國家坐騎》的先鋒性敘事技巧,但是,今天的歷史文化語境和創作語境,已經不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那一段先鋒派文學的環境,不可能再追求一種敘事的游戲而獲取文學的巨大成功和榮光。小說敘事,哪怕是虛構的故事、先鋒性的敘事,也要符合小說內部的敘事邏輯。涼州“義馬傳”的故事,換一個地方,這個故事就不可能發生,發生了,就會讓人覺得是純粹的虛構和生捏硬造。南桔北枳還是好的,水土不服而斷了藝術的生命也是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說,即便是先鋒敘事的虛構形象以及技巧,那么,“義馬”也是涼州的,而不是其他地方的。
我在讀這個小說的時候,一直在思考的是,真的有“義馬”這樣的歷史故事和原型嗎?在經跟作者李學輝交流和確認后,涼州的確有“義馬”的舊制,也有義馬廟存在,而最后的義馬是消亡在民國時期——李學輝的《國家坐騎》從這個意義上說,是為涼州最后一個“義馬”做傳。讀這個小說,給很多讀者和評論者,尤其是我們女性研究者帶來的感覺是,讀得我們心里感覺都不好了——各種糾結和沉重,一個作家須懷了多大的勇毅和信念,才能完成這樣一個小說,為我們留下一段寶貴的歷史與文學資料?由小說來看,在一種曾經被馬戶、圉人和相馬師所信誓旦旦畢生追求的國家精神里,“國家之馬”、龍駒的養成,又凝聚了多少讓人心情沉重乃至內心撕裂的因素?負載國家精神重啟期冀的“義馬”是否可堪重任?
二、負載國家精神重啟期冀的“義馬”是否可堪重任?
大家已經基本認識到,韓義馬這個形象,是當代文學形象譜系里一個全新的文學形象。“在當代文學的人物譜系上,這是一個全新的文學形象。小說中一出生就順利被相馬師檢測認定是‘龍駒并改名為韓義馬的角色,有著傳奇的色彩:為了符合‘義馬的標準并成功成為‘國家之馬,韓義馬經受了一系列的訓練,他以半人半馬的方式生活,并在精神上也完成了人馬合一”。②按照相馬師、圉人、馬戶和馬政司等的希望,他最終要“精神上”也完成“人馬合一”,這是他自己情愿的嗎?而且,在當時是否能夠負載國家精神重啟期冀的重任?
其時,義馬所負載的國家精神和民族精神重啟的期冀,只是小說所要表達的一翼,是善良和有責任擔當精神的小說家李學輝一種精神維度的希望和寄托。但是,他對此,也并非是一種迷信和篤信無疑的。小說在義馬被規訓和養成的過程中,不止有韓驤夫妻尤其是韓驤妻子的掣肘,而且,當時的歷史是什么樣子的呢?清朝覆滅、軍閥割據、涼州大地震等,本身就對義馬的馴養和成為“國家之馬”構成一種挑戰和諷刺:韓驤的妻子:“國家,國家,什么國家?相馬爺死了,只有圉人對他好,誰見過國家的一粒米,一分錢?過個馬日,縣衙還要征捐呢!”(133頁)城里的孩子會不守規紀把痰吐到義馬頭上“朝義馬啐了一口”——城里的民眾也在懷疑義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啐了義馬的孩子的父親“看了,不就一張告示嗎?當今的皇上還在吃奶,一張縣衙的告示頂啥用”(137頁)!從小皇帝開始,圉人的馴育義馬的過程,連他自己也時刻感受到時局對馴育義馬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質疑和挑釁,哪怕袁世凱登基,圉人也只能借酒澆愁,圉人把酒杯扔了:“罷了,罷了!國家的事現在有袁少保操心,我只管訓練好義馬!誰坐天下,馬就是誰的,但終究是國家的!”(149頁)——這更像是一種聊以自慰和自我寬解。
負載當時國家精神重啟期冀的“義馬”是否可堪重任?對此,小說也并不抱有十分的決斷和信心。小說本身就展開了一個對話甚至對壘的平臺。第一,持此信誓旦旦者,主要是圉人、相馬師和馬戶以及馬政司的人,但即便是馬戶也并不總是對此念堅定。除了普通民眾的懷疑和軍閥的或敵意想殺滅義馬或想據為己有,最大的質疑力量,應該是韓義馬的父母韓驤和妻子。他們尤其韓驤妻子畢生所做,都是想索回自己的兒子的一個過程。第二,當時的時局和當政者,本身對“義馬”養成和追求“國家的馬”之精神這個過程也是一個反諷和疑問。小說提供了這樣一種繁富的思考。圉人的執著和歷盡千難萬險追求義馬的鑄造成功并且令其最終被焚化和所謂去“轉世”,與環境時時發出的質疑和挑戰,形成一種反差乃至反諷,而晚清到現代的那段歷史的變動和喧嘩乃至滑稽,是最大的諷刺和事實上的質疑力量。眾人都怪怨圉人和義馬是“亂折騰”,縣長卻說:“你們不懂,他們身上體現的確實是一種精神。國家已成這么個樣子了,再沒點精神和血性,憑蔣委員長從天空中飛來飛去督戰和搶地盤,是解決不了問題的。”(282頁)當時的歷史本身就是對馴養這種半人半馬形制的義馬的質疑,即便當時小說中的人物仍然對此義馬可堪負載國家精神的想法信誓旦旦,但立在現在的時間節點回望,還是會讓人產生疑問,不可避免會覺得那段荒唐的歷史,是對仍然有人追求通過義馬來承擔國家精神的一種反諷。追求的人,尤其義馬自身,是充滿悲劇性的。當然,可能恰恰是這種悲劇性,也是有意義和價值的。如果我們不考慮“義馬”具象的意義——其對人的身體的刑錮和殘酷性,如果考慮“義馬”的象征意義,的確可以警示我們,任何時候,人都該有精神和血性,應該有著國家精神的自覺擔當和追求,即便愚公移山也是足可敬畏的一種追求和行為。
三、國民性反思的凝重主題
評論者認為小說就是“鉤沉出了近代歷史中發生于涼州城的一段燭照家國精神的故事”③。也有人是被《國家坐騎》的書名和一些已經在流傳的評論影響,持“讓一個負載著盛世文化符碼的人馬在亂世中復活”、可以“讓艱難生存中行尸走肉茍活的人們看到中國人文精神的一縷魂魄”④的觀念。這里要說的是,除非視義馬為純粹的文學想象、與現實完全無干的文學形象,否則,從義馬的養成并最終獻祭,其中更加投射出的,是國民性反思的凝重主題。
《國家坐騎》所作國民性反思的凝重程度,堪比蕭紅的《呼蘭河傳》,而且在有的方面,比蕭紅的《呼蘭河傳》更加讓人糾結和難以釋懷。對比蕭紅的《呼蘭河傳》,我覺得這個小說的主旨,更應該是“涼州‘義馬傳”。相對于《呼蘭河傳》中國民性反思最深徹也最為精彩的華章——第五章小團圓媳婦被虐待致死一章,《國家坐騎》里其實也暗寓這樣一個國民性反思的凝重主題。作家、評論家在為“義馬”象征和代表國家精神重啟和是對國家精神的一種追求而感到喜悅乃至興奮的時候,似乎也應該思考的是義馬這個半人半馬形象身上所承載的悲劇色彩——其中對韓義馬這個人的身體和生理的殘害和虐殺。其中,最應該被注意和探討的是國民性反思的主題。義馬出生即遭虐,圉人令木匠打張只能立著睡的嬰兒床——圉床,三個月不許除掉夾他頭的夾板,后來的閹割和以火燒死完成祭禮……全是在眾人尤其圉人的力促下完成。義馬小時候經歷的一次馬舞之后,馬街擺出了流水席,“‘做馬好,還是做人好?吃義馬糧的人,是國家的。他們羨慕著,可著肚子吃著”(34頁)。世道艱難,也令馬戶們的思想混沌若此。“韓義馬像一只肉丸子,翻騰在巴子營的湯中”(35頁)。這句話,簡直就是韓義馬與眾人關系的一個隱喻,暗寓他被吞噬的命運。而韓義馬的淬煉和被認為將轉世為所謂的“國家之馬”,不是他自己情愿的,也不是他的家人尤其母親情愿的。而圉人、相馬師、馬戶們,卻眾手推動促成了這個事情。尤其是圉人,簡直是窮盡畢生精力,要把義馬這個形塑的過程完成。沒有他掌握著國家機器賦予的權力和盤踞在他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那些尋經據典,沒有他以義馬是“國家的馬”來賦予自己行為的偽“正義性”,韓義馬的刑塑和獻祭是不可能完成的,更況韓義馬的母親隨時都有可能把兒子搶奪回去……
圉人在刑虐韓義馬的過程中,比《呼蘭河傳》中小團圓媳婦婆婆還要讓人恐懼和覺得可怕。小團圓媳婦婆婆,更多是愚昧和自身利益相關的利己思想以及傳統積習在作祟,她并不擁有國家賦予她的特殊權力來虐待小團圓媳婦,面對云游真人“婆婆虐待媳婦”的指控,她也是嚇得趕快跪下了、眼淚一對一雙地往下落,一番哀告;圉人,則是既有著傳統的歷史文化和養義馬祖制的憑依,又有了國家層面所曾經賦予他的權力,才完成了對義馬施虐和刑塑的過程……如果小說對塑造和養育、刑塑般形塑出韓“義馬”的行為,一味地批判,未必能有如此沉重和震撼人心的效果。恰恰這當中,又有著相馬師、圉人、馬戶們習得的傳統心理和傳統的忠君報國思想在主導著他們,光緒后溥儀小皇帝登基乃至后來的大清朝完了、袁世凱竊政,等等,本身已經對他們的忠君報國思想構成了一種反諷。他們仍然矢志不渝地追尋——一定要將韓義馬養成和獻祭,來完成他們自身的“使命”,盡管這份使命感已并不可靠和牢靠,甚至他們自己都感到了一種荒謬和不切實際而生的莫名的惘惘的威脅,等等。
而小說中,圉人時時注意到和腦海常常浮現出的韓驤妻子的豐胸和大乳房,也是呈現荒謬和諷刺的意味。一個這樣的人,他所追尋的血性和國家精神,真的能夠負載當時國家精神重啟的期冀嗎?韓義馬之被生理畸形化和最終被奪去生命,是有著深在的悲劇性的,這也是很多如我的讀者和評論者讀這個小說,常常心情過于沉重、心里感覺都不好了的一個重要原因。韓義馬自己并不想為義馬,他的母親也不希望她唯一的孩子被養成半人半馬的形狀——這些全都讓人心碎,卻又覺深深的無力感,我們都沒有力量跳到小說里去救拔韓義馬出非人之境,悲劇性也由此烙印在我們每個讀小說的人的心里。
國家精神的重啟,對當時、對任何時代、對于當下,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是應該再度從類似義馬的這種半人半馬的畸形人的馴育當中產生?小說本身,可能也是一個巨大的隱喻,啟發我們進行更多和更深層面的思考。深層而言,我更愿意把“義馬”歷經淬煉而完成“人馬精神的合一”的過程,和小說對此所作的文學書寫,看成是作家一種先鋒性小說敘事和形象塑造的技巧。作家在當下依然進行一種先鋒性敘事探索,同時又包蘊了新歷史主義小說的色彩和味道。所以,我們可能不能過于把“義馬”形象和將“人馬精神的合一”真實化、在地化或者說具象化對待,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國家精神重啟必然性,我們可以視之為國家精神需要的迫切性和追尋道路上所曾經歷的磨折和困難,可以視之為“義馬”的故事曲折反映了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和地域的故事,可以看成作家李學輝怎樣用文學的書寫,來為涼州最后一個“義馬”做傳,寫出義馬本人、義馬家人的悲劇性命運以及那個時代民眾民生的歌哭,而不是其他。
四、旁逸斜出的人性書寫的
文學力量
有關韓驤夫妻對兒子韓義馬的感情和不舍,本是小說的旁枝,我卻覺得,這旁枝里,偏偏蘊蓄了小說最為感人的那些東西。舐犢情深,人性的溫暖與微光,才應是這個小說最為打動和感染我們的一個方面。
孩子出生,圉人讓韓驤把圉床搬進屋中,把孩子塞了進去。韓驤的妻子要在圉床上鋪點衣物,被圉人阻擋。“她把眼淚夾在眼眶,用手搓摩圉床,從里搓到外”,“夾板夾在孩子臉上時,她撕扯自己的頭發(27-28頁)”,天冷了,韓驤的妻子量量圉床,拆了一條被子,趕制了一條似被非褥的條形東西。她讓韓驤抱起義馬,把它鋪搭在圉床上,把義馬放進去,義馬扭了扭身子,朝她笑笑。圉人弄來小猴,就是為不讓義馬睡覺——馬不能睡覺,“韓驤點了燈,燈下,妻子的淚珠比豆還大”(52頁)。義馬被閹割,義馬的娘三更半夜去敲圉人的門,想知道兒子怎么樣了。役工送來吃的,她:“我沒心思吃,見不到義馬,我啥也吃不下去。”(62頁)
圉人讓韓驤夫婦給義馬腿上綁沙袋練腿法、走法,韓驤妻子偷偷把沙袋弄上小洞,沙袋就慢慢癟了下去,母親心疼兒子(68-69頁)。廟祝拎起燒紅的銅印,要在義馬身上烙印,韓驤的妻子就撲上去搶銅印。韓驤抱住妻子,把她拉到門外。義馬慘叫一聲,韓驤的妻子扳著門框哭罵了起來:你們這些天殺的(120頁)!圉人讓義馬遭遇了狼,雖然義馬咬死了狼,義馬的母親沖過來,揍擊圉人。揍聲嘭嘭。那人(注:義馬母親)一口咬住了圉人的胳膊。胡七爺掄起了鞭子,圉人沉聲道:不可。女人噗地把口中的東西吐到地上,是一塊肉。圉人胳膊上的血涌出,在雪中分外艷紅(157-158頁)……最后,在殺人如麻的韓廷勷要騎義馬,被韓驤夫妻阻,韓廷勷先舉刀砍了韓驤的頭,韓驤的妻子也迎著刀沖了過去,一直恨圉人的母親臨終能說出一句“義馬,就交給你了”!將義馬交給自己曾經最恨的人——多大的悲痛和無奈蘊藉其中(166-167頁)。
假設,沒有韓驤夫妻尤其韓驤妻子對馴養義馬行為的種種掣肘,這個小說是否還可以達到如此深刻和厚重的直蹈人心的苦與痛?當時的國家所形成的馬戶另冊和扁頭人的存在,本來可以泯滅掉韓義馬父母最后一點正常的人性,他們可以麻木地順從、服從甚至樂于奉獻出自己的兒子。實際情況卻是,除了韓驤有實際的、現實生活的考慮,屬相對情愿兒子做義馬的情況,韓義馬的母親,這個無名的母親,自始至終也沒有接受兒子做義馬的現實。她心里裝滿的:他還是個孩子!他是人,不是馬!她和丈夫沒能再有孩子,唯一的兒子牽系她這個母親所有的心力和她的一生,未待義馬最后完成祭禮,他已經為保護義馬失去了生命。即便如此,臨終前,她還不忘把義馬托付給她最不愿托付乃至一直仇恨的對象——圉人。這其中的傷懷與心痛,非得做過母親和身為母親的人,才能體會到吧!有評論家說,義馬和義馬遭閹割、被獻祭,是那個時代很正常的事情。問題是,即使是被一定的歷史文化語境造就的一種特殊歷史與文化遺留,一種特殊的規制,它就是合理的嗎?文學是人學,小說最大的價值,難道不是表達了即便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即便是在早就如此、本該如此的現實的厚障壁面前,小說家依然通過人性的體察和揣摩,在厚障壁上鑿開了一個小洞,透出些許人性溫暖的微光。有了這微光,我們愈加為當時的涼州和涼州生民而感同身受而體會和哀民生之多艱?無論哪個時代,都應該呼喚國家精神和自覺追求乃至踐行國家精神的擔當,但不應該通過扭曲和虐殺人的身體和生命來達成,人類文明和人類社會尚能進步,動力大抵在這些方面吧。
劉醒龍在《國家坐騎》封底,對這個小說的薦語,恰恰突出了涼州對于這個小說的價值和意義:“但凡提及‘涼州二字的文字,命定是要驚世駭俗的,不如此就無法般配。說起來這只是假定,但對生于涼州、長在涼州、半輩子用文字寫涼州的李學輝,無疑是睜開眼睛就要面對的真實,這都怪那些比星月還耀眼的唐詩宋詞。當然,也得益于這遠上黃河的春風不度,才給李學輝從動筆之初就定下極高的門檻。從最早寫唯有涼州大地上才出現的那位緊皮手,到此次能馳騁在涼州大地上的義馬,李學輝用小說很好地傳承了王維、高適和岑參等人的古典浪漫精神,給文學長河的涼州畫卷,留下了品相純粹的一部。”——涼州“義馬”傳,或者說,涼州最后的一個義馬的傳記,的確要飛升起足夠的文學想象力,作家才能讓義馬這個文學形象脫離歷史的記載和口述的口口相傳,在文學文本上完備和豐贍起來,這或許就是劉醒龍稱贊的李學輝所具有的古典浪漫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與其說是“國家坐騎”,不如說是“涼州‘義馬傳”,記錄個人、民眾與一個時代的歌哭的義馬傳。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世紀海外華文作家的中國敘事研究”(17BZW171)的階段性成果]
①鄭周明:《<國家坐騎>:在歷史風沙里聽見蕭蕭馬鳴》,《文學報》2018年5月26日。
②鄭周明:《<國家坐騎>:在歷史風沙里聽見蕭蕭馬鳴》,《文學報》2018年5月26日。
③鄭周明:《<國家坐騎>:在歷史風沙里聽見蕭蕭馬鳴》,《文學報》2018年5月26日。
④鄭周明:《<國家坐騎>:在歷史風沙里聽見蕭蕭馬鳴》,《文學報》2018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