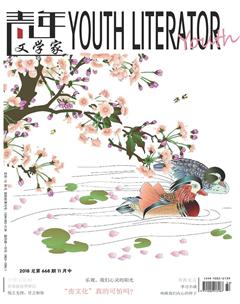識解理論關照下的接受美學翻譯
程相丹 劉著妍
摘 要:在翻譯的識解過程中,譯者對原文的理解表達是否能被讀者所接受是至關重要的。接受美學翻譯觀認為譯文應順從譯文讀者的反應效果,譯作的好壞應以讀者在何種程度上正確理解和接受譯文為標準。意義來源于不同時代的讀者對文學作品動態的闡釋,文本的意義只有通過讀者的閱讀才能被實現。本文擬基于認知語法理論下,論述以識解維度為參照的期待視野是如何作用的,以及在識解維度重構中如何實現接受美學翻譯中的文本意義。
關鍵詞:識解;接受美學;文本意義;翻譯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32--01
一、識解重構中文本意義的實現
譚業升曾指出翻譯是意義在新的語境中通過不同識解方式重新被建構的過程。也就是說,翻譯的過程是譯者先識解原文及作者所表達出的意義,并在譯文中重新建構識解方式,將大腦中的“意義”還原成作者所描述的客觀事實,再結合譯文讀者的認知語境,使譯文被讀者所接受,而得以實現其意義的過程。認知語言學家認為任何一部作品當中的“意義”都應當是動態的開放的,需要讀者參與的,而如何識解文本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譯者。意義的實現成功與否,主要取決于譯者是否采用了恰當的識解方式,以符合譯文讀者的期待。這一觀點實際上正與接受美學中關于文本意義的理論大體上一致。接受理論認為文本具有開放性,即文本“空白”和“未定性”,而任何文本的意義實現都離不開讀者的閱讀,但它也是多方合作的結果。文本意義的來源是原作者和原文,傳遞中介是譯者和譯文,接受者是譯文讀者。從重構識解方式的角度探討接受美學中文本意義的實現,就需要將認知觀和接受美學觀相結合。這一部分將從中介和接受者兩方面結合識解重構進行論述。
二、視角重構時的譯者主體作用
描述同一事物時,由于認知主體選擇的視角有差異,認知過程不同,對事物描述的意義描述也是千差萬別。翻譯時更是如此。翻譯中譯者作為認知主體會進行兩次視角轉換重構來實現其作為傳遞中介的決定性作用。翻譯活動的開始,譯者是作為一位原文讀者對原文進行閱讀和理解。在特定的背景下,利用其自身的“期待視野”與原文及作者進行交流,以達到“視野融合”。作為讀者的譯者的這種主觀能動地發揮與識解與普通讀者是不同的,因為譯者此時不僅要讀懂作者描述的客觀事實和表達出的主觀情感,還要理解吸收原文本中豐富的思想內容、寫作藝術特點和技巧等等。為下一步的翻譯創作做準備,努力使翻譯所需的原文本與作家創作的原文本達到最大程度的相似。
譯者識解原文意義完成后,作為創作主體開始創造性的翻譯原文本重新建構視角,即主動考慮預設第二次接受活動中譯文讀者與譯文的交流對話和視野融合。翻譯的最終目的是給譯文讀者閱讀,雖然譯文讀者與譯文的交流只在翻譯活動完成后才能真正實現,但譯者在進行翻譯創作時必須要發揮其作為文本意義傳遞中介的主體作用,以使譯文讀者能享受到原文讀者在閱讀原文本時的效果。
在接受美學觀下,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發揮主體作用進行視角識解再重構對于譯文文本意義的實現至關重要。
三、詳略度重構中的文本召喚結構
詳略度就是人們“對一個場景觀察或是描寫的精確程度”,也就是說人們可以使用高層次范疇的概念,以概括性的方式來識解外部世界,也可以采取低層次范疇的概念來認知外部世界(金勝昔 2015)。翻譯中,譯者根據表達效果的需要,結合原文作者的實際表達與譯文讀者的認知特點,通過詳略識解方式的轉換,選擇對一場景進行更詳細地描述,或是省略影響順暢閱讀的信息,重新建構出存在多層面“召喚性結構”而又符合譯文讀者期待的譯文。
以接受者為中心的動態對等翻譯活動,為讀者正確理解原作的精神提供了較大的文化闡釋空間,即接受美學所主張的“召喚性”結構。接受美學認為,文本具有未定性,并不是能夠產生獨立意義的存在,而是一個多層面未完成的“召喚性”結構,留有供讀者填充的“解讀空間”。
這些譯文中的“召喚結構”往往需要讀者根據自己的“期待視野”在閱讀中認識把握其內涵并填補譯文的“空白”,使之具體化,最終實現文本的意義。譯文文本意義的來源是原文和作者,傳遞中介是譯文和讀者,要想文本意義被接受,譯者就要在語言翻譯準確的同時,充分重視詳略識解重構的重要性,為讀者“留白”,以便讀者充分理解原作的精神。
四、結語
接受美學是具有現代意義的一種理論,它完成了由“文本中心”到“讀者中心”的轉換。接受美學對讀者的重視與研究在識解理論的關照下給翻譯研究帶來許多啟示。
在接受美學翻譯過程中,讀者的審美期待與文本意義的實現是一脈相承的關系,文本本身是作者的創造物,但這一創造物在進入閱讀前是留有意義空白的,只有通過認知識解主體讀者的閱讀才能彌補空白實現文本的意義。讀者以自己的“期待視野”對作品做出選擇,隨著水平的提高,讀者原有的定向期待被打破或拓展,從而形成創新期待,并對文學作品的翻譯及譯者提出新的要求。譯者主體會盡力將原文和譯文調整至與讀者期待視野相符合的審美距離,從而形成一個循環上升實現譯本意義的過程。而這一過程中,無論譯者或讀者都離不開識解方式,因為翻譯轉換的認知實質是識解轉換或重構。
識解理論參照下的接受美學翻譯研究就是從不同識解維度出發,辯證看待文本、譯者和讀者三者的相互關系,為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開辟了新視角。
參考文獻:
[1]陳玲玲.論接受美學中的“期待視野”[J].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1(02):63-65.
[2]金勝昔,林正軍.識解理論關照下的等效翻譯[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02):11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