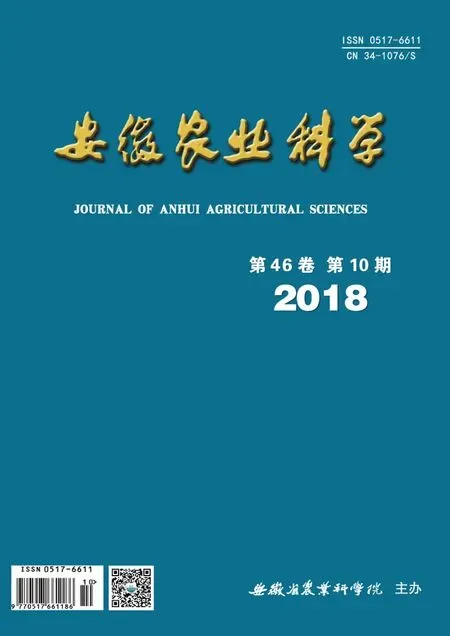中甸牦牛產業現狀及發展思路
陳學禮,和嘉華,鄒淑昆,都 吉,和云鳳,和麗英
(1.迪慶藏族自治州高原生物研究所,云南香格里拉 674499;2.香格里拉市建塘鎮畜牧獸醫站,云南香格里拉 674499)
牦牛是以我國青藏高原為起源地的特有畜種,也是“世界屋脊”著名的景觀牛種,是我國西部特別是藏區人民飼養的能適應高寒、缺氧環境的一種多功能動物,是我國高寒民族地區的主要畜種和重要的生產資料[1]。牦牛具有肉用、役用、奶用等多種價值,其肉、奶等是具有半野生風味的天然食品,藏族人民的衣、食、住、行都與牦牛息息相關。牦牛養殖業是高度適應高寒生態條件的特定生態養殖模式[2]。牦牛作為一種自然資源、生態資源和經濟資源在西部大開發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甸牦牛是迪慶州高原地區特有的畜種,是我國優良牦牛類型之一,主產于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原為中甸縣),以該市的大中甸、小中甸、尼汝、格咱、東旺等地為最多,此外在德欽縣和維西縣等也有分布。迪慶州現有牦牛(包括犏牛)約12萬頭,生活于海拔3 000~4 300 m的高原和高山垂直帶,耐粗飼,覓食力強。
1 中甸牦牛飼養現狀
1.1傳統養殖占主導地位迪慶藏族牧民由封建奴隸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文化沉淀不足,思維相對封閉,加之地域限制,對新技術的接受較慢,科技素質偏低,利用天然牧場全年放牧,靠天養畜情況明顯。而中甸牦牛生長所處的生境,氣候惡劣,植物生長季節很短,枯草期長,牧草單產低,質量不高,飼草匱乏。牦牛營養需要的均衡性和牧草生長供應的季節性矛盾十分突出,中甸牦牛基本處于半饑餓狀態,生產存在“夏起秋肥冬瘦春死”的惡性自然循環,生產周期長,生態成本高,耗費勞力多,牦牛業處于粗放經營的生產模式[3]。
1.2生產性能低中甸牦牛屬于原始品種,個體偏小、成熟晚、生產力低,雖乳、肉、毛、皮、役多種生產性能兼用,但都不突出。長期自繁自養,近親繁殖,造成品種退化,表現出體格變小、體重下降等情況,母牦牛發情率低,空懷率高,普遍存在2年產1胎情況,繁殖性能偏低。
1.3牧場載畜力下降中甸牦牛生活的牧場海拔高,氣溫低,一般5月下旬開始青草發綠,10月中旬枯黃,牦牛覓食青草時間短。由于不注重草場保護,導致牧場過度過牧,沙化、退化嚴重,狼毒等有害植物滋生,牧場利用率不高,導致載畜力下降。
1.3新技術推廣遲緩迪慶州地處以藏族為主的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地廣人稀,山高路遠,人才匱乏,經濟基礎薄弱,財政困難,牦牛產業投入經費不足。由于經濟、交通的限制,部分地方群眾還存在語言溝通障礙,與內地交流機會少,使文化、信息、技術的傳播擴散困難,實用技術和高新技術推廣較慢。
1.4缺乏有效疫病防控體系中甸牦牛放牧于交通困難的高山地帶天然牧場,獸醫防疫工作開展困難,迪慶藏族自治州獸醫防疫部門目前還處于春秋兩季預防及疫病發生時的緊急預防形式,對疫病防治工作不到位,一旦發生如口蹄疫之類疫情,只能撲殺做無害化處理,極大地制約了牦牛產業發展。
1.5牦牛系列產品加工精細度不深當地牦牛養殖戶一般將牦牛直接出售,基本處于出賣初級產品階段。雖然近幾年來出現幾家牦牛產品開發企業,但從事牦牛產業精深加工的企業、特別是龍頭企業較少,缺乏牦牛系列產品深加工體系,加工企業普遍存在產品結構單一、加工程度不高、精產品少、小規模等特點,產業效益較低。
1.6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盡管國家對迪慶州加強了基礎設施建設,但遠不能滿足抵抗高海拔地區各種自然災害需要,基本沒有標準牦牛養殖圈舍,抗御風霜雨雪雹等自然災害能力差。良種繁育體系、飼草生產體系、技術服務體系不健全、不完善,草畜生產機械化缺乏,科技推廣力量薄弱,草原建設和草原監理力度小等諸多問題,使迪慶藏族自治州特色牦牛業未能形成優勢產業走向外地市場。
2 中甸牦牛產業發展對策
2.1建立中甸牦牛的提純復壯與繁育體系開展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牦牛資源調查,摸清各地牦牛資源狀況,通過對迪慶境內各地牦牛群體進行個體評定,篩選優良牦牛組建中甸牦牛基礎母牛核心群;在全州范圍內選擇優秀牦牛種公牛、引進省外優良種公牛或者凍精與之選種選配,對其后代進行選育,選擇優秀種公牛逐步向全州推廣。
2.2建立中甸牦牛雜交利用新模式在對現有黃牛與中甸牦牛雜交利用的基礎上,引進奶肉兼用西門塔爾牛、安格斯牛、短角牛、荷斯坦奶牛等牛種資源與中甸牦牛雜交,并通過對所生產犏牛的生長發育、產奶產肉性能和品質評價,篩選出較為理想的中甸牦牛新的雜交利用模式[4]。
2.3利用同期發情技術開展人工授精傳統養殖條件下的自然交配,公牛需要量大,增加養殖成本和生態成本,引進種公牛價格昂貴,而且有不適應當地環境而死亡的可能,特別引進低海拔地區種牛不能適應高海拔環境。因此無論進行牦牛本品種改良或其他牛雜交,引進凍精進行人工授精是最佳途徑。牦牛發情主要集中在7、8、9這3個月,發情癥狀不明顯,野性大,人不易接近,一般的人工授精極易造成漏配,因而應用同期發情技術開展程序化人工授精具有很好的可行性。程序化人工授精技術的應用可使配種牦牛群體集中發情、集中排卵、集中妊娠、集中分娩,極大地節約養殖和授精技術人員的時間和勞力,也方便母牛妊娠、分娩及產后統一管理,同時應用該技術還可增加受胎率[5]。據對西藏牦牛程序化人工授精技術應用統計,同期發情率平均能達到94.82%,比自然發情率(35%)高近60百分點,受胎率平均為63.34%,比自然發情的受胎率(28.60%)高34.74百分點[6]。筆者2016年在香格里拉市天成倫珠公司牧場使用西門達爾牛凍精對中甸牦牛進行了小規模程序化人工授精實驗,配種27頭中甸牦牛,受胎16頭,受胎率59.26%,而且使其中大部分當年產犢很可能不會受胎的受配牛受胎[7]。
2.4中甸牦牛現代養殖技術的集成應用推廣開展人工草場建設,強化天然草場改良,做好飼草種植與調制,補飼飼料產品開發與推廣,犢牛代乳料研發與應用,犢牛、后備牛、母牛和育肥牛科學飼養,早晚精料補飼與白天放牧相結合,冬春暖棚養畜[8],加強疾病防控技術應用,初步建立科學的中甸牦牛現代養殖集成技術,并通過示范、培訓進行推廣[9]。
2.5進行牦牛肉新產品研發及生產牦牛奶肉不僅營養價值高,而且是綠色食品,符合世界食品新潮流。加強政策、資金、科技投入力量,出臺傾斜政策,扶持龍頭企業,創造有力名牌,依托迪慶州牦牛產品加工企業制定工藝技術規程及產品質量標準,實施生產線升級改造,實現企業自主知識產權技術的產業化,研發完善牦牛奶、牦牛肉、保健品等加工產品規模化生產工藝技術,提高企業產品附加值,以工帶養,延長產業鏈,帶動藏區牧民以養致富,推動藏區牦牛產業的健康發展和縣域經濟發展。
2.6創建中甸牦牛科研科技創新團隊為提升中甸牦牛生產性能,科技與畜牧部門要加強協調,積極組織專業科研人員,創建迪慶牦牛科技創新團隊,開展牦牛資源概況調查、牦牛繁育體系建立、飼草基地與牧場建設、精料研發及補飼管理等深入研究,強化提升牦牛生產性能,為壯大迪慶牦牛產業打下良好基礎。
3 中甸牦牛產業前景
牦牛是我國高寒民族地區的主要畜種和重要的生產資料,是青藏高原不可替代的生物物種。牦牛養殖業是高度適應高寒生態條件的特定生態養殖模式,是地區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更是廣大牧民世代經營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產業,發展牦牛業對提高藏區人民的生活水平,繁榮藏區經濟具有重要作用,正如十世班禪所言,沒有牦牛就沒有藏族人民。中甸牦牛具有高度的抗逆性,在迪慶州高寒牧區,牦牛更是不可缺少的優良畜種,藏族同胞日常生活中肉食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牦牛奶中提取的酥油,是藏族人民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食品,是典型以草換肉奶的家畜[10]。牦牛肉和奶品質好、口味佳,是典型的綠色食品,毛皮和角可制作裝飾品,具有顯著的地方特色。隨著香格里拉旅游業的興起,中甸牦牛系列產品將獲得更多消費者的青睞。因此利用科技手段提高牦牛綜合生產性能,提高出欄率,實現生產方式由粗放數量型向集約質量效益型轉變的產業化開發,加大牦牛系列產品精深加工,提高產品附加值,對迪慶州牧區經濟的發展、維護高寒草地生態系統平衡、促進藏區穩定加強民族團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張容昶.中國的牦牛[M].蘭州: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194-214.
[2] 和占星,王向東,黃梅芬,等.中甸牦牛、迪慶黃牛和犏牛的乳的主要營養成分比較[J].食品與生物技術學報,2015,34(12):1294-1301.
[3] 孫學會.中甸牦牛品質特征變化與應對措施探討[J].畜牧與飼料科學,2016,37(9):104-105.
[4] 陳勇,何志瓊,陳志遠.對牦牛雜交改良的理論性研討[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33(6):1326-1330.
[5] 何世明,馮吉安,余忠華,等.誘導牦牛同期發情的幾種處理方法研究[J].草業與畜牧,2008(6):25-28.
[6] 阿秀蘭,左春偉,拉巴卓瑪,等.牦牛程序化人工授精技術推廣試驗效果觀察[J].草業與畜牧,2015(5):46-49.
[7] 陳學禮,和嘉華,鄒淑昆,等.中甸牦牛程序化人工授精技術應用的必要性分析[J].當代畜牧,2017(5):31-32.
[8] 娘杰吉.冬春季牦牛半舍飼養殖試驗[J].山東畜牧獸醫,2017(11):9-10.
[9] 曹立耘.牦牛飼養及管理技術[J].農村實用技術,2015(9):43-45.
[10] 許春喜.牦牛生產性能低下的原因分析及提高措施[J].青海畜牧獸醫雜志,2011,41(4):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