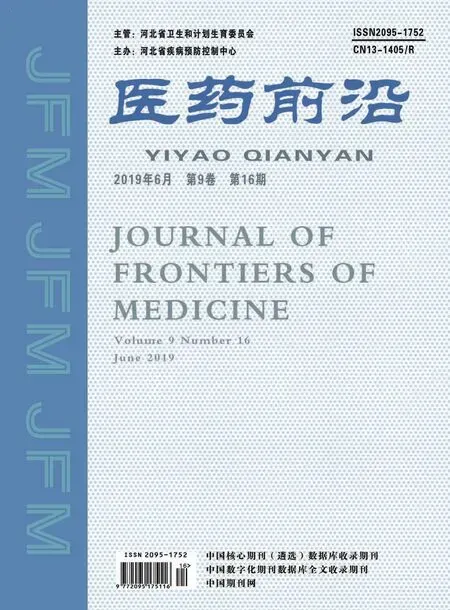一起輸入性惡性瘧疾疫情調查分析
楊吉星 李童 任慧 洪亮 陳道湧(通訊作者)
(上海市虹口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上海 200082)
2017年6 月26 日15 時21分,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以下簡稱“區疾控中心”)接某醫療機構(簡稱“B醫院”)電話報告,稱該院診斷2例惡性瘧病例。而后經區疾控中心調查核實為一起境外輸入性惡性瘧疫情,現將情況報告如下:
1.材料與方法
醫院實驗室采用瘧疾快速診斷檢測(RDT)試劑,區疾控實驗室采用瘧疾RDT試劑,吉姆薩染液對病例全血厚薄血膜凃片染色后進行鏡檢。采用登革病毒IgM抗體和IgG抗體檢測試劑盒(ELISA法)。采用熒光定量PCR檢測通用登革熱病毒(DENV)核酸、登革熱病毒1型(DENV-1)、2型(DENV-2)、3型(DENV-3)、4型(DENV-4)核酸。標本送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心進行流行性出血熱抗體檢測。
2.結果
2.1 病例1發病就診經過
病例1,女,59歲,離退人員。2017年6月21日晚上,在上海現住地家中出現惡心、嘔吐、發熱、乏力、頭暈、腹瀉、黃水樣便(4~5次/天)及尿液紅茶色等癥狀。6月23日出現發熱(自測體溫40.6℃),于6月23日晚上到某醫院(簡稱“A醫院”)就診,門診體查血常規,紅細胞(RBC)4.67×1012/L,血紅蛋白濃度(HB)142g/L,血小板(PLT)12×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n(%)]91.5%,淋巴細胞百分比(L%)3.0%,C反應蛋白(CRP)115.35mg/L,平均血小板容積0.0,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274.00U/L,尿常規結果為尿隱血“+++”,尿蛋白定性“++”,白細胞“+”,當天予以頭孢類藥物靜脈滴注。因患者自述靜脈滴注有疼痛感,6月24日醫生更換為以非頭孢類的抗生素予以靜脈滴注,藥名具體不詳,癥狀未減輕,最高體溫40℃。
6月25 日四肢皮膚多處出現瘀斑,伴惡心、乏力等癥狀。6月26日前往B醫院就診,門診體查全身皮膚中度黃染、四肢可見瘀斑、左側結膜出血,雙側鞏膜黃染,口腔黏膜白斑,咽紅。血常規,RBC3.61×1012/L,HB 110g/L,PLT 14×109/L,N%18.8%,嗜酸性粒細胞百分比0.2%。血生化ALT 200U/L,天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175U/L,L-γ-谷氨酰基轉移酶118U/L,乳酸脫氫酶794U/L,淀粉酶525.55U/L,總膽紅素100.97μmol/L,直接膽紅素69.75μmol/L。瘧原蟲檢查:血片鏡檢結果為惡性瘧原蟲環狀體陽性,RDT檢測結果為惡性瘧陽性。6月26日B醫院以“惡性瘧”病例收治住院治療,給予青蒿琥酯進行抗瘧治療,同時給予保肝、護胃等對癥支持治療,共住院治療17天。6月28日血檢瘧原蟲轉陰,后經多次復查血瘧原蟲陰性,于7月13日予以出院。
2.2 病例2發病就診經過
病例2,男,62歲,離退人員,與病例1為夫妻關系。2017年6月23日晚上,患者在上海現住地出現發冷、頭暈、乏力、食欲下降癥狀,6月24日凌晨出現發熱癥狀發熱(自測體溫39℃)。發熱持續至6月24日白天。6月24日晚上與妻子一同到A醫院就診,門診體查血常規,RBC 4.91×1012/L,HB 149g/L,PLT84×109/L,N%17.0%,CRP32.04mg/L,平均血小板容積8.6fl。當天予以頭孢、柴胡顆粒、清開靈回家口服。6月25日再次出現發冷癥狀,大約半小時后持續發熱(自測體溫39℃)。
6月26 日前往B醫院就診,門診體查血常規,RBC 4.61×1012/L,HB 140g/L,PLT 31×109/L,N%25.60%,嗜酸性粒細胞百分比0.6%,血生化L-γ-谷氨酰基轉移酶73.00U/L,乳酸脫氫酶327.00U/L,總膽紅素22.80μmol/L,直接膽紅素7.97μmol/L。瘧原蟲檢查:血片鏡檢結果為惡性瘧原蟲環狀體陽性,RDT檢測結果為惡性瘧陽性。6月26日由B醫院以“惡性瘧”病例收治住院治療,給予青蒿琥酯進行抗瘧治療,同時給予保肝、護胃等對癥支持治療,共住院治療17天。6月28日血檢瘧原蟲轉陰,后經多次復查血瘧原蟲陰性,于7月13日予以出院。
7月15 日再次出現發熱,體溫38.5℃,伴咽痛不適,7月16日前往B醫院血檢瘧原蟲陰性,給予頭孢丙烯治療后咽痛減輕,但每日仍有發熱,無明顯畏寒寒戰及大汗。7月20日再次前往B醫院檢查血常規,紅細胞4×1012/L,血小板48×1012/L,淋巴細胞百分比16.30%,嗜酸性粒細胞百分比3.6%。瘧原蟲檢查:血片鏡檢結果陽性,RDT檢測結果為惡性瘧陽性。7月20日B醫院再次以“惡性瘧”病例收治住院治療,給予青蒿琥酯進行抗瘧治療,同時給予保肝、護胃等對癥支持治療,共住院治療8天。7月21日血檢瘧原蟲轉陰,后經多次復查血瘧原蟲陰性,于7月28日予以出院。而后半年內未發現瘧疾復發現象。
2.3 流行病學調查
經旅行團組織,兩名患者與6名國內同行人員自6月3日-16日前往南非旅游,一直同行。自述在南非曾前往野外郊游,曾有6晚睡在帳篷里。在國外全程未使用蚊帳,未使用驅蚊水、蚊香等防蚊措施。兩名患者自南非旅行回國后至發病在上海生活。
2.4 治療情況
兩名患者在B醫院住院接受抗瘧治療,醫院均予以青蒿琥酯靜脈推注治療,首次劑量120mg,4h后再給予120mg,第2天起給予劑量120mg/d,共注射7天,總用藥劑量為960mg的標準療程。
2.5 相關檢測結果
6月26 日采集兩名病例靜脈血標本,區疾控中心實驗室分離血清進行登革熱病毒核酸、IgM抗體和IgG抗體檢測,結果均為陰性;標本送市疾控中心進行流行性出血熱IgG抗體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2.6 病例感染類型研判
兩名病例均為境外輸入性惡性瘧病例。判斷依據如下
惡性瘧確診依據:(1)均有明確的瘧疾流行區流行病學史;(2)均有發熱、畏寒等臨床癥狀和血小板降低等血象特征;(3)實驗室檢測和復核結果均為惡性瘧;(4)用青蒿琥酯治療后癥狀緩解,治療有效。
兩名患者在此次發病前一周左右有境外流行病學史。即2017年6月3日-2017年6月16日到瘧疾流行區南非旅游,與回國后一周左右發病,正在境外瘧疾感染的潛伏期。
兩患者回國后至發病前(6月16日-6月21日)一直居住在上海家中。上海非惡性瘧流行區,且本區近五年未監測到傳瘧媒介按蚊,可排除本地感染。
3.討論
據WHO統計,由于青蒿素類藥物的使用,自2000-2012年瘧疾病死率下降了45%,對于5歲以下兒童,瘧疾病死率下降了51%[1]。2005年WHO在相關報告中指出要嚴肅面對抗瘧藥敏感性降低的情況,并警告很可能會出現青蒿素耐藥性[2]。2006年1月19日,WHO正式發出通告,要求停止生產、銷售單一青蒿素制劑或使用青蒿素單一療法治療瘧疾,并呼吁臨床醫生使用復方青蒿素制劑,也就是以青蒿素類藥物為基礎的聯合用藥(ACTs)。病原體從體內清除的時間是WHO衡量瘧原蟲對青蒿素類藥物產生耐藥性的基礎指標。若患者在服藥3 d后體內瘧原蟲檢測仍呈陽性則判定為產生疑似耐藥性;若在7 d后瘧原蟲仍呈陽性則判定為已產生耐藥性[3]。在21世紀初,云南和海南曾相繼報道抗蒿甲醚的惡性瘧病例[4-5]。本文中的病例在青蒿琥酯全程治療后僅不足半月就再次復發,雖未達到對青蒿琥酯疑似耐藥的標準,但應注意是否存在敏感性降低的現象。
隨著我國對外交流的日益頻繁,出境旅游或務工的人員與日俱增。距文獻報道非洲地區瘧疾臨床癥狀不典型、表現多樣化,僅有20.9%有典型寒戰、發燒、出汗等癥狀;64.1%的病例表現為發燒、輕度頭痛、全身或部分肌肉酸痛,并有咳嗽等呼吸道癥狀;還有11.4 %以腹瀉為首發癥狀[6],很容易誤診。本文病例也是以惡心、嘔吐、腹瀉為首發癥狀,很容易和胃腸炎相混淆。所以應該加強我國臨床醫生的培訓,在接診時注意詢問近期有沒有瘧疾流行區的旅行史,增加瘧原蟲血片鏡檢,減少漏診或誤診的發生。上海作為國際化的大都市,設有國際機場、海運港口等對外交流的窗口,面臨著瘧疾輸入病例的嚴重威脅。各醫療機構應做好瘧疾檢測的技術儲備和抗瘧藥的物資儲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