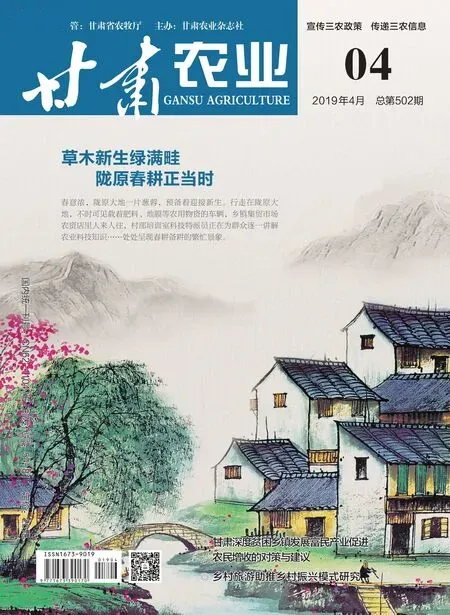組織力與適應性:基于基層黨組織視閾的邏輯分析
黨曉慶,張 峻
中共武威市委黨校,甘肅 武威 733000
針對基層黨組織虛化、弱化、邊緣化的問題[1],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把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等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黨支部要擔負好直接教育黨員、管理黨員、監督黨員和組織群眾、宣傳群眾、凝聚群眾、服務群眾的職責,引導廣大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這是黨中央對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在新時代提出的新要求。實際上,這是從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入手,重新對基層組織的職能進行了新的定位調整,也是強化基層黨組織適應性的重要舉措。本文將對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和適應性的邏輯關系進行初步分析。
一、提升組織力是政黨適應性的必然要求
適應性在政治學中是一個復雜的概念,這些年來中外學者進行了較為深刻的研究。最早將政黨與適應性二者結合起來分析研究的是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他在研究政黨政治秩序的時候發現,“組織和程序的適應性越強,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反之,適應性越差,越刻板,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2]在他看來,政黨適應性是衡量政黨政治制度化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政黨實現穩定性的重要能力。這個能力,使得政黨在面對社會機構、經濟體制乃至群眾心理等諸多要素變化時能夠適時調整組織結構和功能目標。對于這種適應性,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布魯斯·迪克森認為既有來自政黨與外部環境互動中所采取的功能性調整,又有為了適應環境而進行的自我轉變。他稱之為效能型適應和回應型適應,二者都是政黨組織謀求生存發展的一種改革途徑。國內學者張小勁、楊光斌、胡榮榮、聶平平等人對政黨適應性的研究在充分吸收國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同時,也試圖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范式,他們分別從制度性和社會性、內源性和外源性進行了對政黨適應性的考察研究。這些研究不一而足,研究的角度不同,闡述的理論觀點也比較復雜,綜合起來,政黨適應性就是指政黨在發展過程中面對環境挑戰所形成的調整適應能力,是一種內外動態互動的結果。[3]由此看來,國外國內學者們的研究,基本都是在政黨運動變遷的宏觀整體狀態來分析研究,還沒有人把它放到政黨微觀層面,放到政黨組織體系最基本的構成要素——基層黨組織這樣一個視角去分析討論。
組織力是組織在設計和運行以及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合力。[4]黨的基層組織組織力集中體現為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動員能力,它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方面來自于內部的組織力,即組織開展黨內政治生活、進行黨員教育管理、引領群眾開展學習、按時按質完成黨組織任務等能力,這是一種內聚力;另一方面來自于外部的組織力,即組織動員人民群眾實現奮斗目標、完成歷史和時代使命的能力,這是一種整合力。對于基層黨組織來說,它就是一種系統性能力,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對黨員隊伍的教育管理和基層黨組織自身體系的建設上,另一方面對群眾的服務能力、對社會的治理能力和資源調配與整合上。
高度重視提升基層黨組織組織力這是黨的建設一條重要經驗。在革命戰爭年代,更多地是從外部把群眾及社會力量組織動員起來,“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支部建在連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組織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群眾創造戰場”“放手發動群眾,團結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則更多是從內部入手,“貫徹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方針,必須扎實做好抓基層、打基礎的工作,使每個基層黨組織都成為堅強戰斗堡壘”“要以‘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為契機,使各級黨組織書記抓黨員隊伍建設的意識樹起來、把責任扛起來,激活基層黨組織,增強基層組織力”,等等。這些重大思想和重大實踐都是我們黨增強領導力、組織力和戰斗力的生動體現。
以上通過適應性和組織力邏輯起點、以及理論發展的分析,使我們看到了他們二者的確存在著不容忽視的邏輯關系。從中國共產黨不同歷史時期的重大思想和實踐來看,我們提高黨的組織力,正是為了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因而必須要對組織結構、組織能力進行調適。毛澤東時期通過思想教育和運動整頓等手段實現了政黨調適,奠定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從而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5];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從黨的基層組織調整入手,走過了基層組織制度化完善、基層組織功能進一步拓展這樣一個發展路徑,一直沿著適應性這樣一個路子邁進。由此,可以看出,組織力的提升,正是為了適應性,它是政黨適應性的必然選擇和要求。
二、適應性是衡量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水平的重要標準
從塞繆爾·亨廷頓理論來看,適應性也是基層黨組織后天能夠獲得的組織性的另外一種表達方式,因為,他測量的那把尺子就是黨組織的制度化水平。用制度化為標準,衡量基層黨組織有兩個變量,一個是來自于組織性的力量,一個是來自程序性的力量,二者均可用制度化程度得到測量。由此看來,適應性的最終目標就是實現組織制度化。那么,體現組織性程度制度化水平的組織力,便理所應當以適應性為標準來予以衡量。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在轉型期間,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導致單位制解體,大量公共性事務進入基層社區,“兩新組織”和大量流動黨員的涌現,造成黨組織系統的對外對內控制能力削弱,出現了黨對社會對環境以及對自身變革的一種不適應性。這種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弱化,首先表現在黨員隊伍的松散化,比如基層黨組織內部黨員意識淡化,積極性、主動性缺失,理想信念動搖,政治定力下滑等;其次表現在基層黨組織自身組織體系的碎片化[6],比如基層黨組織組織覆蓋面不足,黨群聯系松弛,黨員之間以及黨員與群眾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甚至部分黨員黨性淪喪,價值觀念失范等;三是表現在黨群關系疏離,凝聚群眾的能力減弱,比如群眾對基層黨組織的信任度下降,基層黨組織服務群眾的方式方法流于形式等;四是表現在基層黨組織在基層治理中被邊緣化,應對多元社會發展的能力不足,比如基層黨組織從管理性到治理性轉變中,對出現的新現象不能進行有效應對等。
在此情況下,如何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工作,進一步增強黨的適應性,用適應性標準來衡量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提升程度就成為一種可操作的選擇。近年來,隨著農村新經濟群體的出現,比如,大量的農村種植、養殖專業合作社的出現,隨之而來就是在這些專業合作社當中建立起來相應的黨組織,以便更好的發揮這些專業合作社中黨組織引領發展的重大作用。這種把支部建在產業鏈上的模式,無論是基層黨組織的結構還是其功能都在新形勢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而衡量高度發達的組織的真正尺度是其職能的適應性而非職能的特定性。[2]這樣,我們去考察這些雨后春筍般出現的新的基層黨組織,就能通過適應性來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組織適應性越強,其組織職能就越穩定,發揮作用就越持久。而無論是定量還是定性分析,都離不開與社會與環境的聯系。因此,保持與社會的溝通與聯系是提升基層黨組織適應性的關鍵途徑。[7]毋庸置疑,與社會的溝通聯系能力,也正是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外在呈現。因此,當我們把制度化看作測量適應性的標準的時候,基層黨組織其職能的適應性就突出表現在制度化程度上;同樣,當我們把基層黨組織的適應性看作組織力標準的時候,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提升就突出表現在其適應性上。
之所以我們要重視基層黨組織職能定位、作用發揮,增強其適應性,提升其組織力,目的就是要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黨在社會基層組織中的堅強戰斗堡壘。這是黨適應新時代的需要,適應基層社會發展的需要。能不能在社會基層組織中擔當政治領導力,能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結構、形態、生產生活方式等的深刻變化,能不能真正成為群眾的“主心骨”,能不能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推進工作,能不能自我革新,著力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所有這些,都是為了適應性的要求。而這些也都是提升基層黨組織組織力的基本要求和手段。適應性和組織力是成正比的,提升基層黨組織組織力是其適應性的充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