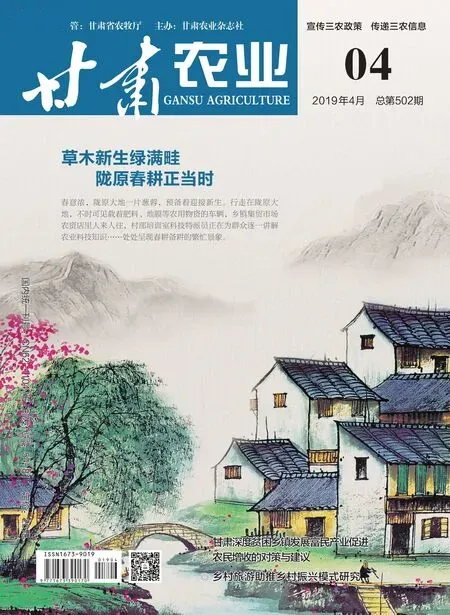關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綜述
寇 煜
蘭州財經大學 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甘肅 蘭州 730020
一、引言
幸福感一詞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便將公眾幸福提到了一定的高度,現世生活的滿足便是公眾的幸福源泉,并指出政府必須聽從人民的意見,而且為了確保公共的安寧,必須建立他們所贊成的制度。由此可知幸福感之于國民的重要性。我國在十九大以來,一直致力于讓改革的紅利更直接惠及全體國民,特別是對于在過去的發展過程中未能充分分享發展紅利的人群,更注重他們幸福感的提升。隨著我國社會結構轉型加速,各個領域的體制改革不斷推進和完善,不少學者開始轉向民生環境和政府規制對于幸福感相關性的研究。
二、研究現狀
(一)對居民幸福感的認識
從國家對居民幸福的重視程度來看,不丹在現代化模式之外尋找到一種新的以幸福為主旨的發展模式。1970年該國首先提出國民幸福總值(GNH)的概念,這一指標體系主要包括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個方面,這對于轉變國家發展的觀念有著重要的意義。[1]而學者對于主觀幸福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早期文獻主要針對個人快樂幸福的來源和影響因素進行研究。[2]進入21世紀,隨著公共經濟領域對全社會宏觀環境的關注,收入差距、通貨膨脹、失業率、政府質量、空氣狀況等宏觀環境因素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成為學者關注的熱點,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現了跨學科的融合,涵蓋了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環境學等多個學科。[3]
在我國政府層面,幸福感作為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這一政府工作要求,體現著我國政府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讓廣大人民得到實惠獲得幸福是長期的工作重點和方向,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打贏脫貧攻堅戰就是提高人民幸福感的重大舉措。從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來看,多數研究者認為幸福感這一概念內涵豐富,其體現了社會心理體系的高度復雜性,一般來說,幸福感是人們對自身生活質量高低的自我評價。[4]居民的幸福指標分為宏觀指標和微觀指標,既包括通過收入、社會保障、公共設施、醫療、教育、政治環境、自然環境等客觀條件可以增強幸福感;同時還包括通過家庭住房、戶籍、家庭收入、文化程度等微觀層面的條件來增強幸福感。[5]此外從財政的角度,宏觀稅負、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等也影響著居民幸福感,可見影響居民幸福的因素有很多。
(二)居民幸福感的考量
運用幸福經濟理論對現實問題進行研究最早見于美國經濟學家Easterlin,他指出:居民的主觀幸福感與其收入水平和國家整體經濟增長情況之間并未呈現出簡單的正相關系。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幸福悖論。[6]近年來,國內有關民生問題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涌現了大量成果,研究視角包括收入差距和機會不均、環境污染、政府質量、城市房價、親貧式支出等,這些研究涉及民生問題的諸多領域,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豐富的成果支持。[7-10]
文宏和劉志鵬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對2002年、2009年、2011年和2015年的數據分析得出:十八大以來我國總體居民幸福感呈上升趨勢,但不同階層還是呈現出不均衡不平衡的特點;[11]馬萬朝,李輝在2016年基于我國微觀經濟數據的研究得出收入與居民幸福感直接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基于我國GDP的增長,居民收入的增長確實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7]邢占軍針對中國的研究提供了經驗和證據,富裕程度較低地區的居民個人收人與幸福感之間的相關性要強于富裕程度高的地區。[12]
公共服務的職能在于通過構建安全、穩定、公平的社會環境,在提高居民財產和人身安全保護的同時,也能夠保證社會公平正義,進而提高了居民幸福感。研究證實,政府教育支出和公共醫療等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而基建不完善、機會不公平等在地域之間存在幸福感的剝奪效應,城鄉之間現象尤為明顯,此外社會不穩定、環境污染對不同收入群體的影響程度也存在差異性,低收入群體缺乏逆向補償能力,幸福感下降明顯,這也直接造成了同一區域環境福利的不公平。人們選擇城市居住的重要原因是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若公共服務業發展與不斷加快的城鎮化進程難以協調,隨之而來的“城市病”則導致居民幸福感下降。[13]
(三)政府規制與居民幸福感
一國的政治環境尤其是國家的政治體制與其公眾的主觀幸福感是息息相關的。關于政府規模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國外文獻提供了一個主流的觀點:政府規模與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關系,即存在最優政府規模,能使幸福感達到最大值。[14]在最優的政府規模下配套最優的政府效率是關鍵,政府在為居民提供公共服務以滿足其基本需求的同時,需要征稅籌集資金維持政府的運轉,政府規模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取決于其提供的公共服務呈現的績效水平與征稅所造成的“稅負痛苦”之間的權衡比較。[15]政府規模的大小都會影響政府征稅力度與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均衡關系。目前研究稅負水平與居民主觀幸福感之間關系的文獻,主要集中在單個稅種的稅負水平和整體宏觀稅負水平兩個方面。作為公共商品供給價格的稅收和居民消費的公共商品水平都會影響居民的主觀幸福感,研究中國居民的稅負對幸福感的影響,應該綜合考慮兩者的作用。魯元平,楊芳結合CGSS的數據以及城市層面的數據,研究稅負、稅收表達權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并發現:我國居民承擔的稅負與其主觀幸福感呈倒“U”型關系,我國稅負水平對居民幸福感的損害從平均意義上而言并不嚴重;在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經濟地位以及城鄉居民之間,稅負水平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存在異質性。[16]
再者,我國現有的財政分權制度往往會扭曲公共支出的結構,往往不利于居民整體福利水平的提升。[17]其核心在于必須清楚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此基礎上政府要轉變職能,逐漸從市場能做以及政府做不好的領域退出。其次,不科學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也扭曲了政府的支出結構,嚴重損害了居民的幸福感。[18]
在政府規制和管理方面,陳剛,李樹利用OLS模型列匯報了腐敗、民生性支出對居民幸福的影響并通過和order probit模型回歸結果對比后發現,關鍵變量的回歸系數和顯著性水平都沒有發生太大變化,都證實民生性支出顯著正向于居民主觀幸福感,而腐敗通過降低民生性支出的比例,進而負向作用于居民主觀幸福感。[9]腐敗嚴重破壞了公共權力的運行秩序,侵害了社會公平正義,影響了經濟發展和居民幸福感,[19]人們對安全、穩定、公平等的關注度往往與其收入水平成正相關關系,高收入人群或城市居民對此類公共服務的關注程度會比低收入人群或農村居民更高,進而獲得更多的快樂和滿足感。[20]
三、總結與展望
由于近年來中國出現了經濟領域“幸福停滯”的增長困局,針對幸福影響因素的研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但是直接進行變量之間影響關系驗證的文獻居多,從邏輯上進行機制和理論關聯檢驗的研究較少。此外從中國獨特制度背景的視角對公共服務支出結構與居民幸福感關系的研究也相對缺乏,公共服務的支出結構直接影響了公共服務各領域的服務半徑和質量,進而影響了居民幸福感,現行財政分權體制下的公共服務支出結構更需要分析和研究。
總之,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并未從根本上促進居民幸福的提升,傳統的政績考核標準并不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政府需要加強財政管理和規制,保證居民公共福利覆蓋的公平性,同時提高公共服務的配置效率,做到稅收表達權的提升,使稅收決策符合全體居民的真正需求,政策制定者必須真正做到以人民的幸福感作為發展的內涵與宗旨。[1]通過對已有國民幸福指標體系的歸納,再結合財政支出的具體統計指標來構建能有效促進宏觀國民幸福的財政考量指標體系,從而促使以財政為核心的政府行為從實現經濟增長的單一目標轉變為保證經濟發展、關注生活倫理與創建和諧環境的多目標體系。所以說,如何利用這些工具變量實現經濟與環境的最優配置以提升人們的幸福感,發揮財政的二次分配作用顯得至關重要,應是下一步要研究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