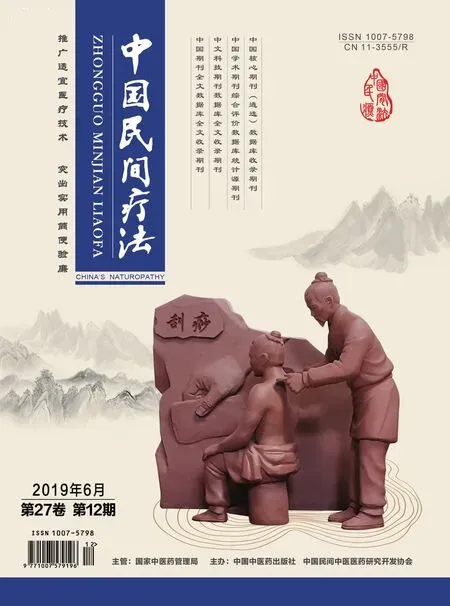彭氏婦科學術思想及診療特色淺析※
彭應濤,彭慕斌
(湖北省應城市中醫院知名中醫工作室,湖北 應城432400)
彭氏婦科歷史悠久,歷經5代,傳承百年,濟世救人無數,聲名遠播,有口皆碑。彭碧山(1884—1951年)少時跟隨堂伯父彭登朝學醫,得其真傳,初步奠定彭氏婦科發展基礎。彭景星生于1930年,自幼在其父碧山公督導下研習經典,并臨床侍診,歷時6載,盡得其傳,18歲懸壺鄉里。彭景星1957年畢業于湖北省中醫進修學校第1屆師資班,1979年被孝感地區衛生局授予“名老中醫”稱號。彭景星先生畢生潛心研究中醫婦科,系彭氏婦科代表人物,退休后繼續指導學術經繼承人開展工作,2014年被湖北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列為“知名中醫工作室”。
經過5代人的不懈努力,目前已確定了崩漏、盆腔炎、缺乳、更年期綜合征、乳腺增生癥5個優勢病種的臨床診療路徑,總結了加味桂枝茯苓丸、丹紅散、調經消斑湯、歸脾膏等10余首經驗方。先后有《王孟英婦科治痰舉要》《盆腔炎從癰論治》等論文發表,并有《彭景星醫論醫案》《彭景星講析名醫醫案》《潛齋方藥縱橫》3部著作出版,初步形成一套獨特的學術思想體系和治療方法。
1 學術思想
1.1 女子以肝為先天 《素問·上古天真論》有“太沖脈衰少,天癸竭”的論述,說明女子天癸與腎經密切相關,與肝經也有關聯。蓋肝主疏泄,主藏血,沖脈起于胞中而通于肝,有“血海”之稱。而女子以血為本,肝在女性生理上具有腎主生殖發育所不能起的作用,有“女子以肝為先天”之說。
“女子以肝為先天”重點強調了女性生理、病理的特殊規律,女子經、孕、產、乳以血為本、以氣為用的生理特點及經、帶、胎、產的病理變化,均與肝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密不可分。調肝法作為婦科常用之法,包括養肝、舒肝、疏肝、清肝、瀉肝等法,并有四物湯、柴胡疏肝散、丹梔逍遙散、龍膽瀉肝湯等代表方。彭氏仿王孟英“運樞機、通經絡”之用藥法,著重調理“樞機氣化”,用葦莖湯、蠲飲六神湯、雪羹湯等治痰調肝,治療經、帶、胎、產諸疾,屢起沉疴[1]。人體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且稟賦有別,見證各異,重視肝經,并不是否認腎、心、脾等臟腑功能在女性健康中的作用。我們應立足整體,辨證論治,方臻完善。
1.2 重視血瘀致病作用 彭氏婦科重視血瘀在婦科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的意義。認為女性生理特點與氣血密切相關。無論外感六淫,還是七情內傷,以及勞逸失常、邪毒感染等因素,均可直接或間接導致瘀血內停,出現月經不調、崩漏、閉經、痛經、惡露不絕、癥瘕包塊等。臨床常見證型包括氣滯血瘀、氣虛血瘀、寒凝血瘀、濕熱瘀阻及久病致瘀等,治療以活血化瘀為基本大法。臨床習慣用方為少腹逐瘀湯、桂枝茯苓丸、溫經湯、桃紅四物湯等,常用藥物包括當歸、桃仁、澤蘭葉、雞血藤、茺蔚子等。
1.3 遣方用藥四物為先 因月經、胎孕、產育、哺乳均以血為用,以致機體相對處于血不足、氣有余的狀態。四物湯為補血專方,又為調經良劑[2],月經不調及胎前、產后諸疾,常以本方作為基礎方。本方合四君,名八珍湯,主治月經過少,面黃頭昏,氣短心悸,脈細弱;本方加人參、黃芪,名圣愈湯,主治月經先期,量多色淡,肢倦乏力;本方加桃仁、紅花,名桃紅四物湯,主治月經量多,色紫質黏夾塊者。此外,以四物湯加味衍化而成的益母勝金丹、四二五合方、泰山磐石散、十全大補湯等,均為彭氏婦科臨床常用方劑。正如方歌所云:“四物地芍與歸芎,血家百病此方通。”
2 診療特色
2.1 辨證與辨病結合 中醫對疾病的診斷比較籠統,有些診斷只是一種癥狀或證候。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先進醫療儀器廣泛應用,為診斷疾病、確定病名提供了準確的客觀依據。試以痛經為例,中醫將其分為氣滯血瘀、寒濕凝滯、氣血虛弱、肝腎虧損等證型而施治。而用B超、CT檢測,則可將病因分為盆腔炎、子宮肌瘤、子宮內膜異位癥或其他疾病,診斷之精細,明顯優于傳統醫學。因而在婦科臨床上,彭氏婦科主張辨證與辨病相結合的思路,力求四診客觀化,辨證規范化,從而提高療效。
2.2 時方與經方并重 彭氏婦科臨證處方,時方與經方并用,兼收并蓄。處方依次以丹梔逍遙散、歸脾湯、少腹逐瘀湯、止帶湯、三青(竹茹、桑葉、絲瓜絡)湯等時方使用率較高,但桂枝茯苓丸、溫經湯、當歸芍藥散、膠艾湯、腎氣丸、當歸四逆湯等經方也廣泛應用。如逍遙散是調和肝脾的代表方劑,常用于月經失調、痛經、乳腺增生等病,是彭氏婦科使用率最高的方劑。以逍遙散為基礎方加味的丹梔逍遙散、黑逍遙散、加味逍遙散,以及自擬丹梔消痤湯,將其應用范圍進一步拓展,在功能性子宮出血、更年期綜合征、精神病、痤瘡等方面,療效較好。彭氏婦科對經方溫經湯推崇備至,認為其是天然的雌激素,調經、種子,首選溫經湯,凡月經不調、不孕癥、崩漏加減應用,獲效者眾多。
2.3 驗方與單方補充 彭氏婦科在辨證用方的同時,摸索總結出很多簡、便、廉、驗、安全的經驗方,如由桂枝、茯苓、牡丹皮、冬瓜仁、葦莖等組成的加味桂枝茯苓丸,治療濕熱瘀滯型附件炎、盆腔炎收效良好;以滋水清肝飲加味而成的調經消斑湯,治療黃褐斑、面部色素沉著也有一定療效。此外,還收集了一些方簡效捷的小單方,如更年期出現烘熱、自汗等氣火偏亢病證,取玄參30 g,開水泡服,每可獲效;地榆苦酒煎為止崩防脫有效方劑,崩漏“塞流”取地榆50 g,用醋(古稱苦酒)煎,露天置一晚,次晨溫服,或可收效。
2.4 膏方與湯劑交替 湯劑功專力宏,臨床應用廣泛,在癥狀改善、病情穩定后改用膏劑鞏固治療,此乃彭氏婦科又一特色。由于膏劑方便、快捷,可提高服藥依從性,往往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若能在萬物封藏的冬季服用療效更佳。常用的膏方有溫經膏、歸脾膏、滋陰補腎膏、復方四物膏等,用于月經過少、未老先衰、亞健康等療效確切。對大病、出血、手術后的康復治療,婦科腫瘤患者手術、放化療后恢復體質,也有一定作用。
2.5 外治與內治配合 《理瀹駢文》云:“外治之理即內治之理,外治之藥亦即內治之藥,所異者法耳。”神闕屬于任脈,位于中下焦之間,《針灸大成》有“神闕穴主百病”的記載[3]。從現代醫學觀點來看,外治法可能通過神經、體液的作用而調節神經、內分泌、免疫系統,從而改善各組織器官的功能,促進機體恢復正常。臍療是將藥粉貼于臍部(神闕)后,在高效透皮促進劑的作用下,從而發揮其藥理作用。如寒濕凝滯型痛經常用痛經散(由血竭、肉桂等組成)貼臍,可收溫經散寒止痛之效。丹紅外敷散[由丹參、紅花、三棱、赤芍等組成,鄂藥制字(2001)第J211~028號],外敷于下腹部,一方面通過熱敷加快局部血液循環,有類似“理療”的作用;另一方面通過藥物滲透作用直達病變部位,利于炎癥吸收;該藥在治療慢性盆腔炎、附件炎性包塊及闌尾周圍膿腫等方面,療效令人矚目。此外,苦黃洗劑(由苦參、黃柏、白頭翁等組成)可解毒殺蟲止癢,治療外陰炎癥深受病友青睞。長期臨床實踐觀察發現,外治法有“四兩撥千斤”作用,不可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