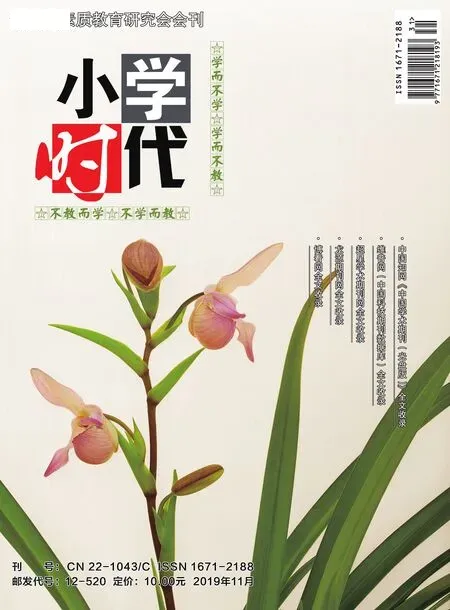找尋略讀課文教學的生命本色
——略讀課文教學策略舉隅
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qū)實驗小學 厲水根
隨著新課程的推行,人教版教材從小學第二學段第五冊開始,遂將課文分為精讀和略讀兩種類型。后隨年級升高,略讀的分量逐步增大。到第七冊,略讀課文的篇數約占全冊課文的44%,也不僅僅是出現在每個單元的末尾,而是融在其中,與前面的精讀課文密切聯系,儼然有成半壁江山之勢。至第三學段五年級上冊起,略讀課文與精讀課文完全是平分秋色了。
小學語文教材中選用的略讀課文幾乎篇篇文質兼美,常常把我陶醉。“我要把自己的感動傳遞給更多的人”,這是我當時的想法,希望通過自己一次又一次“堂吉訶德”式的無畏挑戰(zhàn),輕輕拂去籠罩在個人眼前的層層迷霧,找尋略讀課文教學的生命本色。
策略一:廣征博引,教略學豐
小語方面的專家沈大安老師曾指出:略讀也就是大略地讀,可以叫粗讀。體現在教學上,就是不求精細、全面,但求大致理解、大致掌握即可。以“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為佳。上海師范大學吳忠豪教授更是認為:兒童的閱讀就是讀懂,讀懂就是我們所說的“略讀”。 精讀課文擔任著授之以“法”的角色,而略讀課文則為用“法”服務。葉圣陶老先生對精讀和略讀的處理有著獨到精辟的論述:“精讀文章,只能把它認作例子與出發(fā)點,既熟悉了例子,奠定了出發(fā)點,就得推廣開來,閱讀略讀書籍。”從上述專家的觀點,不難看出略讀課文的教學是不同于精讀課文,特別是在內容理解上要求低于精讀課文,一般是“粗知文章大意”,幫助學生大體理解內容即可。
略教內容之后,多余的時間干什么?筆者認為余下的時間應充分挖掘文本隱含的各種資源,如文章表達形式、作者生平、作者其余作品、同主題作品以及同體裁作品等等,在一堂課中適時呈現,用豐富信息助學生獨立感悟文本。
如執(zhí)教《全神貫注》時,我通過課件適時出示了羅丹的生平簡介,并一一出示羅丹作品圖片,《青銅時代》《思想者》《巴爾扎克》和《雨果》等,在課結束之前又出示了茨威格的生平簡介和原話:“我那時大約二十五歲,在巴黎研究與寫作。許多人都已稱贊我發(fā)表過的文章,有些我自己也喜歡。但是,我心里深深感到我還能寫得更好,雖然我不能斷定那癥結的所在。于是,一個偉大的人給了我一個偉大的啟示。那件仿佛微乎其微的事,竟成為我一生的關鍵。”
這些資料的引入,成為了重要的教學資源,可以達到“一舉三得”之效。一是可以讓學生一下子觸及文本本質,走進人物的內心世界,聆聽其言,感受其心。二是引導學生誦讀簡介,為解讀文本奠定了情感基調。三是由名言帶來的沖擊,為學生課外閱讀埋下了種子,這不吝為一種“潤物細無聲”的課外閱讀暗示。略讀教學是為了培養(yǎng)學生的略讀能力,當略讀成為一種閱讀方式的時候,其指向是為了獲取更大的信息。因而在教學活動中我們要給予學生更多的資源,引導他們進行橫向閱讀。
當然在資源的選擇上,必須尊重學生的認知水平,尊重學生的情感體驗,而不是依教師的個人喜好,不加選擇一股腦兒在課堂中呈現。如武鳳霞執(zhí)教《我和祖父的園子》時,引入了蕭紅的生平資料:重男輕女的父母從小就不喜歡是一個女孩的蕭紅,蕭紅8歲時母親去世了,15歲開始在外漂泊,曾因沒錢交房租被困在旅館中,20歲生下第一個孩子,因無錢撫養(yǎng),把孩子送給他人,后來第二個孩子因病夭折。1938年—1940年,三年間,她生活在五個城市,一直在漂泊之中。1941年,她孤零零一人病在香港,以至于她獨自長嘆——“漫天星空,滿屋月亮,人生如何,為什么這么悲涼。”1942年,蕭紅在香港病逝,時年31歲。
這種資源的引入,筆者實在不敢茍同,因為這對于孩子太過于沉重。武老師不外乎想讓學生全方位了解人物,了解作品。但這種直接讓學生進入成人化的生命體驗,跳過他們本應有的天真童年,這是否太殘忍了?所以資源的選用,也應多從學生出發(fā),讓真正有效的課堂學習資源與課外學習資源互為補充,讓學生習一篇得多篇,舉一反三,做到“教”略而“學”豐,“教”略而“學”不略。
策略二:抓大放小,精略得當
著名特級教師錢正權認為,略讀課文教學應把握好兩點。一是把握好課文在整個單元中的地位。略讀課文應該是精讀課文的有機延伸,是將精讀課文所習得的方法進行實踐運用。二是要把握好方法上的“粗放”。“粗放”也就是允許在略讀課文教學中放棄深摳猛挖字詞含義,但反過來完全“粗放經營”,像“踩西瓜皮,滑到哪兒算哪兒”,泛泛而教,學生如同霧里看花,對文本就不能留下深刻印象,效果也是可想而知。所以教師需選擇重點、精彩之處,引導學生有效研讀,以點及面,達到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之效。
如《桂花雨》這篇文章篇幅較長,在初讀環(huán)節(jié)我設計了兩個層次的讀書。第一層次是要正確流利。第二個層次要求讀出關鍵字。諸如對“全年,整個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氣里”這句,要求學生讀出一個“浸”字,引導學生體會桂花不僅花開時香,晾干了泡茶、做餅也同樣香氣彌漫。桂花,永遠香在人們的心里。它的香,已不受季節(jié)的束縛,香甜了四季,也香甜了人們的生活。又如對“于是,我又想起了在故鄉(xiāng)童年時代的‘搖花樂’,還有那搖落的陣陣桂花雨”這句,讓學生讀出一個“又”字,體會作者不止一次地想起故鄉(xiāng)童年時代的“搖花樂”和“桂花雨”,只是這次母親的話使她又一次想起。淡淡的一個字,卻傳遞出了作者對故鄉(xiāng)桂花的深深懷念。家鄉(xiāng)的桂花,是跟作者童年的快樂連在一起的,那種“搖花樂”和“桂花雨”已植進了她的生命,成為她幸福童年最美好、最耐人回味的記憶……
所以“略讀”教學略去了精讀課文中識字、學詞、學句等諸多頭緒,但不反對文章的重點、精彩之處的精講和引導,教師需使略讀與精讀互相融合,綜合運用,才能在內容理解、情感陶冶與語言感悟上達到比較理想的效果。
略讀教學略去了諸如精讀課文類的字詞深刻解讀,那么余下來的時間就應盡量讓學生去精學表達、精學方法、精學運用……以學定教,把時間充分還給學生。當然略讀課文只有一課時,因此決不能求全求深,抓住一點,一課一得即可。讓學生清楚地知道什么文如何讀,從而為其完全獨立進行課外閱讀打下堅實的基礎。
如執(zhí)教《文成公主進藏》這課時,教師讓學生在默讀課文后提出疑問,然后就圍繞三個問題“課文講述了哪些故事?使臣和文成公主都是怎樣的人?這篇傳說與幾篇寫人的文章進行比較,有什么區(qū)別?”開展教學。第一個問題旨在讓學生學會概括內容,文章讀“薄”。第二個問題可以引領學生關注文本,了解人物。第三個問題對四年級學生看似拔高要求,但在教學中,學生說出了“文章中很多情節(jié)都比較夸張,不可思議;寫人沒有具體寫他們的語言、神態(tài)、動作等;文章中有很多小故事”等獨到的發(fā)現,這不就是傳說的“神奇性、概括性、故事性”等特點,這些收獲雖然朦朧,還不夠清晰,但對學生以后的成長一定助益不少。
這樣的教學充分考慮了教學內容與本冊和本單元其他文本的有機融合,“瞻前顧后”,教學效益得以明顯提高。學生在充分的閱讀實踐中,逐步學會思考,學會閱讀,主動將“知”向“行”轉化。在具體文本的教學中,具體精學什么應因文而異,教師要找準著力點,抓住要求,忽其枝節(jié),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想練,結果什么也沒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