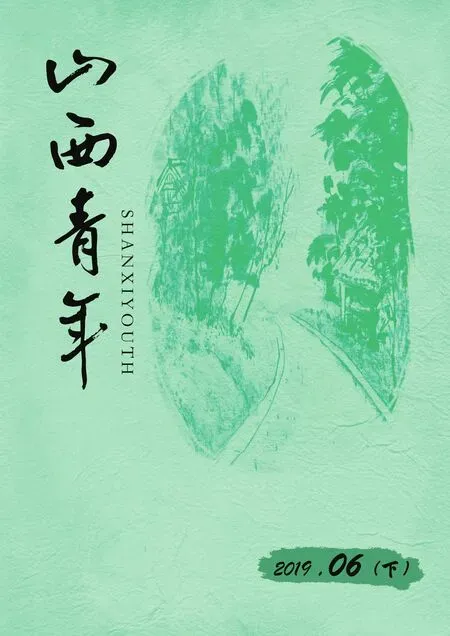期刊創(chuàng)刊號(hào)的鑒賞與研究初探
——以《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創(chuàng)刊號(hào)為例
鄭賀秀
(山西青少年報(bào)刊社,山西 太原 030001)
唐憲宗元和五年(811年),白居易在給元稹的信中,提出了“文章合為時(shí)而著,歌詩(shī)合為事而作”的論斷,這是我國(guó)古代文藝?yán)碚撟顬橹拿}之一。2014年10月15日,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huì)講話時(shí)曾引用過(guò)這句話,指出“一個(gè)時(shí)代有一個(gè)時(shí)代的文藝,一個(gè)時(shí)代有一個(gè)時(shí)代的精神,偉大的時(shí)代離不開與之契合的文藝”。可見,白居易的這一主張仍有深遠(yuǎn)而廣泛的現(xiàn)實(shí)意義。文藝工作者要關(guān)切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汲取時(shí)代營(yíng)養(yǎng),傾聽時(shí)代聲音,把握時(shí)代脈搏,這樣才能創(chuàng)作出積極向上又富于生命力的好作品。
一、創(chuàng)刊號(hào)的根本屬性
近代以來(lái),期刊作為最為重要的社會(huì)傳播媒介之一,一直秉承著傳播時(shí)代精神的歷史使命。因?yàn)榻F(xiàn)代期刊具有新聞性、真實(shí)性、服務(wù)大眾性等根本屬性,“為時(shí)”、“為事”的特征更加明顯。可以說(shuō),期刊是一個(gè)時(shí)代的縮影,是最直接的社會(huì)記錄,是最貼近生活的微觀歷史,上至國(guó)家大政方針,下至百姓衣食住行,都可以在期刊中得到體現(xiàn)。《山西青年》1979年第11期雜志刊發(fā)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從能不能學(xué)習(xí)〈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一書談起》;1980年第1期又從《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一書選取一節(jié)《黨員個(gè)人利益無(wú)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予以發(fā)表;1980年第2期又發(fā)表了趙政民、楊新華撰寫的《劉少奇長(zhǎng)子之死》。因?yàn)槠椒丛┘馘e(cuò)案、劉少奇冤案能不能得到平反是全國(guó)上下普遍關(guān)心的問(wèn)題,引起廣泛共鳴。而這些文章的發(fā)表,也反映了黨和國(guó)家撥亂反正的信心與決心,有外媒據(jù)此發(fā)表了“中國(guó)將會(huì)為前國(guó)家主席平反”的消息(注1),果然,1980年2月下旬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huì)通過(guò)了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決定。
就期刊而言,期刊特色最為集中、辦刊理念最為鮮明的,當(dāng)屬創(chuàng)刊號(hào)無(wú)疑。創(chuàng)刊號(hào)是辦刊人展現(xiàn)給讀者的第一部作品,自然要有一個(gè)“自我介紹”,比如創(chuàng)辦期刊的時(shí)代背景、指導(dǎo)方針、辦刊宗旨、編輯理念、稿約等等,一般以《創(chuàng)刊詞》、《發(fā)刊詞》為表現(xiàn)形式,還有寫成《致讀者》、《寄語(yǔ)讀者》、《編者的話》等形式的,繁簡(jiǎn)不一。比如《讀者》創(chuàng)刊號(hào)上,只在《稿約》下發(fā)了一則不足150字的《告讀者》,其內(nèi)容可以看做是《稿約》的補(bǔ)充,而有的《創(chuàng)刊詞》則是宏篇巨制,寫滿了一個(gè)整版。正是因?yàn)閯?chuàng)刊號(hào)具有指導(dǎo)性、資料性等鮮明特點(diǎn),在考據(jù)刊物本身及考證史實(shí)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研究?jī)r(jià)值,所以又衍生了兩個(gè)重要屬性,收藏性與鑒賞性。
不僅如此,創(chuàng)刊號(hào)還具有較高的學(xué)術(shù)研究?jī)r(jià)值,這不僅反映在所刊文章的社會(huì)及歷史解讀上,就其本身而言,也可以作為認(rèn)識(shí)社會(huì)的鑰匙。每一種期刊的創(chuàng)辦都是時(shí)代的召喚,都自覺承載了時(shí)代的精神與需求,都蘊(yùn)含著創(chuàng)辦者的心血、眼光與規(guī)劃。1978年,我國(guó)期刊有930種,到1985年已接近5000種,1989年則超過(guò)6000種(注2),因而這一段時(shí)間產(chǎn)生的創(chuàng)刊號(hào)較多,說(shuō)明改革開放給社會(huì)帶來(lái)了空前活力,思想的裂變、觀念的迸發(fā),在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中需要期刊這種傳播媒介,但一段時(shí)間內(nèi)資產(chǎn)階級(jí)自由化思潮、地?cái)偽膶W(xué)的泛濫,某些期刊的低俗化傾向,都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再有就是,創(chuàng)刊號(hào)一定不會(huì)憑空產(chǎn)生,某一種期刊的創(chuàng)辦,意味著該領(lǐng)域或行業(yè)需要情感的表達(dá)或理論的梳理,比如說(shuō)上世紀(jì)80年代文學(xué)期刊的大量涌現(xiàn),與文革期間的思想禁錮,有志青年心有郁結(jié)是分不開的;就算是人文色彩較淡的科技類期刊,比如《養(yǎng)花》、《烹調(diào)知識(shí)》等期刊的創(chuàng)辦,也能說(shuō)明國(guó)民生活品味的提升;某類期刊的創(chuàng)辦,說(shuō)明這一領(lǐng)域已經(jīng)引起社會(huì)的廣泛關(guān)注,或?qū)?guó)計(jì)民生產(chǎn)生重要影響。筆者認(rèn)為,通過(guò)創(chuàng)刊號(hào)研究社會(huì)和歷史,是一個(gè)較好的途徑,它可以為社會(huì)學(xué)、歷史學(xué)提供鮮活的素材。
二、《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創(chuàng)辦
這里,我們不妨把眼光放遠(yuǎn)一些,通過(guò)《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來(lái)看一看創(chuàng)辦人是如何苦心孤詣地“經(jīng)營(yíng)”創(chuàng)刊號(hào),創(chuàng)刊號(hào)又是如何與時(shí)代精神連接的。《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的英文名稱是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若是直譯,似可譯為《中國(guó)月刊》。它的創(chuàng)辦,頗為曲折,也頗費(fèi)心機(jī)。
說(shuō)起來(lái),英國(guó)在發(fā)動(dòng)鴉片戰(zhàn)爭(zhēng)之前,也曾想過(guò)用“紳士”與“和平”的手段打開中國(guó)市場(chǎng),比如說(shuō)傳教、辦學(xué)、行醫(yī)和出版等方式進(jìn)行文化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滲透,但顯然,雙方是郢書燕說(shuō),英國(guó)說(shuō)是“發(fā)展貿(mào)易”,而清朝統(tǒng)治者堅(jiān)持認(rèn)為“夷人多事”。1810年,嘉慶皇帝發(fā)布諭旨:“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籍,或設(shè)立傳教機(jī)關(guān),希圖惑眾,及有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揚(yáng)其教,及改稱名字,擾亂治安者,應(yīng)嚴(yán)為防范,為首者立斬”(注3)。
在來(lái)華傳教士中,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最為聰明刻苦,也懂得權(quán)衡的人物之一。
他在傳教之時(shí),發(fā)現(xiàn)中國(guó)地域遼闊,習(xí)俗各異而方言眾多,但文字卻是統(tǒng)一的,加之中國(guó)人有敬畏文化的心理,用印刷品宣傳往往能取得較好的效果。于是,馬禮遜冒著殺頭的危險(xiǎn),出重金請(qǐng)來(lái)蔡高、梁發(fā)等人印刷《圣經(jīng)》和其他宣傳教義的小冊(cè)子,還編纂了《華英辭典》。1813年,英國(guó)倫敦布道會(huì)派威廉·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來(lái)協(xié)助馬禮遜傳教,次年被派往南洋群島華人聚居地。這期間,米憐產(chǎn)生了創(chuàng)辦“中文月刊”(注4)的想法,并得到了馬禮遜的同意。1815年,米憐在馬六甲設(shè)立英華書院和印刷所,8月5日,出版了《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中國(guó)歷史上第一份近代化報(bào)刊就這樣問(wèn)世了。這份創(chuàng)刊號(hào),筆者無(wú)緣親見,從記載來(lái)看,顯得頗有些單薄,只有5頁(yè),但我們卻能從中讀出許多信息。
三、創(chuàng)刊號(hào)里有乾坤
《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為宗教宣傳讀物,自然以“闡發(fā)基督教義為根本要?jiǎng)?wù)”,其辦刊人員也都是傳教士,但這一創(chuàng)刊號(hào)給人的強(qiáng)烈感覺卻是“附會(huì)儒學(xué)”。顯然,米憐等人有意將基督教義與孔孟甚至道家學(xué)說(shuō)相比附,封面右側(cè)拼湊了一句孔子的話:“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發(fā)刊詞(即《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序》,這里統(tǒng)稱發(fā)刊詞)的頭一句就是“無(wú)中生有者,乃神也。神乃一,自然而然,當(dāng)始神創(chuàng)造天地人萬(wàn)物,此乃根本之道理”,這段話,似乎更近于道家理論,而“無(wú)中生有”又是三十六計(jì)的一計(jì),顯然,這種行文是易于為中國(guó)人接受的。米憐曾坦率地說(shuō):“對(duì)于那些對(duì)我們的主旨尚不能很好地理解的人們,讓中國(guó)哲學(xué)家們出來(lái)講話,是會(huì)收到很好的效果的”(注5)。為了適合中國(guó)人的閱讀習(xí)慣,《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采用文言文,雕版印刷,豎排版,單魚尾,配木刻版畫,就像一本線裝書,比較適合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人的閱讀習(xí)慣。從紀(jì)年上看,用的也是中國(guó)紀(jì)年,而不是西歷紀(jì)年。
其次,出版地址的選擇上,也是有著諸多考量的。當(dāng)時(shí),外國(guó)人在中國(guó)尚無(wú)特權(quán),傳教也無(wú)從談起。馬禮遜和米憐都認(rèn)識(shí)到,想在大清帝國(guó)管轄范圍內(nèi)辦報(bào)辦刊,是根本不可能的。而馬六甲距離中國(guó)較近,聚居華人較多,往來(lái)密切,將中文報(bào)刊帶往中國(guó)也比較方便。創(chuàng)刊號(hào)《告貼》中稱:“凡屬呷地(指馬六甲)各方之唐人,愿讀察世俗之書者,請(qǐng)予每月初一二三等日打發(fā)來(lái)人到弟之寓所受之”,據(jù)稱,“通過(guò)朋友、通訊員、旅行者及航運(yùn)等”方式流傳的范圍,在中國(guó)有“九省”之廣。就是說(shuō),出版地址雖未選擇清帝國(guó)境內(nèi),但一定程度上達(dá)到了傳諸華人的初衷。
在讀者定位方面,米憐等人也做過(guò)認(rèn)真思考,表現(xiàn)出與古代“邸報(bào)”、“京報(bào)”不同的特質(zhì),在觀念上已開始考慮讀者的審美情趣和接受心理,顯示出面向大眾的取向。其發(fā)刊詞中稱:“看書者之中有各種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達(dá)、智昏皆有。隨人之能曉,隨教之以道。故察世俗書必載道理各等也。神理、人道、國(guó)俗、天文、地理、偶遇,都會(huì)有些。隨道之重遂傳之。最大是神理,其次是人道,又次國(guó)俗,是三樣多講,其途隨時(shí)順講。但人最悅彩色云,書所講道理要如彩云一般,方使眾位亦悅讀也。富貴者之得閑多,而志若于道,無(wú)事則平日可以勤讀書,乃富貴之人不多。貧窮與作工者多,而得閑少,志雖于道但讀不得多書,一次不過(guò)讀數(shù)條。因此察世俗書之每篇必不可長(zhǎng),也必不可難明白。”雖說(shuō)這篇發(fā)刊詞文白相雜,文理欠通,但在編輯思路、編輯方針與讀者定位等方面,都有精到的認(rèn)識(shí),值得研究與借鑒。
四、結(jié)論
近年來(lái),關(guān)注與收藏創(chuàng)刊號(hào)的人很多,然研究則不甚深入,專著也不多,多為圖冊(cè)等資料收集或隨筆一類普及讀物。這里,筆者以《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創(chuàng)刊號(hào)為例,談了一些創(chuàng)刊號(hào)收藏與鑒賞的認(rèn)識(shí)。筆者以為,創(chuàng)刊號(hào)足為期刊從業(yè)者津梁,亦可為觀察社會(huì)、研習(xí)歷史之窗口。這大概正是創(chuàng)刊號(hào)的迷人之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