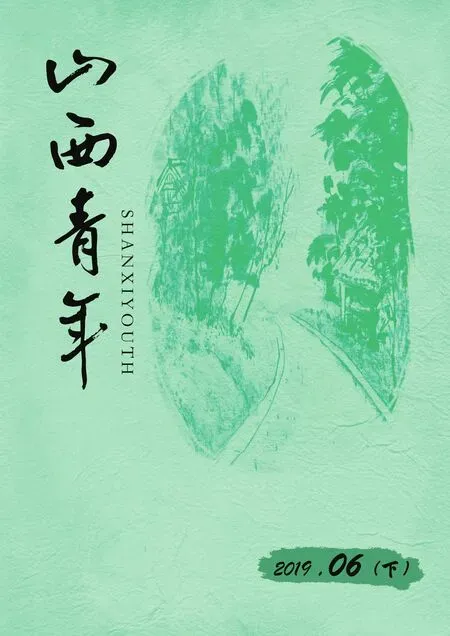論《杜詩詳注》中杜妻楊氏的形象
潘 越
(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9)
史料中我們能夠看到的關于楊氏的史料記載僅有兩則。《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1]與《云仙雜記》:“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妝飾。”[2]從這兩則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出楊氏出身書香門第,本是大家閨秀,嫁給杜甫后過著清貧的生活。遺憾的是其他史料中關于杜妻楊氏的信息少之又少,且其中許多史料尚存在爭議,這為我們解讀杜妻楊氏帶來了一定的難度。但從杜甫的詩集當中,我們不難窺探出詩人對自己妻子的愛。在那沉郁頓挫的筆調下,依舊有著兒女家長的細膩,二十余首的詩作,為我們展現了一位賢良、勤勞、飽經生活磨難的妻子形象。
一、飽經磨難,吃苦耐勞
亂世出詩歌,人間有情暖。杜甫多次以“老”、“瘦”稱妻,其中飽含著夫婦二人對生活艱難的獨特理解。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杜甫寫道:“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3]天寶十四年冬詩人由長安往奉先縣探望妻兒,杜甫在詩中以“老”形容妻子楊氏,可見楊氏在年僅33歲就已經吃了很多苦,飽受生活的磨難。在詩人的敘述當中,我們看到她長期獨自照顧家庭和年幼的兒女,無怨無悔地為詩人撐起半邊天。詩人在外尋求功名時,楊氏設法捎去書信慰藉“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丈夫兩手空空歸家時,也能夠面色如故待他如往常般好,“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
杜甫用平實的手法,沒有過多的拘泥于楊氏外形外貌的細致刻畫,反而只以簡單的老、瘦二字勾勒出楊氏那飽經生活磨難的人物形象。亂世能夠安家照顧子女,在磨難當中依舊不放棄生活的希望,吃苦耐勞,勤儉樸素。
二、掛念丈夫,思歸婦人
杜甫和楊氏對彼此的思念之情在《月夜》和《一百五日夜對月》中最能體現。詩歌寫作于被叛軍拘押長安期間,以兩個不同的角色角度敘述了對親人的思念和牽掛。“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詩人設想妻子月下獨望,把無形的思念化作了有情的淚水,相思無眠。短短幾句就勾勒出了一個美麗的思婦形象。[4]《一百五日夜對月》中借神話牛郎織女的傳說以及詩人的浪漫想象,傳達出有情人之間感情的真摯與高尚,在清新的文字中又暗含著離別的悲情與苦痛,道出了久別之后雙方都盼望團圓的愿望。至德二年八月,分別了一年多的杜甫和妻子終于團聚。詩作《羌村三首》便記錄了當時的情景,“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在兵荒馬亂的時代,人命危淺,命如草芥,楊氏甚至認定他不會生還了,丈夫忽然出現在眼前,這對于日夜思念的楊氏來說簡直不敢相信。由“驚定”到“拭淚”,這中間過程的轉換是真情的流露,是一個思婦形象最好的闡釋。
三、生活艱難,賢良慈母
在生活困苦時,身為母親的楊氏親眼看著幼子餓死,她難以抑制內心的悲痛,嚎啕大哭,“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發閬中》中記道“女病妻憂歸意速”其中“歸意速”可見出楊氏對女兒的慈愛,丈夫離家三月她都沒有因為家中的事打擾他。但女兒生病她便亂了分寸,連忙給丈夫寫了告急信,催其歸來。杜甫深知妻子對兒女的感情,在他看來“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遣興》),楊氏無愧為一個賢良慈母。在生活安穩時,杜甫“晝引老妻乘小艇,眼看稚子浴清江。”楊氏樂相伴,夫妻二人共乘一支小船,看著孩子們興高采烈地在清江中戲耍,共享天倫之樂。楊氏的賢良品質還體現在她比普通的女性更善于營造詩意的生活氛圍,會“畫紙為棋局”緩解生活的壓力。
四、結語
楊氏是一個名門之女,對貧病困苦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不離不棄,甚至用盡自己的能力支撐家庭、照顧兒女。詩人在詩中對妻子的描寫包含了感激、內疚、不安等種種復雜情感,他在詩中自嘲“笑為妻子累,甘與歲時遷”。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說:“中國言夫婦之情最好者,莫如處亂離之世如杜甫,處倫常之變如陸放翁等之所作。”[5]詩篇中我們看到了一位賢良、知書達理、飽經生活磨難的女性形象,她堅毅勤儉、熱愛生活,在任何時刻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杜甫的文學創作。我們可以推斷,杜甫之所以能夠在戰亂時代依舊能保持對文學的初心,和妻子楊氏的支持是分不開的。文學史上大多關注的是杜甫本人的創作,但是在其背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形象卻少有人知,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伴隨著新世紀女性主義的興起已經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男性詩人背后的成功因素。筆者認為杜妻楊氏身上具有中華民族傳統女性的可貴品質,這一類女性身上傳承著民族文化的精髓,理應得到更多的重視和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