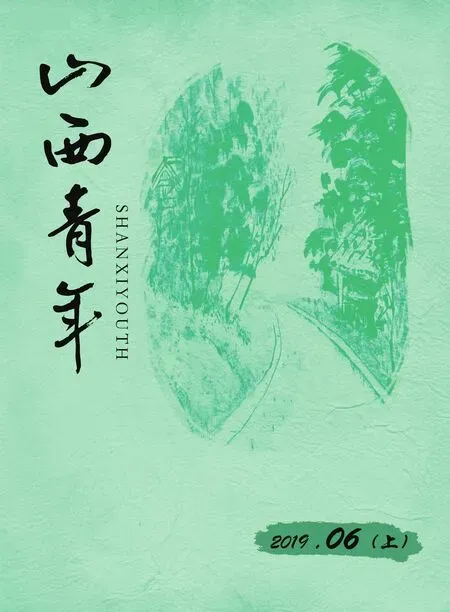建構與重塑:改革開放以來“單位人”的實踐回應*
陶 宇 初明寅
(長春工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系,吉林 長春 130000)
城市改革全面展開以來,東北地區國有企業在不同程度上都發生了改變。這些企業因為各自的調試有了不同的發展,“單位人”的生活史與命運也各不相同,走向差異化。本文立足具有“典型單位制”的東北老工業基地Y廠,以文獻法、觀察法、訪談法、口述歷史法等方法切入,形成“單位人”在此進程中的回應及啟示。
一、國有企業制度變遷的總體表現
國企改革過程中,體制的變革、市場化的轉型、產品的升級、管理思路的轉變,這些絕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實踐中摸索,進而去總結凝練出適應這一階段,并可以持續有效運行的單位發展模式。改革開放與國企改制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生產力,創造了一定的效率與收益。但對于形成并已然得到鞏固的單位制內部,這種改變是深刻的、長期的,也是需要面對一定的困境與挑戰的。
二、變遷中的“單位人”際遇與回應
對于任何一個單位,其改革的過程必然都要承受風險與代價,而這些改革的負重者當中,不同的單位有不同的問題,不同的“單位人”有不同的生活體現。這些變化與生活際遇的改變,也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影響其與家庭生活史的分水嶺,甚至蔓延到更漫長的歲月。
在這場劇烈而持久的變革中,大量“單位人”被清退回家。“‘40、50’現象是Y廠發展的敗筆,當時就是按年齡劃。我那時候,2000年,那就是劃杠劃的。當時我是干部,我剛才說的是工人劃‘40、50’回家。2000年,我們叫內退,內退在R廠也是沒有的。Y廠就是這樣,當時那段歷史,對很多人來說不堪回首。因為下崗,離婚的都有,還不是個別現象。下崗了,兩口子總干仗啊,女的說男的沒能耐,那別人沒下崗,你咋下崗了呢?男的又有點要面子,越干越生,離婚的都有。因為兩口子離婚,造成子女流浪社會,引起更嚴重的社會現象,也是有的。”(Y廠退休姜維口述)因此,無論是改制之后發展較好的Y廠還是其他各單位,幾乎都經歷了減員增效、下崗失業等改革過程,而每一位親身經歷的“單位人”,包括旁觀者也都深受影響。對于他們而言,從原本穩定的單位中離開,需要一個接受的過程。
相類似的,Y廠退休工人毛方曾經歷了單位發展的起起落落,可以說對于Y廠,對于單位有著極其深厚的情感,但在國企單位改革的條件下,還是主動退出,開始了新的生活:“退養,那都是自愿的,你可以自己尋思能干點別的啥,我退養以后賣了一年多手紙,也到舞廳當過服務員,去賣票收票,也當過門衛看守,做了很多工作。”(Y廠退休工人毛方口述)
可見,一方面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自由資源與自由空間不斷得到拓展;另一方面,單位內部的容量不斷縮小,關停并轉所帶來的是減員增效,產業升級相伴隨的是下崗失業。因此,“單位人”的主動的與非主動的流動,都是他們面對新形勢、新時代的一種實踐。
三、結語
在梳理有關“單位人”的回憶中,我們大致可以理出一個脈絡來:“有關國有企業單位形成時期的記憶是集體懷舊的,有關國企單位鞏固時期的記憶是集體反思的,而對于改革以來尤其是改制之后的集體記憶是多元的、差異的,甚至碎片化的、原子化的,是失落與困惑同時存在的。”在這個過程中,單位生活共同體也逐漸分化了:外圍到內部的變異顯現出來的是共同體分化的秩序。首先,單位外組織的萌生使單位密度產生松動,同時在單位之外也存在著可能性。再者,在國企改革中由單位所承擔的職能在不斷的弱化,原有的福利體系在不斷的瓦解和分化,子女接班、家屬照顧等政策也已經成為了一種歷史;大量的社會資源回歸到社會中去,職工福利也從全面逐漸的弱化。事業與企業、干部與職工的貧富差距也在不斷異質化的社會生活中逐漸的拉開。第三,從重視到淡化,從豐富到單一,已經演化為單純的經濟生產組織的單位文化式微。單位共同體最終由分立破產導致分裂,單位性質也從社會生活共同體向經濟利益組織轉化,相對應的,“單位人”的身份也逐漸在改變,工人們曾經光榮的集體意識也不斷的消解,其行動選擇的標準也從價值取向向利益取向轉變。
社會發展、體制轉型、國企改革,當為國家進步的必然之路,但在這種時代前行的潮流之中,每一位“單位人”也被帶入其中,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家人、他們家庭內部的關系、他們子女的未來等等一切都在這場變革中發生著微妙而真實的改變。未來單位何去何從,這關乎每位“單位人”的命運,也引發了“單位人”在不同角度的反思。改革是勢在必行的,但在東北地區,因產品、技術以及管理的不同,因此,改制過程中單位的回應也有所不同,這體現了單位制變遷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