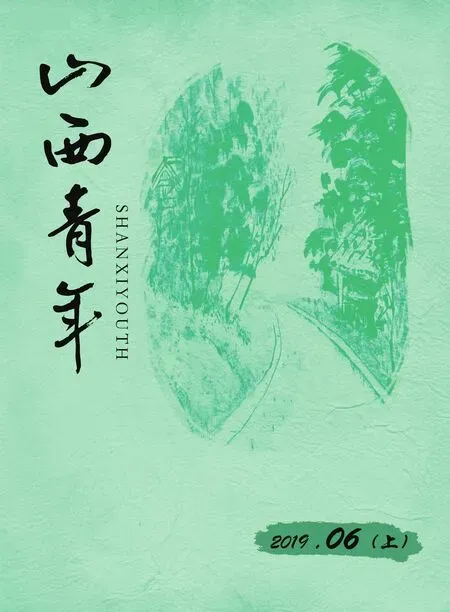淺談日本近世身份制度的瓦解
李亞南
(山西師范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0)
一、日本近世身份制度的建立及特征
日本近世身份制度的建立是通過豐臣秀吉在位時期頒布的兩個措施——檢地、刀狩得以實現的,中世后期及近世時代,領主對于農民的保有地所進行的測量調查,成為檢地。在豐臣時代,為了加強自身權力,實現對被統治者的有效控制,將社會上的各個階層加以區分,規定了兵役、農役人群的區分。從此,服兵役的武士這一群體遠離農村,被迫切斷和農村的經濟聯系,而只能居住于城下町,依靠領主發放的俸祿生活;第二點是刀狩令,規定只有武士可以佩戴武器,從而實現了其對于武力的壟斷,農民只能專司生產,不可染指武器,這樣通過檢地,刀狩基本上構架起了日本近世身份制度的框架;武士成為領取“祿米”的統治集團,農民成為在農村專司耕作的生產者集團,而町人成為溝通城市和農村的流通集團。
日本近世身份制度有以下特征:第一,日本近世身份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沒有一個法令去明確規定它的出臺實施,它是織豐時代——德川時代實施、完善的一系列法令不斷衍生的派生物;第二,近世身份制度是通過強有力的政治軍事強制實現的。檢地、刀狩這一系列政策實施的目的即使為了取消中間階層的特權,從而更好地加強領主權力;第三,近世身份制度實施客觀上導致了武士、領主、幕府優位的結果。在德川幕府時期,頒布的《武家諸法度》等通過服飾等方面的規定,來貫徹這一原則。
二、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近世日本社會結構的嬗變
在德川幕府時期,農業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隨后確立了年貢村請制,農民在繳納夠規定的貢物后,其余剩糧都歸自己所有。這樣,在利益的驅動下,農民采用更加精耕細作的方式去經營土地,來提高產糧出售余糧獲得更高的收入。這樣一種背景下,更多的農產品不是用于開展新的自給自足,而是流通于市場之中,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在這一過程中,農產品的商品化越來越強。在太宰春臺的《經濟錄》中這樣說道:“不以米谷布帛為寶而以金銀為寶”,這就說明日本近世商品化的經濟取代了駐藏式的小農經濟而居于主導地位,當商品經濟在社會中蔚然成風,社會結構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一)町人勢力崛起
這一時期,近世身份制度中,武力為了維持自己在城市中“有身份”的生活并且向領土交貢,他們的收入逐漸入不敷出,日益貧困化,不得不向經濟實力雄厚的町人求助。當然,町人不會因為武士作為統治集團無償向他們提供幫助,而是開展高利貸業務,以此來攫取更大的經濟利潤。這樣的話,町人的經濟實力的增強也引發了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的不斷上升。
(二)武士貧困化
第一、本是區分身份的制度卻成為了自身滅亡的重要因素。通過身份制度,武士取得了統治地位,與此同時,由于使武士聚居于城下町,切斷了他們和城市的經濟聯系,反而使在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武士被農村的經濟所支配,他們的生活收入全都依賴于此。
第二、武士們的旅宿境遇也是惡化了這一狀況。武士們居于城下町,但是需要參覲領主,往來路費昂貴,還要在江戶購邸,這樣的結果是武士們為其所累,耗其所資。
第三、讓武士們引以為傲的身份在另一方面“消費”著他們。在武士內部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制度,為了使身份尊榮,武士們必須在“格”方面大下功夫。在諸如服飾、建筑規格、飲食等方面表現于平民有別,如果不這樣,就很難匹配自己的地位。
(三)農民階層分化
農村中的農民雖普遍自給自足,但其中抗風險能力低的農民因為經受不起天災人禍,而把自己的土地典押出去。于是他們逐漸成為了佃農,大量農民成為佃農,使得土地集中于豪農手中,這樣就架空了武士對土地的支配;另一方面,國家實行增稅,就會引起農民反抗,使社會矛盾激化,逐漸使國家統治基礎瓦解。
三、商品經濟沖擊下近世日本身份制度的瓦解表現
在商品經濟沖擊下,身份制度瓦解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本居于“士農工商”之首的武士,此時他們的地位受到了來自町人、農民的挑戰,町人、農民都逐漸摒棄武士獨尊這一觀念,而更強調自己對于社會的貢獻。農民作為生產者,所有產品均需由其提供,并且他們勉勵工作,更是唾棄作為“寄生階層”武士;而町人,通過借貸建立起之于武士的優越感,也是強調他們的價值。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經濟力量的懸殊變化,引起了名分尊卑的變動。
第二,由于武士日益貧困,他們不惜以賣取身份來換取收入。而此時的下層人民為了滿足他們的精神訴求,二者一拍即合,這在身份制度的堅固墻壁上鑿下了重重的一擊,武士身份不再為其獨有,部分庶民階層也可以通過金錢來躋身上層階級。
第三,商品經濟的發展使更多的人力源源不斷地從事工商業,在農村出現脫農化現象,農民們向工商業領域涌入,使武士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瓦解。同時,貧困的武士迫于生計,也從事起了工商業。
總而言之,以政治強權建立起來的身份制度,妥協于商品經濟及市場經濟,逐步瓦解。之后,推動日本中下層的武士發動倒幕運動,推動日本明治維新改革,一步步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