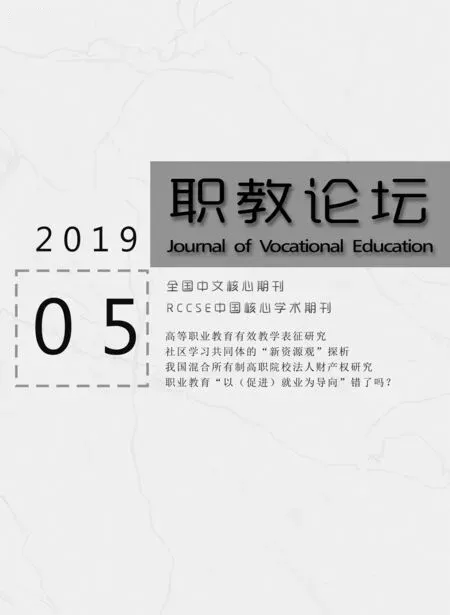高等職業教育有效教學表征研究
□林德山 申作蘭
教學是教育體系的中樞,始終在教育實踐中發揮著核心的作用。同所有勞動一樣,自有教學伊始,破除無效、低效教學,改進優化教學成為教育質量提高的必然選擇。“有效”成為教學評價的基礎指標和主要指標,各層次、各類型的教育都已經把“有效教學”納入研究與實踐的重要內容。 “目前,在國際教學理論研究領域,有效教學研究已經成為與建構主義教學理論研究、多元智力教學研究和反思性教學研究并列的四大國際教學熱點研究領域之一。”[1]隨著我國社會進入了新時代,“有效教學”研究也進入了新階段,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相關研究取得了諸多成果,職業教育領域研究還相對薄弱。高等職業教育作為我國教育中的一種類型,其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機遇和新挑戰,由于高職生源的復雜性,有效教學的研究對高職教育而言顯得尤為重要。
一、有效教學研究綜述
有效教學古已有之,“因材施教”可以認為是孔子開創的儒家學派的有效教學理念;17 世紀,夸美紐斯(Comenius)也提出了“班級授課制”等實現有效教學的手段。現代意義上的有效教學研究與實踐,普遍認為肇始于20 世紀初的美國,其產生的社會化背景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科學化運動”,代表人物是杜威(J.Dewey)、吉特(C.H.Judd)等人[2];另一方面是借鑒泰勒(F.Taylor)的“科學管理理論”追求生產效率實踐逐漸推廣的 “教學效能核定運動”,其主要關注點在學校效能和教師效能。
國外有效教學的研究按照時間線梳理基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20 世紀初至50年代,主要研究內容為教師效能方面,心理學視角較為普遍。如美國心理學家卡特爾(R.B.Cattell,1931)序化了好教師的品質,包括良好的個性與堅定的意志、智力、同理心與機智、思想開放和幽默[3]。這些研究認為教學效能主要取決于有效教師,所以應該培養教師的這些“有效”特質,但是相對忽視了教師在教學中的實際行為。第二階段為20 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針對上一階段的問題,國外學者轉向了有效教學自身及教師行為研究。這一階段涌現了一批影響重大的成果,如加涅(R.M.Gagne)在《教學設計原理》中提出的有效教學設計原理與技術,鮑里奇(G.D.Borich)的《有效教學方法》闡述了5 種有效教學的關鍵行為,布羅非(Jere Brophy)的《有效教學的基本原理》的12 條基本原理。 這一階段,相關研究量表和測量工具被開發應用,大量實證證明教學效果與教師教學行為呈現正相關。 第三階段為20世紀90年代到今天,教學環境、課堂氣氛、有效性標準、課堂組織方式等變量進入有效教學研究范疇,“有效教學”研究進入多元化階段。如斯圖爾特(Stewart,2005)等提出了幫助學生建立自信等有效課堂教學的6 條評價標準[4]。 基倫(Killen,2013)從教學組織方式角度提出了合作學習、角色扮演等9 種有效教學策略[5]。 總之,國外有效教學研究起步較早,研究經驗相對豐富,其成果與實踐對國內有效教學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范式借鑒意義,也為有效教學相關研究的“在地化”實踐提供了重要參考。
我國對“有效教學”的研究早期多從心理學角度出發,現在明確可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83年,邵瑞珍、皮連生、吳慶麟等人編著的《教育心理學——學與教的原理》在該年10月份出版,明確地提出“有意義的學習”“有效測驗”等概念與命題。2000年,陳厚德編著出版了國內首部“有效教學”專門性著述《基礎教育新概念:有效教學》,提出了有效教學的目的、觀念、基本要素和標準。陳曉端等(2017) 分析總結了1986-2016年我國有效教學研究30年的文獻,認為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三方面:教師視角、課改視角和學生視角[6]。一批碩博士論文對有效教學進行了專題研究,以博士論文為例有代表性的有姚利民的《有效教學研究》(2004)、孫亞玲的《課堂教學有效性標準研究》(2004)、何善良的《有效教學批判》(2007)、張紫屏的《課堂有效教學的師生互動行為研究》(2015)等。崔允漷(2009)、余文森(2009)、高慎英(2011)、陳大偉(2018)、張家軍(2018)等學者先后出版了有效教學的研究著作。國內對有效教學研究的同時,也對有效教學進行了反思,“有效教學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內涵知識化和窄化、教學活動模式化和機械化的傾向。”[7]田山俊、汪明(2016)認為有效教學不一定是“好教學”,提出“有效性是衡量好教學必不可少之維度, 卻不是首要維度,更不是唯一維度。 ”[8]肖慶華從倫理學角度對有效教學進行反思,認為“或因倫理缺失,或因倫理缺陷,有效教學易異化為知識主義教學、灌輸主義教學和技術主義教學這三種形態。”[9]高職教育的有效教學研究起步更晚,檢索中國知網和維普期刊網,以“高職”“有效教學”為主題或關鍵詞檢索文獻共493 篇,從2001年開始至2006年共3 篇,主要成果集中在2010年之后,研究內容以具體課程有效教學為主,過分突出了“結果有效”的“對策、策略”。
“由于教學是過程性存在,學生的發展只能在教學過程中實現,而且教學過程比教學結果更具價值,因此研究有效教學,更應該以過程作為切入點。 ”[10]在有效教學研究與實踐中,應該重視基礎性的“本體論”研究,首先需要明晰有效教學的表征系統。借鑒知識表征的分類,高職教育有效教學表征可以分為個體認識論下的整體性表征和社會認識論下的過程性表征。
二、個體認識論下的高職教育有效教學整體性表征
教學是在特定時空中的系統性活動,“是一個涵蓋矢量系統、理念系統、定位系統、條件系統、運行系統和輸出系統的動態結構體系。 ”[11]在高職教育中,教學準備、教學投入、教學實施、教學產出、教學拓展、教學評價等多個環節的“有效”“高效”或“無效”“低效”都是教學的表征,這些表征都強調了整體認知。 “表征是指可以指代某種東西的符號或信號,即某一事物缺席時,它代表該事物。 ”[12]個體認識論有效教學表征主要是指有效教學在個體心理的概念、符號或者標記等反映和存在方式。 根據高等職業教育的特性,其有效教學整體性表征體現在效用、效果、效率和效能等4 個維度(見圖1)。
(一)高職教育有效教學的效用
“有效教學”在高等職業教育領域首先強調的是效用,這也符合“有效”從生產領域引入教育領域的本意。 效用是經濟學常用術語,主要用來度量需求得到滿足程度,其關涉到資源配置。 高等職業教育的辦學方向是 “面向市場”“服務發展”“促進就業”,關鍵詞是“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這就決定了高職教育辦學要“有效用”,所以教學不僅僅要滿足校內需求,還要更加緊密地滿足市場、就業需求。高等職業教育教學效用最終衡量是體現在培養“具有專業技能與工匠精神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
教學有效用還體現在既實現了教學設計又完成了教學目標,更重要的是就業能力提升和服務貢獻提高。 效用是一種價值判斷,教學效用高低體現了教學價值的實現程度, 由于教學自身的復雜性,即使教學環節完成,也不意味有效用,更不能衡量是否“有效”,不能判斷教學價值大小。 從產教融合角度,高職教育中效用就是效益,教學效益是教學行為及結果與高職教育發展目標和社會發展需求是否契合、契合程度如何。“教學效益強調的是教學及其結果的合目的性、合價值性。 ”[13]教學效益從關聯程度可以分為直接教學效益和間接教學效益,直接教學效益主要是指高職教育教學效果,間接教學效益是指高職院校、專業的社會評價;從表現層面可以分為社會效益、集體效益和個人效益,社會效益主要是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及行業企業對其評價,集體效益主要是指高職院校組織及社會對其評價,個人效益既包括學生個人的成長也包括教師(團隊)的提高。
(二)高職教育有效教學的效果
高等職業教育有效教學的第一表征從整體層面而言是“效用”,從教學自身而言重要表征是“效果”。不論何種教育,有教學行為,必然有教學效果。教學效果是教學活動影響下所呈現的教學結果,教學效果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負向的。其與“有效”并無直接關聯,“有效果” 也僅僅是評價教學是否“有效”的一個維度,所以“效果”不能成為教學有效性的首要表征。 高等職業教育中,理論課教學相對效果不夠理想,教師感受成就感較低,抱怨是無效勞動,蘇霍姆林斯基(Suchomlinsky)也曾明確提出:“無效的勞動是每個教師和學生都面臨的最大的潛在危險。”[14]傳統研究上把“有效果”作為有效教學評價的首要因素,在高職教育中看似也是針對性很強的,實際上是不夠科學至少是不全面的。
高等職業教育實踐中, 教學無效果是不存在的,有效果、低效果和負效果才是存在形式,所以需要對教學效果的定義重新界定。 首先,教學效果的評價落腳點在學生的進步和社會評價認可。在高等職業教育中,教學有沒有效果是指學生的素質與技能有沒有提高,教學有沒有效果是指社會對學生的素質與技能認不認可或接不接受,不是指教師的教學行為如何。 其次,教學效果只強調教學行為產出的結果,所以也只以結果評價。 教學效果不關注教學設計、教學環節乃至教學動機,即使它們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聯系。最后,教學效果關注效果有無、大小,不關注有效教學的投入產出比例,甚至有效教學的真偽。高職教育有效果的教學是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教學,是讓學生素質提升、技能提高、能力增強、知識增長、社會認可的教學。
(三)高職教育有效教學的效率
有效教學重效用,必然要講效率。 在高職教育教學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效率是資源配置的關鍵指標,教學效率可以簡單地理解為教學投入與教學產出的比例。 早在20 世紀70年代,蘇聯教育學家巴班斯基(Babansky)就提出了包括“整體最優”“局部最優”的教學過程最優化理論,其以教學效果和時間消耗為衡量標準。從經濟學、管理學角度而言,效率一般越高越好,這是以保證效果為前提的。 教學有效率的提出是教學投入低、教學產出高要求的產物,雖然教育不能產業化類比,但這種“功利化”要求恰恰有助于緩解高職教育投入少的困難,也符合夸美紐斯(Comenius)寫作《大教學論》的目的“尋找并找到一種教學的方法,使教員可以因此少教,但是學生可以多學。 ”[15]
高等職業教育“有效教學”講效率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尤其是在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構建的背景下。 高職教育強調教育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結合緊密, 必然呼應行業企業“效率第一”等文化表征,這也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現代學徒制試點的客觀要求。 大教學投入、高教學投入、多教學投入只能收獲小教學產出、低教學產出、少教學產出,在高職教育領域這稱不上“有效教學”。 同時,有效率并不一定代表有效果,因為教學效率既體現在教學效果上, 也直接體現在教學組織、教學環節中,還體現在教學效能、教學效應上。
(四)高職教育有效教學的效能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個體對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是否有能力完成某個行為的主觀判斷和覺知,以及對實現有效教學能力的客觀表征。 ”[16]教學效用、教學效果、教學效率都是衡量教學效能的依據。 教學效能的“有效性”評價貫穿于教學組織前中后和教學全部環節,也是衡量教學結果的尺度。“教學組織對教學目標的體現程度越高,教學輸出的結果就越接近理想程度,課堂教學的效能就越好。 ”[17]高職教育領域,教學效能主要指教師教學效能,它與教學手段與目的的正確性和教學效果的有利性相關。
在高職教育這個具體的語境之中,頂崗實習等教學環節、現代教育技術等教學手段,是完全符合高等職業教育教學目標的,當這些教學環節、教學手段與教學目標越趨于一致的時候,教學有效就更為凸顯,在這個意義上教學效能越強。 高等職業教育辦學方向是“服務發展、促進就業”,教學效能反映的是高職教學行為所取得的效用和效果的現實性與潛在性, 即教學效用的大小和教學效果的強弱,提高教學效能需要教學理念、教學設計、教學組織和教學運行的保障。 高職教育中,教學效能越大教學越可能真正“有效”,教師教學手段與目的越正確,產生的教學效果(學生發展)越好,教學的有效性越突出。 如果說教學效果是突出了學生主體,那么教學效能則反映了教師能動性和行為自主性,所以效能就成為高職教育教學有效的必然表征。
三、社會認識論下的高職教育有效教學過程性表征
高等職業教育有效教學個體認識論表征強調“結果有效”,這忽略了環境維度和過程有效,所以有效教學研究應該引入情境、具身等變量。 這是有效教育在新時代社會化發展的需求,也是高職教育“服務發展、促進就業”的必然要求。 教學不是在真空之下進行的, 高職教育更不是可以閉門造車的,社會認識論下的有效教學表征研究應該受到重視。“知識表征的社會性是在個體知識表征的基礎上融入外在的影響因素,體現為一種更加完整的認識論框架,它不僅注重主體性要素,也必然包含社會環境、文化背景要素。 ”[18]
社會認識論下的高職教育有效教學表征包括教學效用與學生發展的有機耦合、社會評價與教學診斷的有機統一、教學條件創設與教學過程正當的關聯行為一致。
(一)教學效用與學生發展的有機耦合
效用是高職教育有效教學的第一表征,有效教學行為就是追求“有效用”的教學行為,這種高效用是以效率指標為制約、效能指標為衡量的,最終是以學生發展為落腳點的。學生發展在高等職業教育教學中分為兩個層面: 一是校內層面的教學行為,一是社會層面的就業及發展能力。這是高職教育辦學方向和培育目標所決定的,也是高等職業教育有效教學的鮮明特色。 “以學生發展為本”“以學生發展為中心” 被認為是高職教育有效教學的核心理念,這種發展是針對高職生特質的也應該是符合行業企業需求的。高職教育有效教學要求教學效用與學生發展的有機耦合,教學效用是學生發展的必然追求,學生發展是教學效用的核心評價指標,有效教學必須是保障和促進學生發展的教學行為。
(二)社會評價與教學診斷的互動統一
評價標準是有效教學研究與實踐的核心問題之一,高職教育有效教學評價也面臨信度與效度的評價標準問題,評價當然不是目的,應用評價改進教學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作為一種社會評價,《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作為高職教育質量的重要評價參考,引入了“發展環境、國際影響力和服務貢獻力”等評價指標,再次證明高職教育有效教學表征需要社會認識論范式指導,在進一步“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旗幟之下,高職教育有效教學的社會評價逐漸與教學診斷互動統一。教學行為是教師依法自覺的職業活動,但有效教學“有效果”追求是以學生發展為依據的,這就要求教師應該進行自我判斷,自上而下的教學診斷與改進要求也是以“需求導向”為方針的,這種診斷為保證信度要求是多元化的,但要求院校“自我保證”,也就是首先要求教師自我診斷,要求更加重視社會評價來改進教學。 因而,高職教育有效教學表征包括社會評價與教學診斷的互動統一行為。
(三)教學條件創設與教學過程正當的關聯行為一致
高職教育教學目標中突出實踐能力的培養,這是高職教育培養“技術技能人才”定位決定的,“高職院校有效教學是基于實踐的教學”[19]。 高職教育有效教學實踐能力的培養,需要教學條件創設的保證,教學條件包含設施設備等硬件條件、仿真模擬等軟件條件和文化氛圍等環境條件。教學條件是有效教學的前提條件,有效教學在高職教育中能不能發生在外在上取決于教學條件創設的如何。教學面向具體的高職學生,這些學生既是整體的更是個體的, 教師根據教學實際創設針對性的教學情境,使用恰當的教學手段,這是教學標準與教師教學藝術的統一。 高職教育教學是一種過程性存在,教學過程是師生共同投入的價值活動,“教學活動具有內在的、自足的價值。 ”[20]學生發展與教學效用的實現是通過教學過程實現的,所以教學過程首先應該體現公平性,這正是教學過程正當的倫理訴求,也是高職教育“工匠精神”培養的基礎要求。高職教育教學過程應當要求教學既重視學生群體也要重視學生個體,應該強化過程性評價,改進教學過程與學習過程。
高職教育作為我國教育的一種類型,兼具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特性,其有效教學表征研究需要從整體性和過程性角度進行整合研究,明確效用為其第一表征。 高職教育是面向市場的教育,始終強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所以應該在個體認識論表征的基礎上,同時重視社會認識論表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