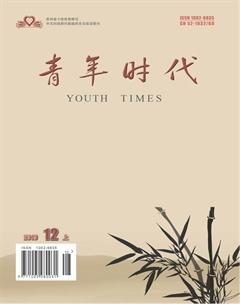明道“人性論”考察
孫瑤茹
摘 要:程顥繼承孟子性善論,在《生之謂性》篇中將本體論引入人性論,對儒家人性論問題進行了升華,為人性善惡找到了理論支撐。對程顥《生之謂性》篇進行探索,是理解二程人性論,理解宋明理學人性論問題的關鍵。
關鍵詞:生之謂性;明道;人性論;氣
一、引言
儒家對人性的討論,發端于先秦,以孟子“性善論”,荀子“性惡論”以及告子“性不善不惡論”最具代表性。孟子認為“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鑠也”,人的本性是善的,并且這個善源于人本身,性善天生,不可改變。與孟子對立,荀子立足于自然,提出“人性本惡”。他認為,爭名逐利是人類之必然,是印在人骨血里的本能。跟二者都不同的告子則認為“性無善,無不善也。”決定人性善惡的因素更多的是后天的學習與熏陶。先秦哲學家們雖爭鳴不斷,但他們僅提出人性的善惡問題,并未明確善惡的來源問題,理論大廈的根基十分不穩。隨后,宋明理學以解決這一問題為核心,進行了完善。理學家們以孟子性善論為基礎,將性與天、道聯系起來,為人性尋找到“理”這個基礎,逐漸構建起一套人性論體系,對之前人性來源問題進行了完善與補充,使儒家的思想體系趨于完整。
在整個宋明理學思想史上,程顥和程頤兩兄弟的地位是比較特殊的,他們二人的人性論可以說是對儒家“天道”本體論的延伸,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將本體論引入人性論,賦予了人性的本體論依據,可以說是為宋明理學人性論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將本體論和人性論相聯結,通過這樣的方法達成“天人合一”,也進一步鞏固了天人相聯關系的根基。故對二程人性論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程顥的《生之謂性》篇為二程論述人性的一個典型,所以本文以《生之謂性》篇為主,對程顥人性論進行考察與研究,也以此來透視二程對于人性問題的闡釋。
二、性即氣
明道在《生之謂性》篇對人性論的討論分為3個層次,在第一個層次中他對氣與性的關系做出了講解,對二者的關系進行了進一步解釋。“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程顥繼承了告子“生之謂性”的觀點,認為人之性是生來就有的,是跟天相聯系的。“即”在此不做相等解釋,不是說氣就是性,性就是氣,它意在說明氣和性地位的等同性。牟宗三先生在其著作《心體與性體》中強調道:“此不是‘體用圓融,乃只是性氣滾在一起之意,說粗一點,是性氣混雜、夾雜在一起,因而不相離也。”這是將氣與性放到了一個位置上來,認為氣和性一樣都是人生而就有的,氣質之性是人性的另外一種表現。在程顥看來,須得將氣、性并列,“論氣,不論性,不備;論性,不論氣,不明。”這是繼承了張載氣化論的觀點,并以此為基礎進行延伸。氣化論認為,萬物包括人類在內,都是氣化產生的結果,人性中含有氣質之性,明道在繼承這一觀點上進行了更加深入地討論。“氣即性,性即氣”之氣是宇宙大化之氣但又不完全是宇宙大化流行之氣。人在形成發展的過程中缺少不了氣的存在,對于個體所具有的性而言,如果離開了“氣”,就失去組成個體的重要部分,個體之性就不甚完整,同時,個人“氣稟”的不同所表現出來的氣質之性也存在差異,這種差異造成了之后所說的氣質之性的善惡問題。需要注意的是,程顥所說的這種氣性關系是局限于“生之謂性”情況下的,即個體生命完成之時,如果要深入追究個體生命完成之前的氣性關系狀況,則是另外一種情況。
氣性關系之后,明道又強調“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在他看來,理學家們所討論的人性已經不是純粹的人性本身。“人生而靜”源自《樂記》,由于《樂記》早已失傳,故原意是怎么樣的不甚清晰,沒有一個可靠的證據來證明它講的就是儒家所說的人之心性,程顥在此借用,將真正的人性化作“人生而靜”以上,是將人性化做了不可說,不能說的領域,目的在于明確人性的不能討論性。然而這與所謂不可知論是不一樣的,在他看來,人類目前以所具有的知識與語言,只是暫時無法對真正的人性做出一個準確描述。人們包括先賢們所探討所爭論的人性,實際上都沒有涉及本來之性,都是“生之謂性”,是個體生命完成出現之時所具有的性。對于這個性之善惡的討論不觸及本來之性,并且筆者認為根據后文“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一句能夠發現,程顥其實是認為本來之性是不會改變的,永恒的善性,根本沒有再討論的必要。
三、性之善惡
個體秉有的“氣稟”數量不同,質量不一,表現出來的性之善惡便有所差別。明道《生之謂性》篇論性的第二個層次便是性之善惡問題。“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天命之性純善不惡,是固定的,所以,在此所討論的性之善惡問題都不涉及本原之性。“理有善惡”之“理”跟宋明理學中核心的具有本原意義的“理”不同,作為本體論體系的理是世界的總括,是一切價值上溯的源頭,也是支撐道德修養的基礎,而這里所說的“理”與天理之理不在一個層次。這個“理”是理應,應當之意,不含有本體的意義。善與惡不是性中原來就有的,性理應只有善一個屬性,這里說到的“性”是生之謂性,后文“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之性也同樣是生之謂性之性。善是人性,那么與其相對的惡也是人道德品質的屬性,善與惡是生之謂性的兩面。正如后文明道以水比喻人性“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這一句是受到《易傳》的啟發。《易傳·系辭上》有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產生天地萬物作為本源之道都是由一對相對的元素構成,受到根源的決定,世間萬物都應相對出現,有清必有濁,有善則必有惡,那么也就不難解釋性之善惡的存在問題。
人性的二重性是宋明理學人性論所圍繞的核心,二程與前人不同的觀點在于直接從本體論角度進行闡釋,相比二程從本體論出發論性,并明確天命之性不必討論,張載從自然角度入手,從氣化角度談性,和伊川、明道有些不同。在宋明理學史上,張載首次提出氣質之性的概念,將它與天命之性并提作為人性論的一部分。他認為人性具有二重性,一是天地之性,一是氣質之性,不同于二程在生形之后論性,他認為天地之性是形而前的,氣質之性是形而后的,對性體和氣稟之性皆做出了討論。天地之性純善無惡,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氣質之性的善惡全然來自于人生而秉有氣之清濁。氣清為善,氣濁則為惡。在張載這里,雖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都同時存在于人,自人降生開始就擁有,但是二者的地位卻有著根本差別。天地之性不可改,它與天相聯系,是永善的,后天的熏習教養無法改變,它永遠作為人性的基底存在。但氣質之性不同,氣的質量清純,就不會遮蔽人本有的善,氣質之性就能夠達到與天地之性的同一。氣的質量復雜,雜質較多,就會對人本有的善進行遮蔽,對善的基底進行掩蓋,所表現出來的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就會截然相反。并且在張載看來,天地之性是人之所必有的,必然地存在于每一個人性中,但是氣質之性卻沒有這一必然性。“形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蒙·誠明篇》)在張載看來,通常情況下氣質之性是惡的,作為道德修養完滿的君子沒有氣質之性,只有純善無惡的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可以說是區分圣賢和普通人的一個標準,是普通人進行道德修養的內容和落腳點,想要成為一個道德完滿的人就必須擺脫氣質之惡性。在氣質之性善惡的來源問題上,明道的回答給予了它本體論的支撐,而在最終所表現出來的氣質之性的善惡由誰決定的問題上,明道繼承了張載的觀點。性有善惡,最終人性表現出來的屬性是由氣決定。人自落地起就與氣產生著不能割裂的關系,澄清之氣會表現出氣質之善性,污濁之氣則會顯示出氣質之惡性。在明確人性的善惡問題之后,惡性存在,那么人性論最后必然會指向修養問題,面對如何進行修養的問題,明道給出了“澄治之功”的修養方法。
四、澄治之功
道德修養問題是程顥人性論最后一個層次,也是《生之謂性》篇全文最為獨特的地方。“夫所謂‘繼之者善也,順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故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首先,明道給出了“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的原因,他用“水流”作喻,對善惡的形成又做了一番解釋。生之謂性如水流,不被濁氣所污染,直接顯現出本性之善就如同水流順應自然,沒有外力干涉的順流而下。正因不被外力干涉,所以它完好地繼承保存著本來性之善,此時,本來性之善沒有完全地被表現出來,至清之水不需過濾,本來善性也不需進行澄治。當水流受到外力擾亂,或是自身有些不足之處以致在流動過程中變得污濁時,人之性就會表現出不善或惡,澄治之功就變得必要。明道雖以清水濁水喻人之善性惡性,但是道德修養的澄治之功和過濾水流是不甚等同的。“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
進行澄治之功時,所用力氣的大小和變得清澈的時間是成正比的,但無論怎樣將濁水變得清澈,最終顯現的成果就是順流而下之水,從根源上而言,并不是和最初的善之清水有所不同的另一種水;對濁水進行“去濁”的過程,也不是普通的過濾,將污濁之物從水中取出。澄治污水卻不取出令水變得污濁之物,按常識來說這種方法是不可能令濁水變清的。然而,明道提出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方法本意是說明在對氣質之惡性做澄治之功時,一定要注意氣性之間的關系。
明道人性論第一個層次講氣性關系為“氣即性,性即氣”,并且在二程看來氣、性需并論。氣、性不離不雜,那么氣質之性中的惡性和讓性實現為惡之濁氣也不離不雜,如濁水中之污濁之物,若是將污濁之物從水中取出,這水便會產生質變化,就算澄清也不是“元初水”,不是元初水自然也就沒有作為清水的意義。明道言之,目的就在于強調氣、性不可分割的關系。
五、結語
程顥《生之謂性》篇分3個層次講人性,第一層次,他對氣性關系做出新的解讀;第二層次,對生之謂性和天命之性做出區分;第三層次,以水流作喻,提出“澄治之功”的道德修養方法。他繼承張載,繼承《易傳》的相關思想,將人性論拔高到本體論,構建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源頭。在氣性關系上,他繼承張載氣化論的基礎,進一步明確氣性不離不雜的關系;明確人性論所討論的層次問題,明道認為真正純粹的人性不容說,一切的人性論都是對生形之后的人性進行的討論;水流而下為天命之善性,清水為生之善性,濁水為惡,然雖水有清濁之分,但皆為生之謂性,澄治后的水是對元初水的一種回歸,并不是另起爐灶,澄治之功是氣質之惡性對天命之善性的一種歸復。明確這3個層次,就能夠對明道《生之謂性》篇進行把握,對二程的人性論進行把握。
參考文獻:
[1]王弼著.中華國學文庫·周易注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3.
[2]程顥,程頤.二程遺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牟宗三.心體與性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張麗華.宋明理學中“氣質之性”的考察[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7).
[6]張錦波.氣質以言性:朱熹“氣質之性”概念的哲學分析[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