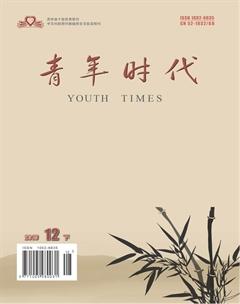俄國(guó)君權(quán)與神權(quán)關(guān)系發(fā)展演變探究
張卓群
摘 要:自988年羅斯受洗以來(lái),東正教成為羅斯的官方宗教,滲透進(jìn)俄國(guó)社會(huì)的各個(gè)方面。與其他歐洲基督教國(guó)家相同,宗教神權(quán)在俄國(guó)與君權(quán)也產(chǎn)生了權(quán)力斗爭(zhēng),二者之間此消彼長(zhǎng),最終教權(quán)衰落。而俄國(guó)深受拜占庭文化影響,其君主權(quán)力、宗教體系又與西歐天主教國(guó)家有所不同。
關(guān)鍵詞:俄國(guó);東正教;君權(quán);神權(quán)
一、基輔羅斯時(shí)期
(一)基輔羅斯國(guó)家的誕生
俄羅斯國(guó)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基輔羅斯的建立。基輔羅斯是瓦良格人在斯拉夫人世代生存的土地上所建立的國(guó)家,但基輔羅斯是一個(gè)各王公領(lǐng)地的松散聯(lián)合,大公國(guó)缺乏一個(gè)真正能夠令行禁止的最高統(tǒng)治者,各王公在各自領(lǐng)地的權(quán)力也受到各種制約。“因此,在11世紀(jì)之前,一人專政是政治上的偶然現(xiàn)象,并不是政治制度。”基輔羅斯在11-12世紀(jì)因下層階級(jí)地位低下、王公內(nèi)訌、波洛伏齊人入侵等原因走向衰落,一部分羅斯人向東北羅斯遷徙并定居,在這一地區(qū)誕生的各新興公國(guó)形成了現(xiàn)代羅斯國(guó)家的雛形。
(二)羅斯受洗
東斯拉夫人最初是多神教的信奉者,但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生產(chǎn)力水平的發(fā)展,多神教野蠻落后的習(xí)俗已經(jīng)不適應(yīng)社會(huì)需求。相反,東正教君權(quán)神授的觀念更有助于維護(hù)階級(jí)秩序、鞏固統(tǒng)治——“為了維護(hù)現(xiàn)存秩序,統(tǒng)治階級(jí)需要向人民的頭腦中灌輸現(xiàn)存制度合理的思想,讓他們回避斗爭(zhēng),憑借超自然的上帝的懲罰來(lái)威脅人民”。外加羅斯與拜占庭經(jīng)濟(jì)交往密切,深受拜占庭文化影響,因此接受東正教成為了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988年弗拉基米爾大公脅迫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二世,迎娶拜占庭公主并皈依東正教,這一事件宣告羅斯成為基督教國(guó)家,東正教成為羅斯的官方宗教。
羅斯受洗后不久,1054年基督教?hào)|西教會(huì)徹底分裂,東方教會(huì)強(qiáng)調(diào)正統(tǒng)性,俄國(guó)東正教受其影響,具有如下幾個(gè)特點(diǎn):“堅(jiān)持一成不變的教義正統(tǒng)性、濃厚的苦修主義和神秘主義、圣物崇拜以及教權(quán)依附于皇權(quán)。”其中教權(quán)依附于皇權(quán)是東正教俄國(guó)區(qū)別于西歐天主教國(guó)家的重要標(biāo)志,“教會(huì)與國(guó)家的關(guān)系是一種相互結(jié)合的關(guān)系,皇帝是教會(huì)的最高領(lǐng)導(dǎo),同時(shí)集‘皇帝與‘教皇之權(quán)于一身。但是,皇權(quán)高于教權(quán),皇權(quán)控制教權(quán)。”期間教會(huì)勢(shì)力雖有過(guò)增強(qiáng),但終究未能蓋過(guò)君權(quán),直至最終成為國(guó)家下屬機(jī)關(guān)。
基輔羅斯時(shí)期,東正教會(huì)為基輔大公授予稱號(hào),并要求東正教徒忠于基輔大公。這一時(shí)期君權(quán)與教權(quán)之間相互利用、相互支撐。王公們繼位和互相締結(jié)協(xié)議時(shí)主教會(huì)出席作為見證者,而王公則掌握當(dāng)?shù)刂鹘倘蚊鼨?quán)。相較于西歐君主與羅馬教宗對(duì)主教敘任權(quán)力的激烈爭(zhēng)奪,東正教王公自始便擁有自由授任主教的權(quán)力,這是他們能夠不受教權(quán)壓迫的重要政治基礎(chǔ)。
二、金帳汗國(guó)與莫斯科公國(guó)時(shí)期
(一)金帳汗國(guó)統(tǒng)治對(duì)俄國(guó)政治體制的影響
金帳汗國(guó)的入侵給羅斯帶來(lái)了深重災(zāi)難的同時(shí),也對(duì)羅斯各公國(guó)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尤其是其統(tǒng)治深刻地改變了東北羅斯的社會(huì)制度。一方面金帳汗國(guó)的長(zhǎng)期統(tǒng)治使本就落后于其他歐洲國(guó)家的羅斯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更加落后并且長(zhǎng)期停滯不前;另一方面金帳汗國(guó)的統(tǒng)治很大程度上切斷了羅斯與拜占庭間的聯(lián)系,使羅斯在西方封建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了東方的專制主義制度。“蒙古人給羅斯帶來(lái)了東方的驛站制度、戶口制度、賦稅制度、軍事制度和行政組織。羅斯社會(huì)原先的附庸親兵關(guān)系被蒙古社會(huì)的臣民關(guān)系代替。”雖然莫斯科公國(guó)興起并領(lǐng)導(dǎo)羅斯人民擊敗金帳汗國(guó),結(jié)束了蒙古人對(duì)羅斯土地長(zhǎng)達(dá)二百余年的統(tǒng)治,但蒙古的一系列制度依舊在莫斯科公國(guó)的政治體制中發(fā)揮作用,“羅斯人終于推翻了蒙古金帳汗國(guó)的的統(tǒng)治,但是‘八思哈制長(zhǎng)達(dá)二百余年的統(tǒng)治卻為俄羅斯國(guó)家政治制度的發(fā)展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以軍事獨(dú)裁為核心的‘八思哈制在客觀上加速了俄羅斯專制制度的形成過(guò)程。”
推翻金帳汗國(guó)統(tǒng)治后,莫斯科公國(guó)的歷任統(tǒng)治者在加強(qiáng)專制制度和建立中央集權(quán)國(guó)家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動(dòng)作用。伊凡三世時(shí)期可以視為俄羅斯專制制度初步形成的時(shí)期,他宣布君權(quán)神授,君主權(quán)力不受制約;他建立了一套中央行政機(jī)構(gòu),設(shè)立衙門;建立常備軍并于1477年摧毀了諾夫哥羅德,使專制制度在全羅斯的推行暢通無(wú)阻。伊凡四世大大加強(qiáng)了專制主義,1565年推行特轄制,嚴(yán)重打擊了封建領(lǐng)主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設(shè)立特轄軍,消滅反對(duì)沙皇的敵對(duì)貴族,通過(guò)暴力手段鞏固了沙皇專制。伊凡四世時(shí)期可以視作專制制度基本形成的時(shí)期,因?yàn)檫@一時(shí)期構(gòu)成這一制度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備:“君權(quán)神授的政治觀念、不受任何限制的君主權(quán)力、絕對(duì)服從的社會(huì)意識(shí)和高度集中的管理體系。”
(二)東正教會(huì)對(duì)民族獨(dú)立的影響
金帳汗國(guó)統(tǒng)治時(shí)期,由于蒙古人沒(méi)有建立有效的直接統(tǒng)治,為穩(wěn)固統(tǒng)治秩序,蒙古人優(yōu)待東正教會(huì),對(duì)神職人員格外優(yōu)待并免除教會(huì)的賦稅。因此,在金帳汗國(guó)統(tǒng)治期間,東正教會(huì)的地位得到了一定提升,既不向蒙古人繳納賦稅,也相對(duì)獨(dú)立于蒙古統(tǒng)治者的控制。
莫斯科公國(guó)興起并成為羅斯統(tǒng)一的主導(dǎo)者后,羅斯東正教會(huì)與莫斯科大公便處于一種既合作又斗爭(zhēng)的矛盾狀態(tài)。一方面,雙方都是羅斯統(tǒng)一的積極推動(dòng)者,在國(guó)家統(tǒng)一與民族團(tuán)結(jié)這一立場(chǎng)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東正教會(huì)在國(guó)家運(yùn)行中處于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又存在分歧。根據(jù)拜占庭皇權(quán)高于教權(quán)的傳統(tǒng),羅斯主教們也不排斥接受皇帝在干預(yù)教會(huì)組織等方面的權(quán)威。但相對(duì)應(yīng)的,教會(huì)服從統(tǒng)治、維護(hù)統(tǒng)治是要以維持大量的教會(huì)和修道院土地為前提的,“盡管東正教會(huì)支持莫斯科大公政權(quán)統(tǒng)一全羅斯的事業(yè),但它不準(zhǔn)備為鞏固中央集權(quán)制國(guó)家而犧牲自己的傳統(tǒng)特權(quán)。”教會(huì)地主逐漸成為國(guó)家內(nèi)部的離心力以及不穩(wěn)定因素。
三、俄羅斯帝國(guó)時(shí)期
(一)彼得一世改革
彼得一世在位時(shí)期,意識(shí)到俄羅斯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西歐,便進(jìn)行了一系列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改革,以加強(qiáng)中央集權(quán)和鞏固封建專制制度。彼得一世不信任杜馬,經(jīng)常回避杜馬親自決定重大國(guó)事,完全以自己名義發(fā)布敕令,“在彼得親自掌管國(guó)事后所頒布的法令中明確宣布:‘沙皇陛下是專制君主,世界上沒(méi)有一個(gè)人的事他不該管。”在地方上推動(dòng)了地方行政機(jī)構(gòu)改革,設(shè)立了省行政單位以鞏固地方政權(quán)機(jī)構(gòu),使沙皇政令得以貫徹;在中央機(jī)構(gòu)方面,改革了舊的效率低下的莫斯科公國(guó)衙門機(jī)構(gòu),以新的中央機(jī)關(guān)——委員會(huì)來(lái)代替舊的衙門,提高了中央機(jī)構(gòu)的辦事效率。通過(guò)一系列改革,彼得一世加強(qiáng)了沙皇權(quán)利,鞏固了專制制度。
(二)教會(huì)權(quán)力走向衰落
教會(huì)與國(guó)家間的緊密關(guān)系在17世紀(jì)中期開始有所改變。1649年俄國(guó)政府開始禁止向修道院捐贈(zèng)土地,1659年又建立了世俗人員組成的修道院衙門,剝奪了教會(huì)的司法權(quán)。尼康的宗教禮儀改革導(dǎo)致了教會(huì)分裂運(yùn)動(dòng),這種分裂極大地削弱了教會(huì)的力量,使教會(huì)逐漸依附于國(guó)家。到18世紀(jì),彼得一世的改革根本性地改變了教會(huì)與國(guó)家的關(guān)系。彼得一世恢復(fù)了修道院衙門并擴(kuò)大了其權(quán)力,修道院衙門削減了教會(huì)機(jī)關(guān)的開銷,獲得了動(dòng)用教會(huì)領(lǐng)地的權(quán)利,教會(huì)領(lǐng)地的一系列包括免除賦稅在內(nèi)的特權(quán)被廢除,這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教會(huì)獨(dú)立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1721年,彼得一世頒布《宗教章程》,建立了宗教委員會(huì),使主教公會(huì)的一切事務(wù)的管理都處于國(guó)家監(jiān)督之下。通過(guò)這一些列改革,東正教會(huì)的獨(dú)立徹底被消滅,君主成為教會(huì)權(quán)力的唯一來(lái)源。教權(quán)終于徹底成為君權(quán)的附庸。
四、俄國(guó)君權(quán)壓倒神權(quán)的必然趨勢(shì)
君權(quán)與神權(quán)的產(chǎn)生都是與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密切相關(guān)的。近代以前,人類社會(huì)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較低,歐洲地區(qū)的社會(huì)生產(chǎn)主要以封建經(jīng)濟(jì)為主,以一家一戶的小生產(chǎn)為基礎(chǔ),彼此沒(méi)有聯(lián)系或很少聯(lián)系。農(nóng)民在被劃分的小塊土地上,不僅生產(chǎn)封建地主和自家生活所需要的農(nóng)產(chǎn)品,而且也生產(chǎn)必需的手工業(yè)品。依附農(nóng)民處于孤立分散狀態(tài),雖然他們?nèi)藬?shù)眾多,但被束縛在土地上,分別進(jìn)行個(gè)體生產(chǎn),互相隔絕,很少聯(lián)系,形不成爭(zhēng)取政治權(quán)利的有效力量。而作為封建領(lǐng)主的地主貴族階級(jí),則享有政治、經(jīng)濟(jì)、法律等諸多方面的廣泛權(quán)力,國(guó)王則正是貴族階級(jí)的代表,是實(shí)力最為雄厚的土地貴族。因此,在生產(chǎn)力水平?jīng)]有產(chǎn)生質(zhì)的提升,傳統(tǒng)封建經(jīng)濟(jì)穩(wěn)固的情況下,君權(quán)的存在和逐步加強(qiáng)是其必然產(chǎn)物。
主觀上,君主與貴族間的矛盾為宗教向世俗權(quán)力滲透提供了機(jī)會(huì)。自丕平獻(xiàn)土開始,教會(huì)逐漸開始掌握政治上的權(quán)力。丕平獻(xiàn)土的目的是謀求君主統(tǒng)治的合法性,“中古時(shí)代的宗教都為封建制度加上神圣的靈光。封建制本身被認(rèn)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對(duì)封建剝削和壓迫被視為大逆不道。因此要反對(duì)封建制度必須披上宗教外衣,剝掉它的神圣光環(huán)。”國(guó)王通過(guò)宗教的加持而穩(wěn)固自身的統(tǒng)治,同時(shí)為限制貴族權(quán)力而樂(lè)于賦予本國(guó)教會(huì)或羅馬教廷一系列權(quán)利以制衡貴族。但當(dāng)教會(huì)權(quán)力得到一定發(fā)展之后,教權(quán)又必將成為挑戰(zhàn)君權(quán)的敵人。教權(quán)往往反過(guò)來(lái)與貴族相聯(lián)合,向國(guó)王勒索更大的政治權(quán)力。這一現(xiàn)象在羅馬教廷影響下的西歐天主教國(guó)家尤為明顯,而信奉東正教的拜占庭與東歐國(guó)家情況則稍有不同。多中心的自主牧首區(qū)缺乏如梵蒂岡般的中央權(quán)威領(lǐng)導(dǎo),也就無(wú)法形成羅馬教廷一般強(qiáng)大的政治力量。
俄國(guó)的君主權(quán)力始終呈上升趨勢(shì),君主專制制度不斷強(qiáng)化。完善中央集權(quán)和君主專制是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完成國(guó)家統(tǒng)一并捍衛(wèi)龐大帝國(guó)的必要手段。在君主權(quán)力提升的過(guò)程中,東方專制主義的影響不可忽視,而舊的土地貴族和教會(huì)的權(quán)力則受到了削弱,失去了與君權(quán)抗衡的能力。
俄國(guó)東正教的引入最初便具有強(qiáng)烈的政治色彩,是基輔羅斯王公鞏固統(tǒng)治、加強(qiáng)與拜占庭聯(lián)系的政治手段,其根本目的便是服務(wù)于現(xiàn)實(shí)政治。這注定了俄國(guó)的東正教會(huì)自產(chǎn)生之始便在國(guó)家機(jī)構(gòu)中處于君權(quán)之下,這是東正教本身所固有的特性。雖然在蒙古入侵和大空位時(shí)期君主權(quán)威受到打擊,教會(huì)權(quán)力有所提升,但仍不具備羅馬教廷一般掌控世俗權(quán)力的實(shí)力,最終教權(quán)不斷被削弱,直至最后徹底成為從屬于君權(quán)的國(guó)家行政機(jī)構(gòu)。
由此可見君權(quán)的提升和教權(quán)的衰落是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必然趨勢(shì),這一點(diǎn)上俄國(guó)與西歐國(guó)家的表象大致相同。但不同于西歐國(guó)家君權(quán)與教權(quán)的激烈斗爭(zhēng),西歐基督教世界在丕平獻(xiàn)土后教會(huì)權(quán)力便凌駕于君主權(quán)力之上,在經(jīng)歷了亞維農(nóng)之囚與宗教改革等事件后才逐漸走向衰落。而俄國(guó)的東正教會(huì)實(shí)力較弱,自始至終都未能與君權(quán)爭(zhēng)奪世俗權(quán)力的主導(dǎo)權(quán),這又是俄國(guó)歷史發(fā)展與西歐有所不同的地方。
參考文獻(xiàn):
[1]瓦·奧·克柳切夫斯基.俄國(guó)史教程[M].張草紉,浦允南,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3.
[2]曹維安.俄國(guó)史新論[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2.
[3]張建華.俄國(gu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姚海.俄羅斯文化[M].上海: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社,2013.
[5]孫成木,劉祖熙,李建.俄國(guó)通史簡(jiǎn)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孟廣林.中世紀(jì)前期的英國(guó)封建王權(quán)與基督教會(huì)[J].歷史研究,2000(2).
[7]朱寰.略論中古時(shí)代的君權(quán)與教權(quán)[J].東北師范大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93(6).
[8]戴桂菊.俄羅斯東正教探源——羅斯接受基督教的原因與后果[J].世界宗教研究,1998(4).
[9]樂(lè)峰.簡(jiǎn)論東正教的基本特點(diǎn)[J].世界宗教研究,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