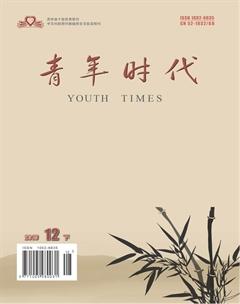滇越邊境跨國(guó)婚姻形成的促動(dòng)因素研究
盧秋容
摘 要:從過(guò)去到現(xiàn)在,滇越邊境一直存在著這一群體,那就是非法跨國(guó)婚姻群體。對(duì)滇越邊境跨國(guó)婚姻形成的動(dòng)力機(jī)制進(jìn)行研究,將有助于“一帶一路”戰(zhàn)略實(shí)施。跨國(guó)婚姻是多重因素促成的,本文從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及社會(huì)方面進(jìn)行綜合探析,得出滇越邊境邊民們的跨國(guó)婚姻與我國(guó)婚姻市場(chǎng)擠壓導(dǎo)致中國(guó)籍男性過(guò)剩、越南男女比例失衡導(dǎo)致越南女性過(guò)剩互補(bǔ)、我國(guó)經(jīng)濟(jì)快速發(fā)展帶來(lái)的吸引力、族群文化認(rèn)同構(gòu)成中越兩國(guó)關(guān)系及政策的動(dòng)力機(jī)制存在密切關(guān)聯(lián)。
關(guān)鍵詞:滇越邊境跨國(guó)婚姻;政治驅(qū)動(dòng);經(jīng)濟(jì)驅(qū)動(dòng);文化驅(qū)動(dòng);社會(huì)驅(qū)動(dòng)
一、跨國(guó)婚姻問(wèn)題的提出
目前,國(guó)內(nèi)中越跨國(guó)婚姻主要集中于4個(gè)方面:第一,研究跨國(guó)婚姻的類(lèi)型、路徑及婚姻模式;第二,跨國(guó)婚姻對(duì)邊境地區(qū)社會(huì)穩(wěn)定研究,其中,部分學(xué)者認(rèn)為跨國(guó)婚姻會(huì)威脅邊境社會(huì)的和諧穩(wěn)定,越南媳婦以婚姻為名,從事一些非法活動(dòng);第三,從國(guó)家認(rèn)同與民族認(rèn)同視角來(lái)研究跨國(guó)婚姻,有學(xué)者們認(rèn)為越南籍媳婦因無(wú)法獲得中國(guó)籍身份,從而導(dǎo)致她們國(guó)家認(rèn)同及身份認(rèn)同出現(xiàn)危機(jī);第四,從社會(huì)適應(yīng)視角對(duì)流入中國(guó)境內(nèi)的越南籍媳婦研究困難,現(xiàn)中越跨國(guó)婚姻從邊境地區(qū)向中國(guó)境內(nèi)蔓延,文化背景、語(yǔ)言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融入當(dāng)?shù)爻蔀樗齻兪滓媾R的問(wèn)題。
跨國(guó)婚姻作為一種特殊的區(qū)域性移民現(xiàn)象,滇越邊境跨國(guó)婚姻具有特殊的邊民和跨境民族身份以及獨(dú)特的地理位置,不再是單一元素形成跨國(guó)婚姻,而是要從多元視角,且把這一社會(huì)現(xiàn)象放在當(dāng)代背景進(jìn)行分析,從而深刻、準(zhǔn)確探析出跨國(guó)婚姻背后的深層成因。
二、調(diào)研點(diǎn)跨國(guó)婚姻現(xiàn)狀
我國(guó)西南邊境地區(qū)邊境線較長(zhǎng),僅云南段邊境線長(zhǎng)4 601千米,有16個(gè)少數(shù)民族跨界而居。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東南部,與越南接壤,與越南的國(guó)境線長(zhǎng)428千米,主要與3個(gè)縣城接界,分別是富寧縣,國(guó)境線長(zhǎng)75千米;馬關(guān)縣,國(guó)境線長(zhǎng)138千米;麻栗坡縣,國(guó)境線長(zhǎng)138千米。文山州有4個(gè)口岸,分別是麻栗坡的天保、都龍與董干口岸,富寧縣的田蓬口岸。
筆者調(diào)研的地點(diǎn)是文山州富寧縣田蓬鎮(zhèn),邊境線長(zhǎng)60千米,常居住人口有62 495人,其中少數(shù)民族人29 633人,占總?cè)藬?shù)的47.57%,主要有壯族、苗族、彝族和瑤族。田蓬鎮(zhèn)與越南的同文、苗旺縣接壤,有廟壩、龍哈、下寨、田蓬4個(gè)村委會(huì),27村小組直接接界。截至2017年,田蓬鎮(zhèn)共有804越南媳婦,通過(guò)合法手續(xù)的結(jié)婚證的共有85對(duì),719對(duì)跨國(guó)婚姻屬于事實(shí)婚姻,同中國(guó)籍丈夫生育的子女?dāng)?shù)量有1 044人,而越南籍媳婦從越南帶過(guò)來(lái)的子女?dāng)?shù)量有42人。
三、跨國(guó)婚姻形成的動(dòng)力機(jī)制
跨國(guó)婚姻的成因隨著社會(huì)變遷而改變,不再是簡(jiǎn)單的地緣和同一民族認(rèn)同所影響的,逐漸受到整個(gè)中國(guó)婚姻市場(chǎng)及女性在婚配選擇影響。
(一)跨國(guó)婚姻數(shù)量受兩國(guó)關(guān)系的影響
跨國(guó)婚姻易受兩國(guó)之間關(guān)系的影響,若兩國(guó)之間友愛(ài)和平共處,則跨國(guó)婚姻數(shù)量就多,否則反之。在現(xiàn)代國(guó)家未建立前,滇越邊境兩側(cè)邊民的跨國(guó)婚姻歷時(shí)悠久,當(dāng)時(shí)統(tǒng)治者曾頒布法令來(lái)制止此種婚姻,但還是“禁而不止,且聚眾既多”。隨著現(xiàn)代國(guó)家建立后,政府逐漸增強(qiáng)邊民對(duì)邊界、領(lǐng)土觀念,影響到滇越跨國(guó)婚姻,這不僅關(guān)乎兩個(gè)家庭,更是關(guān)乎兩個(gè)國(guó)家。1950年,中越是“同志加兄弟”關(guān)系,且受新中國(guó)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影響嫁入越南的中國(guó)人較多,且中國(guó)女性嫁入越南較多,滇越邊境兩側(cè)邊民交往十分密切。1960年,美越戰(zhàn)爭(zhēng)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中國(guó)援越抗美,中越還保持著親密關(guān)系,因蘇聯(lián)對(duì)越南進(jìn)行援助,所以越南邊境地區(qū)相對(duì)中國(guó)而言經(jīng)濟(jì)條件稍好,從而不少文山一側(cè)的邊民嫁給越南。20世紀(jì)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越兩國(guó)得關(guān)系屬于對(duì)持狀態(tài),特別是1979年對(duì)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兩國(guó)邊境區(qū)域處于一個(gè)敏感時(shí)期。一旦發(fā)現(xiàn)中越邊境的跨境民族來(lái)往密切,那就被判為國(guó)家間諜,此時(shí)中越邊境來(lái)往逐漸減少。1990年后,特別是2000年中國(guó)加入世界貿(mào)易組織,越南女性嫁入中國(guó)的數(shù)量逐年遞增,中國(guó)女性嫁到越南的甚少。
(二)傳統(tǒng)婚戀模式變遷
改革開(kāi)放與“一帶一路”建設(shè)的推進(jìn),尤其是農(nóng)民不再受土地的束縛,他們擁有更多的機(jī)會(huì)走出農(nóng)村從事一些非農(nóng)行業(yè)。隨著農(nóng)村人口數(shù)量不斷流出,中國(guó)女性思想得到解放后,越來(lái)越多的女性自愿走出農(nóng)村來(lái)到發(fā)達(dá)或沿海地區(qū)打工,而農(nóng)村女性也作為一種資源流出村莊,之前封閉保守的農(nóng)村屏障不斷被打破。因曾經(jīng)邊境地區(qū)的婚姻圈受到空間限制,不再僅限于當(dāng)?shù)貙ふ液线m伴侶,而是去發(fā)達(dá)地區(qū)尋找合適的結(jié)婚對(duì)象。因此,形成一個(gè)全國(guó)性及流動(dòng)性強(qiáng)的婚姻市場(chǎng),不再受地域限制。在當(dāng)今跨地域性的婚姻市場(chǎng)中,男性要想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wù),就必須加入全國(guó)性通婚圈,以激烈的手段獲得理想型配偶,而不再像從前那樣只通過(guò)地方性的通婚圈尋找一位理想的配偶。但是邊境地區(qū)的女性受到沿海或發(fā)達(dá)地區(qū)的吸引,在外打工中就會(huì)選擇合適配偶結(jié)婚,從而導(dǎo)致了大量邊境農(nóng)村地區(qū)的女性外流,且當(dāng)?shù)氐哪行允艿胶艽蟮幕橐鰯D壓。如果邊境農(nóng)村地區(qū)的男性要想娶到理想型配偶就必須拿出高于當(dāng)?shù)鼗橐鍪袌?chǎng)的婚姻成本,否則就很難找到理想型配偶。但是邊境地區(qū)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較落后,這就是當(dāng)?shù)啬行缘闹饕岸贪濉薄T谌绱思ち业幕橐鍪袌?chǎng)中,經(jīng)濟(jì)能力較弱的邊境地區(qū)男性就很難娶到本國(guó)女性,且受到很?chē)?yán)重的排擠,從而邊境地區(qū)的“剩男”越多。因此,這一大部分“剩男”就會(huì)通過(guò)區(qū)域優(yōu)勢(shì)到鄰國(guó)尋找伴侶,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wù)。
邊境地區(qū)部分男青年由于內(nèi)地婚姻擠壓導(dǎo)致娶妻難,也是造成邊境地區(qū)跨國(guó)婚姻頻繁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山州邊境地區(qū)居民貧困,生活比較困難。本地女青年不愿留在家里,紛紛到外地打工,最后就留在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地區(qū)。外地女青年也不愿意嫁到本地農(nóng)村。女性就“只出不進(jìn)”,造成邊境地區(qū)適齡階段的青年男女比例失調(diào),本地男人娶妻成了一大困難。這一困難恰好可以通過(guò)跨國(guó)婚姻解決。在越南找媳婦距離近、成本低、口碑好,逐漸成了適齡男性娶妻普遍選擇的一種方式。反觀越南邊境地區(qū),因20世紀(jì)90年代的中越戰(zhàn)爭(zhēng),越南邊境女子多于男子,造成當(dāng)?shù)匦詣e比例失衡,且經(jīng)濟(jì)發(fā)展較為落后。越南女性和中國(guó)男性的搭配恰好是兩個(gè)地區(qū)性別的“失調(diào)”與“互補(bǔ)”。
(三)族群文化認(rèn)同和邊境交流頻繁
1.族群文化認(rèn)同
滇越邊境山水相連,同一族源,文化語(yǔ)言相通,在歷史上皆有邊民跨國(guó)通婚的習(xí)俗。在新中國(guó)成立后,滇越邊界大部分明確勘定劃分,原來(lái)生活的同一地域被人為劃定為兩個(gè)國(guó)家,但是,對(duì)于邊境人民來(lái)說(shuō),他們?nèi)匀谎永m(xù)原來(lái)的生活傳統(tǒng),并沒(méi)有明確國(guó)家意識(shí)和邊境意識(shí)。雖然是生活在兩個(gè)不同的國(guó)家,但追根究底他們是同祖同源,擁有相似的語(yǔ)言、文字、服飾、信仰和習(xí)俗。因地緣優(yōu)勢(shì)使兩國(guó)邊民走動(dòng)頻繁,促成了跨國(guó)婚姻現(xiàn)象的形成和發(fā)展。對(duì)邊境人民來(lái)說(shuō),出國(guó)就像串寨子,跨國(guó)婚姻就是在“家門(mén)口”找對(duì)象。邊境村民進(jìn)出越南非常自由,既可以走正式的口岸和通道,也可以走民間便道。對(duì)當(dāng)?shù)厝藖?lái)說(shuō),滇越邊境設(shè)置的進(jìn)出關(guān)口形同虛設(shè),他們總有辦法過(guò)去、進(jìn)來(lái),穿梭自如。富寧縣的4個(gè)跨境少數(shù)民族都與越南跨境民族有共同節(jié)日或共同祭祀儀式。
2.邊境交流頻繁
邊境交流頻繁是邊境地區(qū)跨境民族跨國(guó)婚姻的重要成因。換句話說(shuō),滇越境跨國(guó)婚姻是基于地緣、血緣、族緣及業(yè)緣等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所形成的,而內(nèi)陸中越跨國(guó)婚姻幾乎是通過(guò)中介或拐賣(mài)促成的。
隨著中越“兩廊一圈”經(jīng)濟(jì)帶的構(gòu)建,兩國(guó)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往來(lái)較為頻繁,加之文山州向越南開(kāi)放的4個(gè)口岸。因兩國(guó)邊民跨境民族文化相似度極高,尤其是語(yǔ)言相通給邊民活動(dòng)帶來(lái)極大的便利,這就容易讓兩國(guó)邊民互相認(rèn)同和接納彼此為同一族群。在調(diào)研過(guò)程中得知,在1990年后文山州邊境地區(qū)村民們到越南做生意或打工,在取得越南家庭的信任后,就娶了越南媳婦。我國(guó)邊境相較于越南邊境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與人民的生活水平質(zhì)量較高,這就吸引了越南籍女性愿意到中國(guó)工作,形成了跨國(guó)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有的越南籍女性通過(guò)來(lái)中國(guó)打工結(jié)識(shí)到中國(guó)籍男性之后就結(jié)婚了,這就體現(xiàn)出業(yè)緣是跨國(guó)婚姻的重要渠道之一。長(zhǎng)期以來(lái)的跨國(guó)婚姻,形成了邊境地區(qū)交錯(cuò)的以“血緣”為主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如壯族、苗族、瑤族等跨境民族都有跨國(guó)親戚。尤其是跨境民族的邊民交往密切,一起參加具有族群文化認(rèn)同感的節(jié)日。
(四)經(jīng)濟(jì)差距形成“推拉”合力
跨國(guó)婚姻所屬國(guó)家在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發(fā)展存在的差距是跨境婚姻形成的主要?jiǎng)恿ΑT谡{(diào)研中得知,越南籍女性嫁入中國(guó),希望通過(guò)婚姻來(lái)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以及越南娘家的生活質(zhì)量。越來(lái)越多的越南女性愿意嫁到中國(guó)來(lái),以為中國(guó)有錢(qián),寄望于通過(guò)婚姻改變自己的命運(yùn),甚至改善整個(gè)家庭經(jīng)濟(jì)狀況。邊境兩側(cè)發(fā)展差距構(gòu)成跨境婚姻的“推拉”合力。
文山州邊境農(nóng)村吸引著越南邊民嫁入或入贅到中國(guó)來(lái),正是因?yàn)樗麄儭按蠖鄶?shù)人希望在物質(zhì)方面得到改善”。目前,中國(guó)和越南在經(jīng)濟(jì)上存在巨大的差距,越南邊民通過(guò)婚姻的方式進(jìn)入中國(guó)邊境地區(qū)。雖然文山州邊境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整體發(fā)展水平低于其他地區(qū),但相較于越南邊民的生活水平來(lái)說(shuō),中國(guó)邊民生活質(zhì)量是高的。由此可見(jiàn),中國(guó)邊民農(nóng)村家庭收入水平高于越南農(nóng)村家庭收入,而且這種差距非常明顯。正是這樣,越南邊民會(huì)想盡一切手段來(lái)到中國(guó)。越南籍小孩到中國(guó)邊境地區(qū)上學(xué),成年人到中國(guó)邊境地區(qū)務(wù)工,并找機(jī)會(huì)與中國(guó)當(dāng)?shù)厝送ɑ椋粼诋?dāng)?shù)厣睢T侥线吤裣Mㄟ^(guò)這種特殊方式留在中國(guó),最好的途徑是成為“越南媳婦”或“越南姑爺”,這是一種“經(jīng)濟(jì)理性”的行為。嫁來(lái)中國(guó)的目的是追求更好的經(jīng)濟(jì)收入,提高生活質(zhì)量和水平,過(guò)上更好的生活,也是為了讓后代有更好的教育和社會(huì)保障。但一旦越南籍邊民發(fā)現(xiàn)嫁入中國(guó)后,發(fā)現(xiàn)中國(guó)生活不如自己所想的那樣美好,就會(huì)選擇拋棄家庭,重新嫁入經(jīng)濟(jì)條件相對(duì)優(yōu)越的家庭。
四、結(jié)語(yǔ)
滇越跨國(guó)婚姻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邊境地區(qū)的跨國(guó)婚姻是基于地緣、血緣及族群文化認(rèn)同呈現(xiàn)出的一種婚姻行為自覺(jué)性,這是與內(nèi)地中越跨國(guó)婚姻明顯區(qū)別的一大因素。但隨著社會(huì)快速發(fā)展,跨國(guó)婚姻形成不僅只有這一單元因素,還包括多元因素,慢慢轉(zhuǎn)化為以社會(huì)因素為主。滇越跨國(guó)婚姻的形成是多元因素共同促成的,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因素:第一,政治驅(qū)動(dòng),跨國(guó)婚姻易受中越兩國(guó)關(guān)系及政策的影響;第二,社會(huì)驅(qū)動(dòng),我國(guó)婚姻市場(chǎng)男性過(guò)剩與越南婚姻市場(chǎng)女性過(guò)剩形成互補(bǔ);第三,文化驅(qū)動(dòng),受地緣、血緣及民族認(rèn)同感使滇越邊境地區(qū)邊民互動(dòng)頻繁;第四,經(jīng)濟(jì)驅(qū)動(dòng),中越邊境地區(qū)經(jīng)濟(jì)差距形成推拉合力,中國(guó)經(jīng)濟(jì)水平是越南女性嫁入云南邊境地區(qū)的拉力,而越南經(jīng)濟(jì)水平則是推力。
參考文獻(xiàn):
[1]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國(guó)婚姻及其族群關(guān)系[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2]羅文青.和平與交往:廣西邊境地區(qū)跨國(guó)婚姻問(wèn)題初探[J].廣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6(1).
[3]白志紅,李吾景.中緬邊境非法跨國(guó)婚姻對(duì)云南邊境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和諧穩(wěn)定的影響分析——以云南省龍陵縣徐家寨為例[J].昆明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1(4).
[4]保躍平.選擇與困境:云南邊境跨國(guó)婚姻的社會(huì)學(xué)分析[J].北方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4).
[5]谷家榮.地域、身份與認(rèn)同——云南金水河村傣族跨國(guó)婚姻調(diào)查[J].人類(lèi)學(xué)研究,2009(10).
[6]羅柳寧.例論中越邊境跨國(guó)婚姻建立的基礎(chǔ)——兼論“無(wú)國(guó)籍女人”的身份[J].廣西民族研究,2010(1).
[7]師有福,滿麗萍,自正發(fā),等.滇越跨境民族和諧文化關(guān)系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