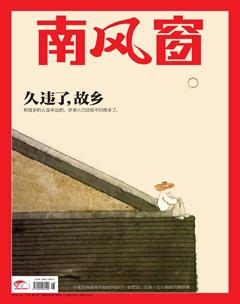酒杯里的中國人
之心

不得不說,生活在一個酒的生產和消費大國,尤其又到了年關,《南風窗》的《酒里·人間》出現得恰逢其時。
對于筆者這樣對我國主要名酒都了解不多的外行人來說,這一組仿佛讓人浸潤在醇綿酒香里的文字,既是酒知識的科普,也是體驗各地民風世情的文化之旅,更是中國人個體與群體處世哲學的生動寫照。如果要將酒在國人、歷史和文化中的地位加以區分,我倒覺得可以借用馮友蘭先生對人生境界的說法: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文化)境界、天地境界。
自然境界是酒的最初形態:在基本滿足了糧食需要后,人們為了追求更深層次的口腹之欲而發明(也可能是偶然發現)了酒。這階段的酒,沒有任何人為賦予的意義和標簽,它只是一種飲品。
功利境界,則是人們希望借助酒達到某種具體的目的。比如,驅寒;比如,以酒為業,養家糊口;比如,為了交際應酬飲酒,是為了融入某一圈子,獲得群體的情感認同或某種現實愿景;比如,為了宣泄快樂或痛苦而飲酒,是希望麻痹和釋放情感。
道德(文化)境界,比如歷史上,文人墨客們的為酒癡狂,“斗酒十千恣歡謔”“白日放歌須縱酒”是唐朝的豪邁灑脫,“把酒問青天”“沉醉不知歸路”是宋朝的婉約深情,“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是今人對古人的追憶與思慕……在中文系讀書時,經常有同學開玩笑:要是古人不那么嗜酒,我們現在得少多少“背誦全文”啊!這句話背后的真正意思是:要是沒有酒,我們的詩歌、文學得多黯然失色啊!在燦若星河的史學、文學、藝術史中,酒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筆觸;但在嚴肅的道德家眼里,酒往往又被賦予了放縱無節制、失德敗行等暗黑標簽。
天地境界,則關乎“融合”一詞。傳統釀酒工藝與現代企業運作模式的博弈,得天獨厚的酒產地與外來文明的碰撞;各個酒產地對地域風情、生存哲學和審美原則的堅守與吸收其他酒特長的搖擺;世代以酒為生的傳統人,其價值觀、愛情觀,與信奉快餐文化、及時行樂的都市人的對壘;甚至個體的縱情享樂與理性克制的撕扯,一直并且將長期存在下去。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之所以飽經滄桑卻綿延不絕,靠的正是一股兼收并蓄的包容情懷,中國人太懂得在求同存異中達到和諧。這是人生的大智慧,也是中國人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
有趣的是,到了當今社會,酒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意識觀念中,正“返璞歸真”,回歸其本來的單純物質形態。知識分子心中和筆下的酒,自帶各種風情,但世代生活于酒產地的人們,或許對此并沒有自覺清醒的認知,但這并不妨礙他們自主地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樣”。這才是生活和人生本來的模樣,你不需要懂得太多太深奧的大道理,按照自己的本心走下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