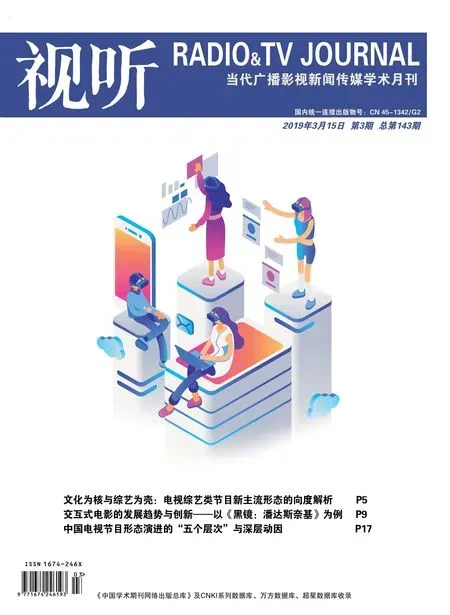電影《芳華》敘事空間的多重建構
□ 蔡宏全
電影《芳華》改編自嚴歌苓的同名小說,由馮小剛導演執導。影片通過營造我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場景和氛圍,再現主人公們的青春年華,掀起了一陣追憶“芳華”的熱潮。《芳華》全片采用蕭穗子這一故事內人物的內聚焦模式作為電影文本的主要敘事視角,以蕭穗子回憶故事的旁白展開敘述,講述以劉峰、何小萍等人為代表的一代文工團人的命運變遷。影片通過內聚焦模式敘述“撒謊精”何小萍在文工團遭到排擠,“活雷鋒”劉峰“觸摸”女戰友等事件,主要以事件的因果關系為動力,以事件的順序發展為主線來建構故事,具有相當清晰的敘述指向。影片在整體敘事當中,構造多個帶有時代特征的敘事空間發展情節,突出人物性格并深刻展現影片主題。
一、電影敘事空間簡述
作為一種以視覺畫面為基礎講述故事的藝術,電影敘事通過直觀的空間視覺呈現才能夠形成自己獨特的敘事個性及話語魅力,而敘事的技巧以及組合形式都以此為基礎。塑造敘事空間的主要目的在于為故事事件創造真實的環境,引導讀者進入虛擬的故事世界。
經典電影《肖申克的救贖》故事空間主要置于監獄之中,監獄作為強制剝奪自由、高度強調紀律的特殊空間來展現人對失去自由以及被強制改造的恐懼。而西班牙電影《看不見的客人》將“辯護演習”的敘事空間和“殺人事件”的敘事空間分別構置于男主人公的公寓和人跡罕至的野外。一個是被當作給人安慰和內心的空間,另一個是給人以人性釋放且道德法律束縛薄弱的空間,看似對立的二重空間實際上呈現出一定的互文性。殺人者把公寓當作壓縮并保衛內心的空間,這個密閉的空間就開始有了人性的轉化,在“律師”的拷問下慢慢撕裂了他人性的面具,而在空無一人的野外,人性最殘忍的一面更是暴露無遺。所以不難看出,空間有著強有力的象征和隱喻的功能。電影《芳華》中營造的文工團大院、對越自衛反擊戰戰場、戰地后方慰問演出等多個敘事空間具有重要的結構意義。
二、《芳華》的多重敘事空間
(一)夢想消解地——文工團大院
在《芳華》這部烙印一代人獨特而鮮明的青春記憶的影片之中,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部隊文工團大院是承擔了大量敘事作用的主要故事空間。“當空間和時間元素、人的行為和事件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空間變成了場所,體驗的多樣性是敘事空間的最為重要的特征。”①眾所周知,文工團是基層士兵艱苦的軍營生活中唯一的一道色彩,將文工團、特殊年代以及少男少女的愛情和命運相結合,文工團大院這個空間成為了一個具有清晰特性的場所。馮小剛還原了紅色年代中充滿理想和激情且相對封閉的敘事空間,作為整部影片塑造歷史背景、環境氛圍、人物以及展現大量故事情節的基礎。
在影片當中,何小萍一出場就成為了低人一等的角色,不被善待的命運似乎早已被書寫。她想讓正在勞改的父親看到她穿上軍裝的模樣,她想得到她從未得到過的身份認同,而她卻沒辦法向室友們解釋為什么要“偷”軍裝,更沒辦法得到室友們的原諒和理解。剛踏入文工團大院,她就成了眾矢之的,有傷風化的冤枉和臭氣熏天的嫌棄也隨之而來。她在文工團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孤獨無助,而劉峰對她的幫助是她在這個集體里的唯一支柱。劉峰一直是被歌頌的“活雷鋒”,善良無私,他專挑大家不吃的破餃子,幫林丁丁修手表,抓別人不小心放跑的豬,幫戰友做沙發……他總是為集體付出,從不計回報。而正是因為這樣,他仿佛不應該擁有常人一樣的情感,大家都愛他的付出,將他的一切作為視為理所應當,可大家都把這份善良和高尚獨立于這個“集體”之外。以至于林丁丁面對這樣一個大家都贊揚的人對她表現自己赤誠的內心時不知所措:“不為什么,誰讓他是活雷鋒,活雷鋒就是不行。”劉峰就因為這樣的一個“觸摸事件”變成了一個“道德有問題”的“罪人”,除了何小萍,沒有任何人為他一如既往的善良和付出伸張過一句。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認為,社會由多個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空間所組成,這些空間建構起“場域”,在“場域”當中,每個個體“就被拋入這個空間之中,如同力量場中的粒子,他們的軌跡將由‘場’的力量和他們自身的慣性來決定”。②在宣揚集體主義的獨特年代,這個集體至上的環境中,容不得個人的主體性。在文工團大院這個敘事空間中表征了一群少男少女的集體性格,而“不合群”的何小萍和“手捧群體”的劉峰的悲慘命運似乎是必然的。不管是低于集體的出身和高于集體的奉獻都意味著孤獨,都意味著得不到集體的包容與理解。馮小剛對文工團大院這個獨特敘事空間的構造,將時代的扭曲、個人和集體的沖突、善與惡的邊界模糊等主題在影片當中凸顯。
(二)心靈庇護所——對越自衛反擊戰場
劉峰犯下“錯誤”之后,心甘情愿地上了戰場。馮小剛對戰場的構建也是不遺余力,斥資700萬元打造了一個槍林彈雨、滿目瘡痍的敘事空間,與文工團大院的和平閑適形成強烈的對比。對戰場這一敘事空間的構造更加側重于何小萍和劉峰的獨特個性及心理轉變的深層次表達。“在敘事作品中書寫一個特殊的空間可以很好地表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③對戰場的細致構造,將戰場的激烈和生命的消亡赤裸裸地搬到了銀幕之上。
從和平的文工團到了激烈的戰場空間中,劉峰從無私奉獻的“活雷鋒”成了無畏勇敢的戰士,他一如既往地點燃自己。劉峰指揮連隊護送馱隊向前線運送彈藥途中遭敵軍伏擊,劉峰帶隊拼命反擊,完全不懼怕死亡。他不僅用他的無私和奉獻做支撐,更是將他由于對林丁丁的愛而不得和被集體拋棄所凝聚的絕望融情于空間之中。他曾說過自己的“私心大著呢”,心如死灰地等待犧牲應該就是他在戰場上最大的“私心”了,戰場這個激烈血腥的空間反而成了使劉峰平靜的庇護所,為戰而死成了他實現自己價值的最便捷的方式。劉峰離開后,何小萍也將自己放逐到了戰場上,成了一名救死扶傷的護士。在這樣一個硝煙彌漫的地方,她的悲慘和孤獨顯得格外渺小,反倒給了她在生活重壓下喘息的機會。在這里她能找到自己的價值,不會再有人排斥譏笑她,明明是尸橫遍野的疆場卻成了她實現自我的避難所。
“一個豐富的性格世界,是許多組性格元素合成的復雜網絡結構,在這種結構中各組性格元素互相依存、互相交織、互相滲透,互相轉化并形成自己的結構層次,使性格呈現出復雜而有序的運動狀態。”④戰場這一敘事空間將人物的心理狀態進行沖突性的展現,分別把被神化的劉峰和被孤立的何小萍的人物性格進行了融合性的描敘,讓故事人物的形象變得更為立體和豐富了起來。
(三)夢想棄置點——戰地后方慰問演出
劉峰的離去也使何小萍的精神支柱消失,她想要逃離這個冰冷的集體。文工團去戰場后方的舞臺進行慰問演出給了何小萍命運線索一次轉折的機會。馮小剛用艱苦的環境、惡劣的天氣以及戰士們的打氣等構造了一個極具事件性的敘事空間,并以“裂口”的方式呈現事件自身。
何小萍真正變得心如死灰是在她的精神支柱劉峰被“打倒”之后,劉峰是何小萍在這個集體存活下去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就是這份力量也湮滅了,她不愿再給自己和這個集體機會了。但她找不到機會和理由走出文工團大院這個冰冷無情的地方。直到到了戰地后方去慰問演出,卓瑪意外摔倒,她終于得到了跳A角的機會,終于能夠實現她作為一個文工團員向戰地軍人送去溫暖的價值,但她卻不屑一顧。敘事作品中的空間總是被填滿了空間以外的許多意義,戰地舞臺對于戰士來說是精神慰藉的來源,對于文工團員來說是實現價值和理想的空間。建構戰地舞臺為敘事空間作為何小萍這條敘事線索轉折點的空間基礎,對文工團員來說本該充滿能量和夢想的戰地舞臺卻成了她嗤之以鼻的無情之地。她想要逃避承認自己在這個集體中是有價值的一份子,知道自己能離開這個集體去追隨劉峰的時候,這個轉折性的戰地舞臺格外賦予了她最后釋然的微笑,以及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希望的重現。
(四)舞臺最終回——荒地與最后一次舞臺
文工團面臨解散的最后一次舞臺正好和何小萍再次“相遇”。在戰場奮不顧身地搶救傷員讓何小萍陡然成為英雄,這卻讓一直在塵埃中掙扎的她崩潰了。見過了太多的殘酷,遭受了太多的冷待,突然獲得這樣的殊榮讓她像一棵凍得太久的大白菜搬進了暖和的屋子里那樣壞掉了。當她回到文工團時,聽到昔日熟悉的旋律,仍然喚醒了她內心深藏的夢想和激情,在音樂聲中翩翩起舞,荒地已然成了舞臺。將舞臺和荒地這兩個空間同時展現出來,來證明舞美、燈光、觀眾都不是何小萍所真正追逐的,她內心對舞蹈那份純粹的熱愛是無法被磨滅掉的。荒地這個空間的塑造正是何小萍心理空間的具象化,寸草不生的荒地象征著何小萍的心如死灰,而舞蹈則象征著她對生命潛藏的一絲希望。這是文工團的最后一次的告別舞臺,但卻是何小萍涅槃重生的舞臺。“空間和時間標志融合在一個被認識了的具體整體中。時間在這里濃縮、凝聚,變成藝術上可見的東西;空間則趨向緊張,被卷入時間、情節、歷史的運動之中。時間的標志要展現在空間里,而空間則要通過時間來理解和衡量。”⑤在影片中的象征意義上,時間是空間的第四屬性。“最后一次的舞臺”很好地承接影片前部分情節,并為之后何小萍擺脫精神失常狀態的情節發展線索埋下伏筆,是具有強烈事件性和內涵色彩的敘事空間。
(五)浮沉命運線——海口和蒙自
對于《芳華》來說,海口和蒙自都是為描敘文工團解散多年之后的人物發展而構建的,意圖將人物的命運這條敘事線索完整呈現以緊扣“芳華已逝”的核心主題。失去了手臂的劉峰在海口自謀生路,遭遇不公對待,誰還知道他曾是人人歌頌的“活雷鋒”;而不管是出現在鏡頭中的蕭穗子和郝淑雯還是在她們談話中被交代出各自生活的陳燦和林丁丁,他們全都生活得精彩又體面。劉峰與何小萍相約蒙自,祭奠在戰場犧牲的戰友,兩個被社會閑置的人坐在一起回首當年。一個沒人想得到的擁抱,一張沒人會在意的照片,是他們彼此之間羈絆的具象化。他們過得不好,又“比躺在陵園里的兄弟好太多”,最終故事回到蕭穗子的旁白中構造的話語空間——孩子的婚禮上與戰友的重聚。芳華已逝,時間在他們身上烙下了無法磨滅的傷疤,縱使過去再輝煌,如今也變得黯淡;縱使過去再悲慘,如今也已成往事。
三、結語
“只要電影是一種視覺藝術,空間似乎就成了總的感染形式,這正是電影最重要的東西。”⑥馮小剛對敘事空間的豐富構建使整部影片有了更強的感染力,避免了單一的敘事空間帶來敘事的單一化,將觀眾隨著空間的切換引入敘事情節當中,引導敘事并深刻刻畫人物命運浮沉。基于對芳華已逝的緬懷,以個人的方式深刻反省和檢討時代,成就了一部反響極大的文藝片。
注釋:
①[英]馮煒.透視前后的空間體驗與建構[M].李開然譯.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74.
②[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M].劉暉 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15.
③龍迪勇.空間敘事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295.
④劉再復.性格組合論 [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59-60.
⑤巴赫金.小說理論[M].白春仁,曉河 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75.
⑥[法]馬賽爾·馬爾丹.電影語言[M].何振淦 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