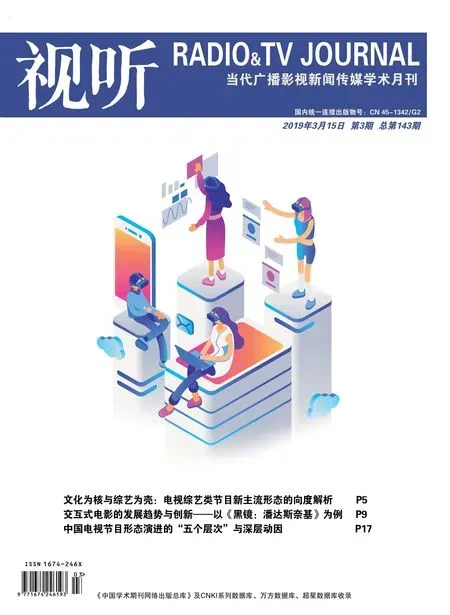意見領袖理論在新媒體時代的變遷
□ 劉娟娟
意見領袖的概念是起源于拉扎斯菲爾德等人的研究,他們經過一系列研究注意到二級傳播的現象,即大眾傳播傳遞的信息并不是直接經由媒體傳達給受眾,而很多時候需要經過意見領袖這一“中間人”。先能與大眾媒介的信息進行接觸,并經過加工后再傳播給群體其余成員的人即是意見領袖。意見領袖理論的發現,印證了人際交往,尤其是主要群體間的人際交往,在交際效果過程中起到了獨特的作用。①
一、傳統媒體時代和新媒體時代意見領袖的不同點
在新媒體時代,網絡基礎設施的普及以及即時和非即時通信工具的發展降低了通信活動的成本,在跨區域甚至跨界社區之間提供了個人交流的可能性,大眾傳播不再是過去少數專業人士的專有權利,而是已經成為一定的專有權力。由于新媒介對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的整合,意見領袖不再來自于追隨者同質化的初級群體,而是具有大眾傳播的特征,由此激發了很多的改變。
(一)趣緣群體的出現
隨著利益集團的成長,小我的群體屬性變得加倍多樣化,這只是用戶面臨的“建議來源”之一。個人不再受到線下團體的限制,甚至在一起吃東西時不玩手機已經成為測試家庭關系的標準。過去受眾的一些意見可能會改變,因為他們無法獲得主要團體的支持。現在他們可以在互聯網上通過各種興趣群體獲得社會支持,主要群體對他們造成的社會壓力削弱。隨著傳輸成本的降低,個人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與跨地區甚至跨界團體取得聯系,形成一個以共同利益為紐帶的“部落”。
(二)權力的重新分配
新媒體成長伴隨著劇烈的權利去中心化與再中心化。一方面,技術發展帶來了“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交話語更加集中。技術賦權使話語權下放,社會上堆積著各類狂歡式表達和價值觀,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邊界不斷模糊,人們可以依照本身的意愿消解傳統和權威,隨意發表意見。然而,面對大量的信息,觀眾很難迅速識別出有價值的部分,而且他們不得不依靠少量的資源來幫助他們篩選信息并重新聚焦話語。在這一過程中,組織化的媒體的權力正流向自媒體化的意見領袖群體中,這也深刻地影響著現實政治的進程。在美國大選中,特朗普正是通過推特這一新媒體平臺,繞過傳統媒體的圍剿,通過推特網民和意見領袖的支持,打敗了建制派的希拉里。這意味著一種加倍民主(或是民粹)的政治可能性。
(三)意見領袖——資本拓展的新疆界
意見領袖脫離初級群體進入開放的社交媒體的過程,也是資本的力量對其進行收編重構的過程。威廉斯認為,媒體技術的發展形成了各種社會“意圖”。因此對于新媒體及寄生于其上的意見領袖的分析,就不能脫離中國的媒體市場化發展的語境。
在大眾傳播時代,存在于初級群體的意見領袖,對信息的篩選并不受資本的影響。但在新媒體時代,意見領袖是在資本與商業驅動的新媒介之內被構建出來的,意見領袖不再是資本的法外之地,而成了資本開拓的新疆土。這符合新自由主義的邏輯:盡可能地擴大私有產權的領域與資本的自由活動范圍。
(四)初級群體影響力變弱,新的意見領袖參與大眾傳播過程
拉扎斯菲爾德在書中指出,意見領袖不僅在政治范疇,在人們日常生產生活范圍都存在廣泛的受眾群體。在大眾傳播的時期,媒體是信息來源和傳播者,而觀眾是接受者。因此,意見領袖的角色是單向溝通過程,缺乏反饋;在新媒體時代,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意見領袖在參與傳播的過程中也產生影響,而且進行實時的互動和反饋。意見領袖可以是信息的傳播者或反饋的接受者。
(五)全景敞視監獄——意見領袖的自我規訓
離開了初級群體的意見領袖,將自己置身于具有福柯所謂的“全景敞視監獄”特征的新媒體平臺中。相較于大眾傳媒時代,意見領袖是模糊而分散匿名的,但在新媒體時代,意見領袖在賽博空間的一舉一動都以數據的形式呈現在監管部門的面前。意見領袖們時刻感受到權力的凝視,在發布信息時必然不斷地自我規訓,達到福柯所說的“標準化”的結果。
二、新意見領袖擴張背后隱藏的風險
(一)道德風險的存在
雖然新的意見領袖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但他們仍然缺乏合理的內部道德體系和外部監管制度來約束他們,某種程度上存在著一定的道德風險。最顯著的是,許多大V盲目地追逐熱點,并傳播在專業領域之外的大量事件以擴大影響力。這在造成用戶信息超載的同時,也導致社交話語領域紊亂。在一些相對敏感的時期,一些大V不適當的演講可能會引發社會矛盾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二)易加劇群體的沖突分化
大眾傳媒時代,由于傳統媒體進行單向傳播,受眾被動地接受,缺少反饋機制。新媒體與眾不同的特點是直接互動,這進一步模糊了傳播方之間的界限。意見領袖將自己的關注者和追隨者團結在自己周圍,形成群體關系,并將他們融入正在進行的群體互動和公眾事物協商中,所以,影響力更具有即時性。意見群體的內部整合構成了群體共識,同一內部群體的整體捆綁與異質群體的沖突會加強整合或分解。然而,集團營地的形成對媒體環境有著不可預測的影響。
(三)與受眾關系更不平等
拉扎斯菲爾德指出,意見領袖并不集中在特定的群體和階級中,而是平均分布在社會的任何群體和階層中,和受影響的人,即受眾處于平等關系而非上下級關系。新媒體時代,意見領袖和觀眾的地位有所變化。在新媒體時代的研究中,學者蔡艷和曹慧丹研究意見領袖時提出,這個時期的意見領袖具有基督教的屬性。在受歡迎程度方面,它們更具魅力,并且它們與普通觀眾之間地位有所區別。
三、如何應對新媒體時代的意見領袖
在意見領袖崛起的當下,作為奉行“黨管媒體”與“群眾路線”的國家,官方部門應處理好與這些“中間人”的關系,使信息和政策更加有效,同時還需要建立更加開放和透明的信息系統,避免信息阻塞導致的部分不良指導造成的危害。有關部門應該對意見領袖進行規制,防止其淪為資本的機器;也應該建立國家—意見領袖—群眾的有機聯系,對其進行積極的賦權,使意見領袖更具有公共性與人民性。
(一)完善和執行與網絡輿論相關的相關法律規范
意見領袖的言論歸根結底就是輿論引導力的問題。意見領袖的意見和行動的指導應納入法律約束框架。建立和完善信息發布制度,加強信息核查和控制,消除重度的煽動性、情緒化,明顯的低質信息和言論;政府和有關部門要依法治理網絡,積極引導,嚴格執法,嚴懲不負責任、發布煽動性言論的負責人。同時,要建立健全互聯網輿論工作機制,完善問責機制,為輿論指導提供潔凈的公共空間和完善的制度保障。
(二)培養公共理性,提升媒體素養
新媒體中以群體為基礎的傳播方式,消除了用戶質疑和批評的能力,并做出了不合理的分析和反應,從而影響了輿論界的良好氛圍。媒體素養影響人們辨認、判定、評估和利用信息的本領。面對新媒體的復雜信息和輿情,觀眾應該能夠正確理解分析媒體信息,提出批評意見,提高對負面信息的免疫力。
(三)建立和完善輿情反應機制
在“紙包不住火”的新媒體環境下,互聯網輿論的傳播效應不斷擴大。積極引導意見領袖在這個時候是特別重要的。可以允許多元的話語權和上訴權,但必須堅持以一維為基礎的多元核心價值觀。一方面,利用新技術構建輿情監測系統,對事件反應進行及時跟蹤,增強輿情分析;另一方面,加強監測隊伍建設,提高技術應用能力。二者共同發力,才能使意見領袖更好地引導輿情。
大眾傳媒時代意見領袖曾廣泛分布于各個階層,新媒體意見領袖則帶有鮮明的都市中產階級的特點。在網絡公共話題的討論中,都市中產占據著極大的話語權。在社交媒體中,經由意見領袖的挑選進入公共議程的往往是受中產階級關注的議題,比如魏則西事件、雷洋案等,這些議題加深了中產的危機感,并經由意見領袖的話語建構,使中產階級的訴求轉化為“我們”“公眾”“人民”的訴求。
注釋:
①[美]保羅·F·拉扎斯菲爾德,伯納德·貝雷爾森,黑茲爾·高徳特.人民的選擇:選民如何在總統選戰中做決定[M].唐茜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