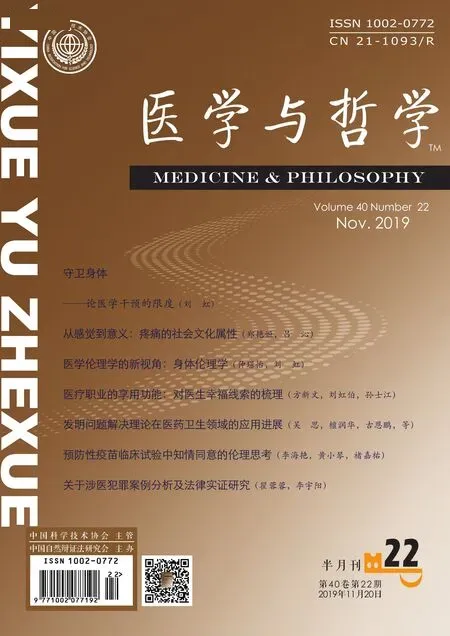醫學倫理學的新視角:身體倫理學*
仲璟怡 劉 虹
晚近,我國著名醫學倫理學家杜治政教授發表題為《梳理·整合·開拓·堅守——醫學倫理學的回顧與思考》的重要文章,對我國醫學倫理學37年發展的歷史,對醫學倫理學、生命倫理學的若干重要問題進行了高屋建瓴地剖析和論述。杜治政教授[1]指出:“現在還要求超出機體,從身體視角認識疾病。這是醫學,也是醫患關系中的重大理論問題。有關身體哲學的研究,國外學術界出了許多成果,我們不妨學習一下。”身體倫理學是身體哲學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醫學倫理學、生命倫理學不可或缺的補充和矯正。在身體倫理學的語境中,我們對醫學倫理和生命倫理遭遇的困惑會有新的穎悟。
1 實踐呼喚身體倫理學
1.1 生命倫理學:實踐中的失能、失效、失范
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哲學構成了碾壓一個時代的理性主義至上的思維方式和話語邏輯,影響波及人類精神世界的不同領域,醫學倫理學和生命倫理學都在其輻射范圍之中。醫學倫理學強于普適倫理法則的頒行,弱于對身體感受和情境事件的回應;生命倫理學依舊沒有走出笛卡爾普遍理性原則的窠臼,失察于身體的倫理意義,生命倫理學的原則面對諸如生命合成、人獸混合胚胎、基因編輯等問題表現出失能、失效、失范的尷尬。
醫學倫理學和生命倫理學試圖從理性出發,為醫學行為和生命科學研究“講秩序”、“立規矩”,并將之作為判定是非善惡的普適標準。但是,身體主觀差異和不確定性、身體情境事件等卻往往被普適性的理性標準排除在外。在當代科學技術條件下,身體提出的新的問題不斷沖擊和挑戰現有的倫理學理論。例如,當代醫學技術可以長期維持持續植物狀態者的心跳和呼吸,然而,長期沒有正常意識、沒有身體感受、沒有生命尊嚴的持續植物狀態者,是維持還是中斷其存活狀態的問題、安樂死問題等,令醫學倫理學和生命倫理學糾結不已,至今難以給出能得到社會認同的普適性意見。類似的困境,如面對頭顱移植、基因編輯、人體試驗等傷害身體的醫學行為,現有的倫理學理論蒼白無力甚至相互矛盾,實踐干預乏術。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1.2 身體倫理學:補充和矯正
身體是生活的主體,當現有的倫理學理論無法應對流變不定的身體問題的時候,削足適履,將身體作為管制對象或長期處于理論爭鳴、實踐干預乏力的狀態都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現象。走向身體本身,建構身體倫理學的必要性由此凸顯。
2005年,《身體倫理學:后習俗的挑戰》一書出版,書中作者提出“身體倫理學”的概念:“我們提供的不是關于身體的生命倫理學(bioethics about the body),而是‘身體倫理學’(ethics of the body)。”[2]
身體倫理學以身體哲學為理論基礎,強調倫理學理論與實踐的具身性,強調關注患者的整體性身體,強調身體感受。身體倫理學不否認醫學倫理學和生命倫理學追求普適倫理規則的價值和意義。醫學倫理學和生命倫理學作為醫學場域、生命場域的宏大敘事、常規線性敘事的形式,提供評估醫學行為是否合乎倫理標準的抽象規則,是社會主流文化判定醫學行為善惡是非的權威化、合法化的表現。因此,身體倫理學無法替代醫學倫理學和生命倫理學。但僅僅有抽象的原則是不夠的,身體總是獨特的、個別的、具體的,醫學實踐中的倫理問題總是具身的、感性的、個別的,因此,身體倫理學作為具象敘事、多線性敘事體現出不可或缺的價值和意義。
身體倫理學并不是一種新的倫理學理論體系,而是身體哲學思潮中的組成部分或者說是身體哲學在倫理學中的表現形式。身體倫理學是一種本體選擇、一種話語方式、一種研究的方法進路,其學科定位是對醫學倫理學和生命倫理學的補充和矯正。
2 身體倫理學的話語場域
2.1 身體的本體性存在是身體倫理學的基本觀點
身體是由軀體與靈魂、物性與神性、感性與理性、自然與社會等多維度構成的不可分割、不可重構生命整體。其中每一個維度的缺損或者被損害都是身體的傷殘甚至毀損。身體的存在是世界和人類存在的前提。身體整全性存在思想凸顯身體的價值:身體是意義的紐結,是意義的發生場;身體是多維價值的主體,不只是顯示遺傳性征的生物載體。
身體本體性存在思想強調,身體是本真的存在,身體的基本結構是身體固有的、不可分割的、不可外力設計或制造的、不可外力賦予或增減的。以下針對身體的行為屬于危害身體安全、違反身體倫理學的行為:人為中斷身體億萬年自然進化的歷程,改寫或強化身體;將科學技術的語言和邏輯強加給身體,罔顧身體內在的語言和發展的自然邏輯;貶低身體作為人類價值的坐標系、生活目的地和幸福根源的終極價值,將人工身體、人造身體強加給人類;無視身體自洽的系統的存在,無視身體擁有自主適應環境的能力、有自己與環境和諧共處的訴求和方式,更改身體元素,機械加工身體、破壞身體本真結構、以人工智能機器人替代身體等。尊重身體整全性和本體存在是尊重生命的前提。試圖用醫學手段改變身體整全性和本體性存在的危害身體安全的行為,都是醫學暴力,都是對身體的傷害,都是踐踏倫理的行為。
2.2 身體間性的倫理關系是身體倫理學的重要話題
莫里斯·梅洛-龐蒂提出的“身體間性”充滿著倫理意蘊,其指向是身體與身體交互之間顯現出來的相互關聯的倫理關系,是“我”和“他人”身體間的倫理對話;身體間性的構架以“身體圖式”作為倫理范式,強調身體間的協調性和相互性;身體間性的倫理性質可以通過身體的意向活動表現出來;身體間性的倫理關系體現為主動能體與被動受體的統一。
醫患之間的倫理關系的解讀,從身體間性入手比主體間性更適宜。爭取最大的健康效益是醫者和患者身體意向性的共同所指,即醫患身體間性決定了醫患雙方互為主體的平等地位,決定了醫患理解、醫患溝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醫者和患者的身體為異體同質的身體間性,決定了通過醫患互動實現共同決策、結成醫患共同體的可能性、現實性和可能遭遇的困難。醫患身體間性的倫理追求境界是將醫患雙方導向醫患共情,導向身體間的對話、協商與溝通。醫療資本運作是消弭醫患身體間性倫理關聯最大的消極因素。當下醫患倫理關系中的各種問題的根脈,深深埋藏在身體、身體間性、人性和醫療運行機制中。
3 身體倫理學學科特征
3.1 以身體為本體選擇,是身體倫理學的特征之一
身體倫理學的本體論基礎是身體哲學。身體倫理學關注整全身體而不僅僅是身體的某一個維度或者某一個方面。關注整全性身體,是生命倫理學的基本范式。我國著名生命倫理學教授孫慕義[3]指出:“身體的倫理即是整全人的倫理、人的整全性倫理或整全性‘我’的身體倫理。”那么,什么是整全性身體?正如有學者在研究身體倫理學的合法性問題的時候指出的那樣:“身體是物質的、自然的,又是精神的、社會的;身體是感性的、非邏輯的,又是理性的、邏輯的;身體是思想的、認識的;又是行動的、實踐的;身體是人類文明和文化的創造者,又是文明和文化的元素和組成部分;身體是醫學的主體,同時也是醫學的客體;身體是皮膚、骨骼、臟器、大腦的有機結合體,身體是人的整體性存在,身體就是完整真實的‘我’,身體不僅是生理、心理的、社會的存在,更是文化的、哲學的存在,身體是無法偽造不可復制唯一合法的身份形態。”[4]因此,身體對身體倫理學具有不可替代的本體論意義。人類的所有倫理行為都是身體整體的行為,是多元因素綜合的結果,而不是某一個方面發生作用的產物。身體支配倫理行為,身體是各種倫理問題產生本原所在。考慮身體的倫理問題,關注身體是朝向事物本身的關鍵。
3.2 以患者感受為話語方式,是身體倫理學的特征之二
患者感受是患者在感受源刺激下產生的患者具身反應,是患者身體個體的、獨特的、無法抹除、無法替代甚至是難以言說的體驗。醫學倫理學和生命倫理學有太多的理性原則,卻沒有一條關注過患者感受。身體倫理學的話語方式即其表達思想的形式不是理性的原則,而是患者感受。
身體感受是身體存在的核心標志,是身體哲學的核心范疇。身體感受是一張網,身體活在感受之網中;人的生活其實就是各種身體感受的集合與糾纏:意識感、快感、性感、幸福感、愉悅感、滿足感、成就感、榮譽感、自豪感、價值感、歸屬感、失落感、孤獨感、寂寞感、壓抑感、挫敗感、羞恥感、欲望、憂郁、憤怒、仇恨、嫉妒等心理掙扎乃至肌膚痛感等生理痛苦,構成了人類生活的基本內容;時間、空間、平衡、動蕩、安寧、騷亂、質量、強度、力度、硬度、高度、溫度、濕度等身體的感受,交織成人類生活的經天緯地;神圣、崇高、善良、正義與邪惡、卑鄙、陰險、罪惡等對立的人性,都根植于身體之中。喪失部分的身體感受,危及生活質量;喪失全部身體感受,即死亡到來。身體自身的生命活動、與外部世界的接觸都是在身體感受的平臺上實現的。
患者感受是包裹患者身體的、揮之不去的霧霾,是各種病痛感受的集合與糾纏:困擾感、焦慮感、不適感、痛苦感、窒息感、瀕死感、恐懼感、絕望感、壓抑感、憤怒感、寂寞感、孤獨感等彌散其中。患者就活在這種情景感受之中。心理掙扎糾合著生理痛苦,構成了患者生活的基本內容。
身體倫理學關注被醫學倫理學和生命倫理學遺漏的患者感受。注重患者訴說,強調傾聽、體認、體察、理解患者感受,并以患者感受作為認知原點,審視和度量醫學活動中的是非善惡之別,言說和評估醫學行為中的道德和利益之爭。
以患者感受為原點的身體倫理學,揚棄了醫學倫理學和生命倫理學的抽象、規范和約束,顯現了身體倫理學的具體、包容和通達。關注患者感受,是身體倫理學基本內核。
3.3 以身體現象學為方法學進路,是身體倫理學的特征之三
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方法在身體倫理學中的運用是指展現患者身體存在的本質然后再加以描述的方法,其基本特征是:排除任何成見、面向身體本身、 直觀把握和描述患者感受。身體現象學方法的關鍵是要返回到意識與世界的原初關聯——身體,回到現象或原初知覺經驗——患者感受。身體知覺經驗和患者感受是最原初的經驗,是身體倫理學認識和實踐的基礎;在身體倫理學的語境中,患者感受是其與醫學之間的一種直接對話和作用關系。由此,身體倫理學的任務是返回醫學診療行為和醫患身體間性的原點——身體與身體感受。
將患者身體與身體感受作為身體倫理學研究的進路,是一種以患者身體為本來面目、以患者知覺為基本介面、以患者感受為基本狀態、以醫患身體間性為基本關系的方法學變革,也是身體倫理學的關注點區別于醫學倫理學、生命倫理學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