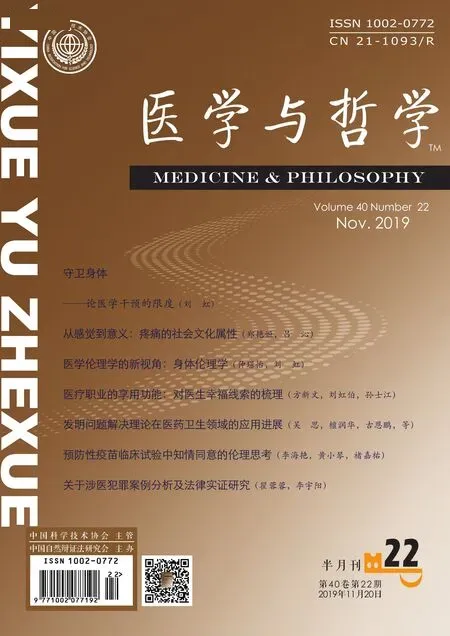淺論《唐律疏議》中的醫事制度*
王海容
西周《周禮》關于醫事衛生管理的記載,證明我國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對醫事衛生十分重視且運用法律制度來進行規制。進入封建時期尤其是歷史上著名的強盛朝代唐朝,頒布了不少有關醫藥衛生方面的法律條文,對我國醫療法制健全有很大的影響。唐代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醫事組織的管理、醫生的教育和選擇,并對醫療事故和利用醫療作欺詐行為進行嚴厲的懲處。唐代中央和地方都設有醫療機構,中央醫療機構由三個部門組成:尚藥局、藥藏局和太醫署。太醫署不僅掌管全國醫療工作,而且擔有醫學教育之責,不斷為宮廷輸送醫療人才。地方上的醫療機構和醫療教育機構規模小、數量不多,主要是由各都督府,大、中、小州的醫學博士負責。唐代嚴格的醫療教育制度和醫療考試制度,保證了整個醫學隊伍的質量和水平。而對醫事制度的完備、細致的規定,則體現在當時一部極為重要的法典——《唐律疏議》。
1 《唐律疏議》中醫事制度的特點
《唐律疏議》中關于醫事制度的相關規定散見于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和斷獄十二篇中,且主要是義務性規范,即醫生從事診療業務的規定是散見于各個罪名中的,沒有涉及醫護人員的權利性規范。
首先,注重對個體權利的尊重和維護。雖然《唐律疏議》作為一部封建法,帶有濃厚的等級觀念,但是,《唐律疏議》法律明文規定了對丁匠、防人、官戶、奴婢等賤民以及囚犯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的保護,并不因其特殊的社會地位而漠視其最基本的權利保護。
其次,注重對婦女的特殊保護。如對于在押的懷孕犯罪婦女,《唐律疏議》亦有在拷決孕婦和處決孕婦時要采取保障嬰兒生命和防止流產等措施等規定。這一規定對后來的法制也有深刻影響,如被宋朝所沿襲。
最后,嚴格規范醫療行為。《唐律疏議》不僅對醫務人員的醫療過失,醫師以治病為名,弄虛作假、騙取財物以及醫師向司法機構提供偽證等行為給予嚴厲的懲罰,而且嚴格規范制藥和賣藥的行為。
2 主要醫事制度
《唐律疏議》雖然只有502條,但卻是疏而不失,面面俱到,是古代法律之集大成者,有的甚至被現代延用。
2.1 宮廷醫療
在《唐律疏議》的首卷《名例》“十惡”之中的“大不敬”包括“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文及封題誤”和“若告造御膳,誤犯食禁”兩種宮廷醫生對皇帝“大不敬”的行為,并對兩種行為進行了解釋和細化,即“議”。議曰:《周禮》:食醫掌王之八珍。所司特宜敬慎,營造御膳,須憑《食經》,誤不依經,即是“不敬”[1]11。
在制藥方面,唐代有十分明確且嚴格的規定,尤其是合和御藥,因用藥者系皇帝,更是要求甚嚴,尚藥局和藥藏局的宮廷醫生必須對經典典籍和處方掌握透徹、嚴格遵循,否則將招致嚴重后果。根據《唐律疏議·職制》,以下三種情況被認為是合和御藥有誤:第一種情況是“誤不如本方”,具體指藥的份量和制藥方法不符合本方要求,即“分兩多少不如本方法之類”;第二種情況是“封題有誤”,具體包括題封上注明藥的性質與處方不同(即“合成仍題封其上, 注藥遲駛冷熟”)和藥品形態與處方不符(即“以丸為散,應冷言熱之類”)兩種情形;第三種情況是對藥的選用和清洗不精細、不到位,未做到“應熬削洗漬”及“去惡留善”等要求,即所謂的“料理簡擇不精”。在這三種情況中,前兩種直接威脅到皇帝的安危,故作為“大不敬”列入“十惡”,且刑至絞;最后一種情況可能導致的最壞結果就是影響療效,不致傷害人的健康和生命,危害較輕,故僅科以徒刑一年。另外,根據重視實際危害結果的原則,凡未進御者各減一等。
唐代延續了周朝時期的“食醫”的編制。“食醫”是我國最早的宮廷營養醫生[2]。食醫的主要工作是“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3]。而唐代的食醫對皇帝的飲食安排,必須以《食經》為依據,如果違反《食經》的要求,則是“大不敬”行為,將被處以絞刑;若有穢惡之物在食飲中,則徒二年;簡擇不精及進御不及時,則參考前一條減二等處罰。
2.2 民間醫療
除對宮廷醫療行為有所約束外,《唐律疏議·雜律》之“醫合藥不如方”條對面向普通民眾的醫療行為也作出了相應的規制。“醫合藥不如方”條包括如下內容:其一,把醫師和賣藥者在用藥或賣藥中不符合本方的行為視為犯罪。其二,從主觀上進行了區分,并根據主觀上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刑罰規定,如“誤不如本方”者,出現患者死亡的僅“徒二年半”,而“故不如本方”導致患者死亡的,以“故意殺人罪”論處,即使患者沒有任何損害后果的,醫師也要被“杖六十”。其三,對賣藥者的行為進行類推,即“賣藥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亦如之”[1]483。其四,根據親疏尊卑對醫師(賣藥者)的上述行為應受刑罰作出進一步規定,如患者系親屬尊長,即使罪過輕于過失,也按過失殺傷罪論處;若死亡患者系奴婢,則僅“徒二年減三等杖一百之類”[1]483。
2.3 禁巫
唐代統治者已充分認識到了巫術侵害人的生命健康,破壞國家正常政治生活的危害,因而對其規定有造畜蠱毒罪、造厭魅罪及造符書咒詛罪、妖書妖言罪等專門罪名,且處刑很重。在《唐律疏議·名例》篇中,將“造畜蠱毒罪”、“造厭魅罪及造符書咒詛罪”,歸入十惡大罪之列嚴厲打擊。犯“造畜蠱毒罪”者,除本人被處絞刑外,還要連帶同居家人及知情不報的里正、坊正、村正;犯“造厭魅罪及造符書咒詛罪”且目的為殺人者,以“謀殺論減二等處罰”。明、清沿用了此兩項罪名及其刑罰。除此外,《唐律疏議》還造了“妖書妖言罪”。據疏議,妖書指“構成怪力之書”;妖言,指“詐為鬼神之語”,皆借以妄言他人或自己有“休證”(吉祥的征兆),國家有咎惡,其要害是“并涉于不順者”。自造妖書妖言及傳用以惑眾者,皆處絞。唐代對巫術(包括巫醫術)的打壓,從客觀上促進了中醫醫學的發展,推進了文明進程。
2.4 對“疾殘”者的照顧
在《唐律疏議》中,將“疾殘”按殘損的輕重依次分為殘疾、廢疾(有殘疾而不能作事之人)、篤疾(重癥者)三類并據此分別給予不同的關懷和照顧[4]。首先,是在律條中規定篤疾者享有與年屆八旬老人相同的配侍丁的待遇,如“祖父母、父母、通曾、高祖以來,年八十以上及篤疾,據令應侍”[1]69。其次,減免廢疾者刑罰,如廢疾者犯流罪以下的罪名,可以“收贖”(即以銀贖罪)。再次,禁止對廢疾者刑訊逼供。如“諸應議、請、減,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并不合拷訊,皆據眾證定罪,違者以故失論”[1]550。最后,《唐律疏議》對“疾殘”之人給與減免賦役的照顧。該法中的相關律條有,《唐律疏義·名例》之“犯徒應役家無兼丁”條、《唐律疏義·職制》之“役使所監臨”條、《唐律疏義·戶婚》之“脫漏戶口增減年狀”條等。
《唐律疏議》制定了非常詳備的法條對“疾殘”者予以一定的關懷和照顧,這固然是因為“疾殘”者對統治者的威脅相對較小,而統治者通過此又可體現其仁政的緣故,但對“疾殘”者來說,這確實是一種來自“國家”的保護和照顧。
2.5 囚犯及賤民的醫事權利
唐朝非常注重囚犯的衛生保健工作,《唐律疏議·斷獄》之“不給囚衣食醫藥”條規定:囚犯在生病時,經主司陳牒,長官親驗后應當給予救治,如果囚犯病重還應脫去其枷、鎖、丑,并允許囚犯的一名家人進入監獄給予照顧。如果獄吏不按規定給囚犯醫藥或應脫去枷、鎖、丑而不脫,則罰其“杖六十”;因此導致囚犯死亡的,則罰獄吏“徒一年”。 值得一提的是,《唐律疏議》專設《斷獄》之“處決孕婦”和“拷決孕婦”兩條律條對囚犯中的孕婦給予了特殊的保護:如果懷孕婦女犯死罪的,“當決者,聽產后一百日乃刑”;對懷孕婦女需要用刑的,也要給予減免和照顧;同時規定了對違反上述律條者的處罰措施。
此外,《唐律疏議·雜律》之“丁防官奴婢病不救療”條規定了對在役丁匠、官戶、奴婢的醫事保護,該條規定:“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戶、奴婢疾病,主司不為請給醫藥救療者,笞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1]484雖然為丁匠、防人、官戶、奴婢進行醫療的目的是為了控制病情的惡化及病役的蔓延,但是這些規定也體現了統治者對生命的尊重,從客觀上保障了這些人的健康。
2.6 對食品衛生和公共衛生的重視
隋唐時期的衛生保健較前代有不少進步,隋代人們懂得蚊蠅接觸飲食之后容易使人得病,并首次提出“飲食中毒”的概念,《唐律疏議》則明確規定了“以毒藥藥人”的罪名。該條規定:有毒的肉類食物,一旦致人發病,就必須將所剩下的焚毀,“違者杖九十”。如果故意送給別人或出賣,致使有人中毒得病者,“徒一年”;因此造成他人死亡的,“絞”;即使是他人自己食用而死亡的,也要按過失殺人給予處罰(盜取該物而食用致死者除外)。這條律令對預防食物中毒的發生具有重要意義,至今仍有借鑒價值。
唐代對公共衛生也較重視,每年給藥以防民疾,如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玄宗親制開元《廣濟方》5卷,頒布示天下;天宗五年(公元746年)又令郡縣長官就《廣濟方》中選其切要者,于村坊要路處榜示宣布;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又親制《貞元集要廣利方》5卷,頒布于州、府,以療民疾。除此外,唐代還設有專門的收容機構,佛教徒私人組織的“悲田坊”和政府設立的“養病坊”,專門收容窮苦病患,收養治病。
3 結語
《唐律疏議》距今已千余年,但其有關醫事制度方面的規定,內容豐富、制度翔實、影響深遠,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借鑒。《唐律疏議》不僅注重保護皇族的利益,而且注重對包括賤民在內的所有個體的權利的尊重和維護;不僅對“疾殘”者予以一定的關懷和照顧,而且對囚犯實施恩宥和優恤,展示了中國傳統社會保障的初步形態;不僅對普通婢女,而且對在押囚婦也給予醫事上的特殊保護,這一方面體現了婦女在唐代社會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體現了政府的人道主義作風;不僅對巫醫術嚴厲禁止,而且對醫療行為進行嚴格規范,從客觀上保障了普通民眾的生命健康,促進了中醫學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