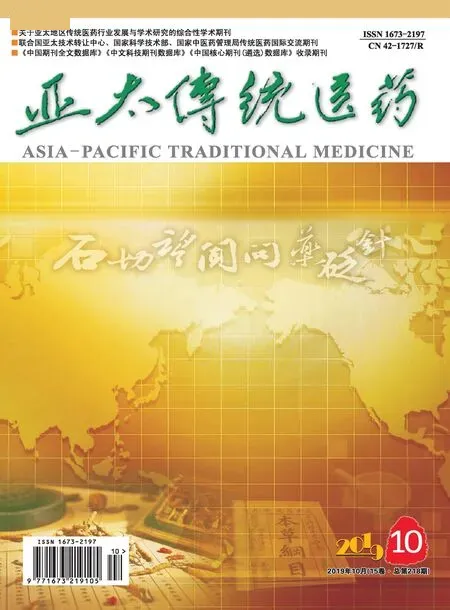張菁主任醫師治療經行頭痛經驗
李丹妮,張 菁*
(1.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婦科,天津 300193;2.天津中醫藥大學,天津 300193)
經行頭痛是指每遇經期或行經前后,出現以頭痛為主要癥狀,經后則止,為婦科臨床常見病。經行頭痛的發生與月經周期關系密切,本病西醫學歸屬于經前期綜合征(premenstrual syndrome,PMS)的范疇,是指在黃體期出現軀體癥狀、精神癥狀和行為改變,月經來潮后自然消失。現代醫學對本病病因的研究尚無定論,認為可能與女性精神因素和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相關,傳統觀點認為本病與經前女性機體內雌激素過多而孕激素不足,與雌、孕激素比例失調相關,目前的研究認為黃體晚期孕激素的撤退可能是激發PMS的原因,此外神經遞質異常、維生素B6缺乏均與PMS的發生相關[1]。西醫學對于本病的治療常基于心理治療,對癥予抗焦慮藥、抗抑郁藥、維生素B6或口服避孕藥以改善臨床癥狀。中醫學辨證論治而不拘泥于辨病論治,使得中醫藥治療本病具有明顯優勢。導師張菁主任醫師從事婦科臨床工作30余年,臨床經驗頗豐,對本病的治療療效確切,現將其治療本病的經驗介紹如下。
1 謹守病機,詳審虛實,明辨經絡
經行頭痛屬中醫學“內傷頭痛”的范疇,早在清代張璐所撰的《張氏醫通》中就有“每遇經行頭輒痛”的記載。其病因病機為情志內傷,導致肝郁化火,肝火上擾清竅,或瘀血內阻,使血絡不通,不通則痛,又或者素體血虛,經行氣血下注沖任,使腦失所養,而致不榮則痛。張菁主任醫師認為經行頭痛的病理關鍵在于氣滯和血瘀,與肝臟密切相關。女子以血為本,以氣為用,《素問·調經論》云:“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生理狀態下任脈通暢,太沖脈盛,血氣充盈,有滿而溢,月經方可應時而下。肝藏血,主疏泄,喜條達而惡抑郁,經行頭痛與肝密切相關。《臨證指南醫案》云:“女子以肝為先天,陰性凝結,易于怫郁,郁則氣滯血亦滯。”現代社會,受生活、工作、家庭等多種因素影響易導致女性情志不暢,而女子又以肝為先天,若情志不暢,則肝失條達,氣機不宣,加之經前期沖任氣血沖盛,若肝疏泄失司,則致血不能下注胞宮,氣血壅滯,沖氣夾瘀血上逆,阻滯腦絡,脈絡不通而致頭痛。正如《傅青主女科》:“經欲行而肝不應,則拂其氣而痛生”,故張菁主任醫師治療本病時,常以行氣活血、通絡止痛為要,同時注重疏肝藥物的使用,使肝氣條達,氣行則血行,氣血通暢,則頭痛自除。
張菁主任醫師認為經行頭痛一病,雖臨床上氣滯血瘀者為多,但不乏有氣血虛弱者。《素問·脈要精微論篇》載:“頭者,精明之府”,腦為髓海也,五臟六腑之氣血皆上榮于頭面,濡養腦竅。素體虛弱之人,本氣血不足,加之行經期氣血下注胞宮,經后血海空虛,不能上榮頭面,使腦失所養,導致不榮則痛。氣為血之帥,若素體氣虛,氣不能推動血液運行,易導致瘀血內阻。因此也可表現出虛實夾雜之證,臨證中應詳審頭痛之虛實,經前頭痛者多屬實,經后頭痛者多屬虛,刺痛、脹痛、掣痛多屬實,空痛、隱痛多屬虛。此外,應明辨臟腑經絡,以做到用藥精當。
頭痛常因部位不同而所屬不同經絡,張菁主任醫師臨證常主張分清臟腑經絡,在行氣活血、通絡止痛的基礎上酌加引經藥。如后頭痛下連項部多屬太陽經頭痛,可加蔓荊子、羌活、川芎等;前額連眉棱骨痛多屬陽明經頭痛,可加葛根、白芷、知母等;頭兩側疼痛多屬少陽頭痛,可加柴胡、黃芩等;巔頂頭痛多屬厥陰頭痛,可加吳茱萸、藁本等。靈活運用引經藥能夠使藥物直達病所,藥專力宏,取得良效[2]。
2 標本兼治,順應陰陽,調暢氣血
張菁主任醫師主張經行頭痛的辨治應分清標本緩急,急則治其標,旨在緩急,多用膈下逐瘀湯加減以活血化瘀,行氣止痛,常用藥為延胡索、白芍、桃仁、紅花、雞血藤等,延胡索為止痛要藥,《本草綱目》記載:“延胡索,能行血中氣滯,氣中血滯,故專治一身上下諸痛。”現代藥理研究認為從延胡索中提取的延胡索乙素具有明顯的鎮痛作用。白芍能養血柔肝,有緩解止痛之功,現代藥理研究表明其有效成分白芍總苷具有良好的抗炎、鎮痛作用[3]。桃仁能入心肝血分,善泄血滯,能夠增加腦血流量,降低腦血管阻力,改善血流動力學,同時具有鎮痛作用[4]。紅花為活血化瘀、通經止痛之要藥,紅花中主要成分紅花黃色素對中樞神經系統有鎮痛、鎮靜作用[5]。雞血藤補血行血,有舒筋活絡之功,取其藤類通絡之意。
緩則治其本,旨在調經。經行頭痛一病以頭痛為主癥,通常月經前后出現,究其病因,根本在于經行前后氣血失調,因此當頭痛緩解后,常重在調理氣血,使氣暢血和則頭痛自止。月經周期的演變是天癸陰陽消長轉化的結果,張菁主任醫師主張根據月經周期特點,順應陰陽變化補腎調周,調暢沖任氣血。行經期重陽轉陰,以活血調經、化瘀生新為要;經后期血海空虛,陰長陽消,應滋陰養血以促進內膜生長和卵泡發育;經間期為氤氳之時,重陰必陽,疏肝補腎,活血化瘀,重在促新;經前期陽長陰消,補腎助陽,以維持陽長。
3 病案舉隅
聶某,女,37歲,已婚,2018年12月29日初診,主訴“經前及經期頭痛6月余”。患者平素月經5~7天/24~28天,量少,色暗紅,夾血塊,經前乳房脹痛,痛經(+)。末次月經2018年12月24日。近6個月每于經前4~5天出現頭痛,以頭頂部及兩側太陽穴處明顯,至月經來潮后2~3天頭痛緩解。刻診:情志不暢,易怒,乳房脹痛,納可,寐安,二便調,舌暗紅苔薄白,脈弦細。曾于內科就診除外顱腦病變。行婦科彩超示:子宮大小5.1 cm×4.0 cm×3.2 cm,內膜厚0.5 cm,雙附件未見明顯異常;西醫診斷:經前緊張綜合征。中醫診斷:經行頭痛,證型:氣滯血瘀證。治則:行氣活血、通絡止痛。處方:桃仁10 g、丹皮12 g、烏藥10 g、延胡索10 g、梅花6 g、五靈脂10 g、紅花10 g、枳殼12 g、香附10 g、菟絲子10 g、皂角刺10 g、玫瑰花12 g、雞血藤15 g、柴胡10 g、郁金10 g、川芎10 g、吳茱萸6 g、藁本10 g。共7劑,日1劑,水煎服,囑患者調情志,避風寒。
2019-1-5二診:患者頭痛消失,服藥平和,未訴其他不適,舌暗紅苔薄白,脈弦細。處方:劉寄奴10 g、澤蘭10 g、女貞子15 g、赤芍10 g、白芍30 g、覆盆子10 g、雞血藤15 g、枸杞子10 g、牛膝10 g、菟絲子20 g、鹿角霜20 g、玫瑰花10 g、川芎10 g、延胡索10 g、黃精10 g、郁金10 g、藁本10 g、柴胡10 g。繼服7劑。
2019-1-12三診:患者訴工作壓力大,時腰酸,舌淡暗,苔薄白,脈弦細。處方:當歸10 g、白芍30 g、菟絲子15 g、川芎10 g、熟地黃15 g、烏藥10 g、柴胡10 g、香附10 g、玫瑰花10 g、延胡索10 g、鹿角霜20 g、益母草15 g、郁金10 g、巴戟天10 g、淫羊藿10 g、吳茱萸6 g、藁本10 g。繼服7劑。
2019-1-19四診:患者訴2019-1-18月經來潮,經前頭痛較前減輕,乳房脹痛減輕,本次月經量較前增多,色暗紅,伴血塊,舌暗紅,苔薄白,脈細。予初診方去柴胡、郁金、梅花、月季花、枳殼,加當歸10 g、川芎10 g、牛膝10 g,繼服7劑。其后根據月經周期予上述方劑調理,2019-2-16復診時患者訴月經來潮前頭痛消失,無乳房脹痛,月經量增多,色紅,少量血塊,無痛經,無其他不適。予養血活血方劑7劑后囑患者停藥。后隨訪患者經前未再發頭痛。
按:患者平素情志不暢,肝失條達,結合初診癥狀可辨為氣滯血瘀證,故予膈下逐瘀湯加減以緩解頭痛,酌加柴胡、郁金、香附、玫瑰花等疏肝理氣之藥,并加吳茱萸、藁本、川芎等引經藥。二診患者頭痛消失,為頭痛緩解期,且即將進入經間期,故治則以疏肝補腎、活血化瘀為主,三診經前期,月經將來潮,以補腎助陽、行氣活血為法,四診正值經期,當以行氣活血、通絡止痛為主。
4 結語
張菁主任醫師在臨床診治本病時重視鑒別診斷,通過病史采集,借助輔助檢查除外高泌乳素血癥、顱腦占位等病變,明確診斷為經行頭痛者再行中藥治療,以免失治誤治,貽誤病情。治療中,急性期以治標為主,常從氣滯血瘀論治,注重調肝,目的在于行氣活血、通絡止痛。由于經行頭痛與月經周期密切相關,因此緩解期的治療常結合女性月經周期生理特點,順應陰陽的消長變化,補腎疏肝養血,使氣暢血和,清竅得養,頭痛自愈。此外,張菁主任醫師注重明辨臟腑經絡,重視引經藥物的使用,使藥效直達病所,事半功倍。由于本病常反復發作,與情志、精神壓力等因素密切相關,因此張菁主任醫師常常結合情志疏導,強調日常調護的重要性,調情志,避風寒,慎起居,如此治療,每獲良效。